編按:王耀宗教授和博士生陳冠匡一同撰寫〈從台獨運動的歷史看香港的本土主義〉,探討香港和台灣的本土主義。文章內容豐富,現分四篇刊登,本文為第三篇。
本土主義興起的背景
從1997年至2003年,香港人經歷各種跌宕,先有亞洲金融風暴、禽流感襲擊,後有SARS(非典型肺炎,俗稱沙士)奪去299條人命。各種打擊對香港經濟民生影響甚大,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領導的特區政府雖未致於無力應對,但起初的鴻圖大計因經濟困境而擱置;新機場開幕的混亂、八萬五建屋計劃的無疾而終等,都令其首5年任期蒙上陰影。其後,董特首推行「高官問責制」,希望強政勵治,挽救大家對「港人治港」的期望;可惜,其政府於2003年強推《基本法》23條立法,加上經濟蕭條,50萬人上街,令特區政府陷入困境,其後的紅灣半島事件、領匯上市觸礁,更成為「駱駝背上最後一根稻草」。
2003年的50萬人示威遊行成為北京對港政策改變的分水嶺,1997年至2003年間,中央的治港原則為不插手、不干預香港事務(註1),而中央6年來的克制,在分水嶺前後有明顯的變化,更有各種跡象顯示中央加強對港的干預(註2)。首先是通經貿,例如:中央首先扶助香港經濟,港府與內地簽訂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稱《更緊密經貿安排》),在貨物、服務業及貿易三方面,促進兩地經濟融合。而除經濟方面,中央此後對香港政治及社會的干預,亦比03年前明顯得多。
在政制改革方面,因《基本法》附件一、二限制了主權移交後首10年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方法,香港社會開始對其後的選舉方法展開討論;其中,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雙普選」成為泛民主派的主要訴求及論述,而根據當時香港大學民意研究中心調查,「雙普選」的支持度一度高達七、八成。(註3)然而,北京經歷2003年23條立法一役仍有餘悸,生怕香港民主化會影響中央管治,故此,中央開動國家機器,針對「雙普選」作反對論述,如普選不能損害一國兩制,「一國」高於「兩制」,中央對港民主化有最終決定權等等。
而最明顯的干預,乃2004年的人大釋法,這人大常委決議非但否決07/08年「雙普選」,並且決定2008年立法會以及以後的選舉中,地區直選與功能組別議席比例不變。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的干預,以此釋法為里程碑,明確地表示中央對政制發展有最終決定權,而其後十年的政制發展,以中央高度介入為主調。
中央對07/08雙普選「落閘」,埋下了2010年民主黨進入中聯辦談判的伏線。由於立法會否決了政府就07/08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的建議,政制改革原地踏步,往後數年政制改革毫無寸進,而2011年政改方案的通過也只反映中央對港政制改革步伐中的主導地位(註4),其後對特首後選人「愛國愛港」的討論,以及2014年8月31日人大「8.31決定」,只令中央自2003年後對港的直接干預更明顯、更赤裸,也令港人產生愈來愈大的抗拒。

在社會經濟層面,中港融合趨勢亦於2003年後變得明顯,《更緊密經貿安排》除為中港商人提供商貿機會,亦方便內地居民到港旅遊,推出自由行政策,隨着香港與內地愈來愈多城市簽訂協議,擴展計劃,至今已有49個內地城市居民可以個人身份訪港。(註5)2009年實施但較早前已收緊的深圳戶籍居民「一簽多行」政策,更曾令內地旅客(特別是走私的水貨客)數字飆升,甚至超出香港人口數倍 (2003年的850萬;2014年的4,720萬),驚人數字令人質疑究竟香港能否承受如此龐大的旅客流量,更甚,水貨客對日常用品的搶購嚴重影響香港居民的日常生活,根據《蘋果日報》2013年的報道,屯門和上水在全新界和深水埗等地區的物價最貴,而對奶粉、藥用品、日常用品等影響最大。(註6)
中港融合的影響不僅在於日常生活,背後的是兩種認同身份之間的矛盾,而2006年至2007年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拆卸,到2009年至2010年間的廣深港高速鐵路在立法會撥款,正反映舊有的「殖民地香港人」身份被磨蝕。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爭議一方面反映港人強烈抗拒「中國人的身份」;另一方面,北京極其擔心香港人心未歸的事實。爭議因一本《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的偏頗內容而引起,令香港各界對國教科的內容關注,生怕中國執政集團真如該手冊所言「進步、無私與團結」為小孩子洗腦;經過一連串的示威、佔領政府總部及學民思潮成員的絕食行動,特首梁振英決定取消國教科的3年開展期,由學校自行決定開科事宜。(註7)

總括而言,中央對港政策在2003年前後有明顯變化,如劉兆佳所述,1997-2003年間中央對港政策離不開「不干預」、「以不變應萬變」的原則,但此原則在2003年後起了重大變化。(註8)再者,中央的干預並非只針對較重要的政制改革,對香港經濟、社會事務,中央的「無形之手」每每有跡可尋。
本土主義的論述
在北京不斷增強其影響力之下,「本土主義」勃然而生,本土主義論述出現的時間實有兩波:第一波(自2007年起) 及第二波本土論述 (自2012年起)。
在中央漸漸由幕後走到幕前之時,第一波本土論述也在香港政治論述中嶄露頭角,然而,本土論述卻非轉瞬間走到港獨這一步,第一波的本土論述不能避免地與當時熱熾討論的「八十後」、「新社會運動」、「世代論」混為一談。其實,八十後的出現,正因排拒着上一代學生隨年紀漸長,而提出經濟上北望神州、政治上民主回歸,故之八十後要回歸本土。(註9)而當其時,回歸本土的要義乃對香港這片土地的感情,甚至對鄉土生活的熱愛(註10),這份感情最主要反映在「反高鐵、保菜園村」的運動中。
這一波的本土論述源自2003年起的一連串因城市規劃問題而引起的本土運動,大抵可被整理為幾個重點,第一:否定中環價值;第二:對發展至上主義的排拒;第三:重視中下階層。(註11)雖非「戀殖」,但第一波的本土論述卻無可避免地與殖民地歷史扣連,對天星、皇后碼頭的集體回憶,對灣仔囍帖街的保育,都是從殖民地歷史中尋回身份認同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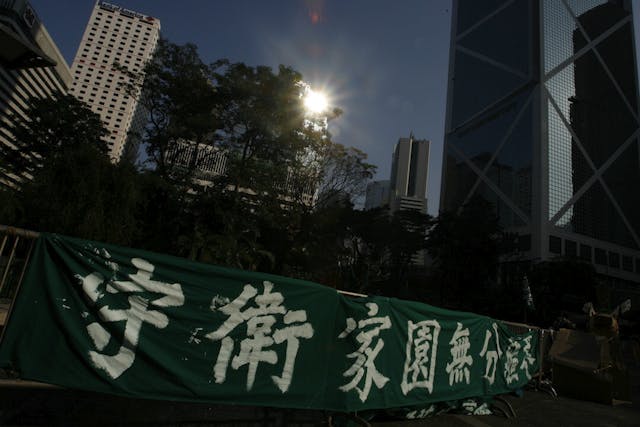
第二波的本土論述,以陳雲的「城邦論」為主,該理論的形成背景肇於民主黨走進中聯辦談判,以陳雲(2011)的說法,那是「投共」,而大陸孕婦來港產子事件,同樣是其背景之一。與第一波的本土論述不同,城邦論要解釋的是中國與香港的關係,並非只是香港人與該片土地之間的關係,而在城邦論中,香港是有170多年歷史,卻被形容為「孫女」,反觀「阿爺」的歷史只有短短的60餘年(註12),不值一哂。推到極致,就是「港獨論」。
城邦論立論背景是日趨熱熾的中港矛盾,特別是身份認同的矛盾。假如第一波的本土論述是在殖民歷史中尋回自我,那城邦論則是建基於對中共或中國的排拒的論述。香港在陳氏眼中幸得英殖政府引入自由及法治,得以保留優良中國傳統文化,故更要排拒中共和中國的劣質文化。而在陳氏的《城邦主權論》中,香港人的國民身份建立,被遠遠追塑至開埠前:(一)嶺南遺民;(二)英裔遺民及南亞遺民;(三)華夏難民;(四)南洋難民。(註13)

筆者認為第二波的本土論述最明顯特徵是對中共或中國的排拒,並非只尋回舊殖民地身份,而是建立有深厚歷史淵源的香港人身份。據徐承恩(2014;2015)的說法,香港華人原有四大族群(本土、客家、蜑家、福佬),本土族群與客家族群影響只限於新界,到1898年才租借予英國,之前對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發展影響有限。故之,徐氏認為在香港開埠前後,擔當更重要角色的是蜑家與福佬兩大族群,他們甚至參與了開埠前的走私貿易體系,是殖民地政權的第一批合作者。徐氏對香港史開端的看法,有一大膽推論:他們的歷史就是香港的「史前史」。(註14)
蜑家與福佬族群在香港開埠後,得到英國政府的「嘉許」,批出土地,從中獲利,成為首批華人精英,佼佼者包括新加坡歸僑譚亞才,蜑族郭亞祥和盧亞貴。而真正發展出視香港為家的「主體意識」,徐氏認為那要等到以海洋族群為主的香港華人受西方文化影響之後,西方教育的引入,才培養出一群穿插於中西之間、又視香港為家的華人。(註15)
第二波本土論述將香港人身份建基於100多年的殖民歷史,甚至比開埠更早期的史前史,無論是否直接影響個別本土運動的參與者,也必定為本土主義運動提供了理論基礎,提供了政治遊說的說明。(註16)
綜觀以上兩波本土論述,理論構成的時代背景略有不同,所要回應的爭議及訴求亦然,第一波回應的是天星、皇后碼頭拆卸、市區重建、高鐵建造,舊有「殖民地香港人」身份正在褪色,年青一代要在殖民地歷史的集體回憶中尋回身份,而第二波卻受到一連串的中港矛盾事件影響:如D&G事件、新界東北爭議、反國民教育科、「光復上水」行動、大陸孕婦來港產子、雙非等,對中共和中國的排拒比第一波本土論述明顯得多。中國對香港的「再殖民」或「文化入侵」並非只趨生一系列本土論述,亦為政治參與者製造助力,以「本土」議題吸引選票、發動集體行動,大致來說,本土主義的社會及政治組織性並不強。他們往往通過社會網絡媒介作出聯合行動,近年更對傳統泛民之「和理非非」守則提出強烈批評,認為應改以「勇武」對抗建制派,更連一向在立法會被視為最激進的組織,如人民力量及社會民主連線,也被他們批為過度溫和。2016年農曆年初一晚發生的旺角騷亂的嚴重衝突事件,警方大舉拘捕100多人,有些就是「勇武派」的成員。
註1:劉兆佳,(2013),《回歸後的香港政治》,香港:商務印書館,頁7。
註2:見馬嶽,(2010),《香港政治:發展歷程與核心課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頁73。
註3:同上。
註4:事實上,2010年政改方案對選特首的選舉委員會人數的調整,比起2005年的方案更為「倒退」(2005:1,600人,2010:1,200人)。而立法會所新增的十個議席,則為地區及功能組別各分得五個。
註5:旅遊事務署。
註6:〈受自由行水貨客影響 屯門 上水 物價貴絕新界〉,《蘋果日報》,2013年7月25日。
註7:蔡耀昌,(2015), 〈2003年以來的香港社運新貌及其結構根源〉,載於鄭宇碩編,《香港政治參與新型態》,香港:香港城市大學,頁86。
註8:劉兆佳,(2013), 《回歸後的香港政治》,商務印書館,香港,頁11,15;據劉氏所言,其變化可見於中國共產黨的文件及領導人發言,見頁15-31。
註9:鄒崇銘,(2013),〈少年香港說〉,載於黃塔烽、許煜編,《80前後:超越社運、論述與世代的想像》,香港:圓桌精英出版社,頁26。
註10:董啟章,(2013),〈土地,就在我們的腳下──反高鐵苦行者給我們的啟示〉,載於黃塔烽、許煜編,《80前後:超越社運、論述與世代的想像》,香港:圓桌精英出版社,頁255。
註11:陳景輝,(2009), 〈本土運動的緣起〉,載於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絡編,《本土論述2008》,香港:上書局,頁29。
註12:陳雲,(2011),《香港城邦論》,香港: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頁9, 24, 114
註13:嶺南遺民乃在新界聚居的農民、漁民及海盜,聚居期遠於1842年前。英裔遺民及南亞遺民隨英殖民政府而來,多為官員、傳教士、鴉片商及苦力。華夏難民則在1950年代至70年代末逃避混亂中國政局而來。最後的南洋難民是因五十年代印尼等地獨立建國後受排斥的華人。 以上資料引自陳雲,(2015),《城邦主權論》,香港:四筆象出版社,頁38。
註14:徐承恩,(2014),《城邦舊事──12本書看香港本土史》,香港:紅出版,頁22;亦可參考《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香港:圓桌文化
註15:徐承恩 2015, 〈香港人千年史: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載於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絡編,《本土論述: 2013-2014》,台北: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55, 57。
註16:香港有關本土主義的論述近年可謂百花齊放,有經特首梁振英批評而獲關注的《香港民族論》,而由一眾學者所書,宣稱走「第三條道路」(即非「民主回歸」亦非「獨立建國」)的《香港革新論》中,書中黃冠能(2015)與何俊霆(2015)亦分別有對香港人的身份作出討論,而兩人都以「自由」和其他的核心價值為重點(如「法治」、「廉潔」等),同樣地都是以英殖政府帶來的舶來品,根據何俊霆(2015)的說法,七十年代在港英政府管治下,自由、法治和廉潔等核心價值得以在鞏固,該十年為其關鍵時期。
從台獨運動的歷史看香港的本土主義・四之三
本系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