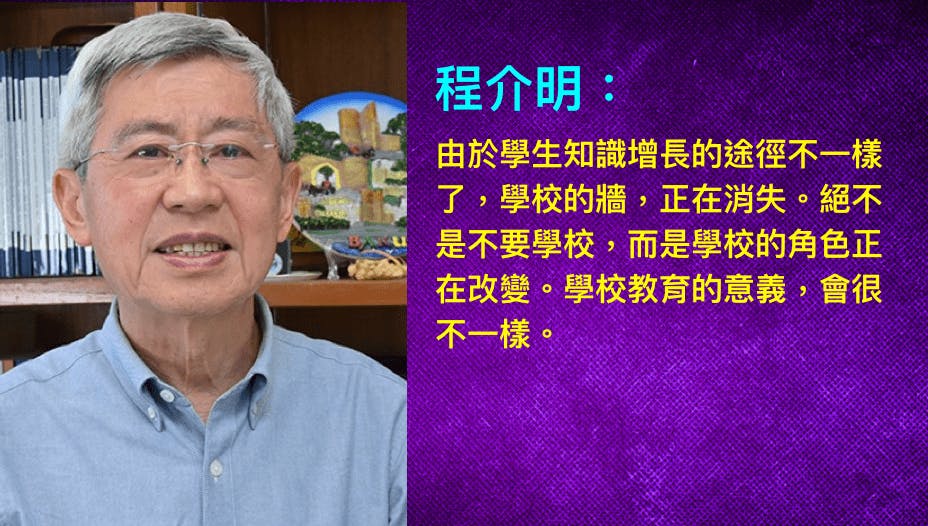上周談到OECD關於學校未來的四種情景,又與朱永新的「未來學校」互相呼應。這之後,參加了幾個會議,不期而然,都與這個話題有關。國際上、中國內地、香港,在教育問題上的討論,話題正在迅速轉變,匯聚到「學校的未來」。因此在這裏與讀者分享。
這種話題的轉變,是因為全球的疫情肆虐,學校被迫停課。停課帶來很多的不幸,在很多國家,冒着劇升的疫情還要復課,就是因為心痛學生失去了教育。而教育,往往與「上學」畫上等號。「上學」很重要,學校是教育的重要基地,這大概沒有人會否定。關鍵是,當「上學」成為不可能,怎麼辦?
於是出現全球性的「線上教學」,其散播速度不亞於新冠肺炎(雖然不排除世界有些角落、即使是富裕國家的有些角落,束手無策;學生白白喪失了幾個月的學習)。不過,同樣是線上教學,卻會有不同的取向。第一種:盡量希望能夠滿足實體課堂可以做到的。第二種:在停課的情況下,改變了不少學生的學習模式,有了不少新的嘗試。第三種:拋開原來正規課程的格局,設計新的學習嘗試。
這裏面,不同的社會與文化背景,會有不同的情形。例如在公開考試壓力大的地方,忙於完成應試需要的學習內容,就變成了教師和學生最牽掛的。不同的年級,也會有不同的情形。例如高年級的學生,自學的可能性就比較高。幼稚園,就始終是「重災區」。當然,教師的心態與水平、學校的文化、教育制度的運作模式,都令到各地發生的種種嘗試很不一樣。因此,全球的圖像,是非常多元參差,但也可以說是遍地開花,豐富燦爛。
學校社會 結成夥伴
不說全球,只看香港,也是一樣。有些學校,不習慣變化,開始幾個月,按兵不動,到後來也不得不變。有些學校,開始時勉為其難,權宜姑且,後來才熱起來,結果產生不少精采的經驗。也有些學校,平常就很多創新,廣納各種教學資源,停課之下,反而大展拳腳。不同的學校,其文化、習慣、心態都會不一樣。就算在同一所學校,不同的教師,也會有不同的態度和施展空間。香港因為採取「校本發展」模式,因此有橫向的多姿,但也有縱向的參差。這是現實。現實本來就是複雜的,只是人們慣於簡單的單一結論,來判斷或者描述一個複雜的情景。
但是,在種種五花八門、目不暇給的情形裏面,有一個明顯的共同點:學校的牆,正在被打開。是疫情,使學校的牆,不由分說地被迫要打開。也使學生,被迫要在學校圍牆以外學習。這與OECD的學校前景──教育外判、學校成為學習中心……──不謀而合。這也是為什麼近期的網上討論,不論是國際、內地還是香港,正在逐漸移向「學校的未來」。因為疫情期間發生的種種,誘使人們去考慮:把學生關在學校的牆內,必要嗎?足夠嗎?合適嗎?也誘使人們去考慮:把學生放到學校的牆外,有可能嗎?有優點嗎?有缺陷嗎?
再想一想,學校的牆,其實已經不斷地在打開。不過疫情之下的停課,迫使我們去打開「課堂」的牆,而課堂往往被認為是學校教育的核心。不是常有人說:「教師要教好每一堂課!」「學生的轉變,由課堂開始!」課堂沒有了,就成為對學校教育最大的挑戰。
為什麼說,學校的牆,不斷地在打開。第一種情形:學校授課結合現實。這本來是多年來許多教師所做的,良好願望是希望學生學的有用,又或者學得有興趣。今天看來,其意義,其實是脫離「分數」、「考試」、「學歷」這些「實際」,而把「課堂」擴充到課堂以外。這是過去在不知不覺中走過來的。回想筆者在學校學物理,牛頓定律,是從黑板上的公式開始的,接着就是習題計算,根本沒有空間知道其實在意義。是完全另外一種學習,現在已經比較少見。
社會參與 已成常態
第二種情形:把社會引進學校。學校邀請校外的力量,進入學校協助──家長進校、校友回校、嘉賓講座、駐校音樂家、駐校作家、體育教練、舞蹈教師……──在香港學校已經是司空見慣,不是什麼新聞。都是把校外的現實,拉進校內的學習生活。就像本欄介紹過的,從社會新聞、街頭現象學習法律理論,就是讓學生實實在在地感覺到,理論是從社會上來的。
第三種情形,把學生送進社會。這在最近幾年,愈來愈廣泛。一項全港1595所學校的調查,包括中學、小學、幼稚園、特殊學校,平均每所學校11.3個項目,屬於與校外社會上的機構結夥;涉及超過4000個校外單位。除了一貫的種種比賽,很多都是課程以外的活動,把學生的學習經歷,拓展到學校以外的現實環境。也有一些項目,讓學生到真正的社會崗位,親身體驗工作的現實(而不是職業培訓)。
第四種情形:在學校以外學習。這裏指的,不是校外的補習學校,而是失學的兒童。筆者曾參與籌備在香港舉辦的”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2009),就接觸過印度一位女教師,在火車站開班,讓在流浪的孩子學習基本的生活技能,也讓他們有信心尋找自己的前途。在香港這樣的社會,也有中途輟學的青少年,他們如何學習?稍為年長,不通過學校而學習,由於電子平台的普及,就更加是一種普遍現象。
第五種情形,建設學習型的社區。上周末博鰲教育論壇的主題,就是關於教育的社區化。世界上已經有不少地方,作了很有意義的嘗試,把整個社區,建設成為一個學習社區。
港大建築系的同事,也曾經在內地設計一個學習型的社區,裏面的學校設施,已經融化在社區裏面。另一個出名的例子,是加拿大的綜合學習指標(Composite Learning Index),是根據UNESCO的學習四大支柱──學會生存、學會學習、學會實踐、學會共同生活──設計出一個指標體系,用來標誌一個城市的「學習化程度」,共17個領域,26個指標。例如:學生的解題能力、在職培訓的機會、每戶用在圖書館、博物館、現場表演藝術的支出……等等。
疫情衝擊 挑戰觀念
但是因為疫情,看到的卻是新的一面。在一個會上,香港的「翻轉教學協會」在一個港大與內地「教育三十人論壇」合辦的大型論壇上,首先提出的是在線上運作,「如何面對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引起了聽眾很大的興趣(當時境內外有4.5萬聽眾)。同一個會,江西寧都的教育局長,介紹了如何在疫情中,運用線上學習,讓學生有了新的學習興趣,也有了新的自信心;而這個縣,本來是一個貧困縣。筆者最近到過不少學校,也看到不少教師,在疫情之下,正面積極地讓學校出現新局面;而這些學校,有些因此轉弱為強,有些因此全校教師、師生更加團結,甚至有些從瀕臨倒閉的邊緣,而變得生氣勃勃。
筆者的觀察,這是因為疫情的衝擊,打破了舊的思維與規限,絕處逢生,反而帶來了新氣象。他們有了新的目標、新的途徑,反而摸索出新的教育意義。這就是教育的新常態。其意義,不可小覷。
由於學生知識增長的途徑不一樣了,學校的牆,正在消失。絕不是不要學校,而是學校的角色正在改變。學校教育的意義,會很不一樣;人們對學校的成敗優劣,也會開始有不同的觀念。學校的排序,將會很不一樣!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