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C,
你好嗎?看到你昨晚發給我的元朗地鐵站的新聞鏈接,我了解你做爲一個前媒體人悲憤的心情,我不知如何安慰你,也許我該告訴你我今天在聖彼得堡的所見所想。
今天一早,我去參加了在Tripadvisor上訂的這個城市行脚團。你也知道我到每一個城市都愛挑一個當地人搞的免費或付費的行脚團參加, 它能讓我以最快的方式大致了解這個城市的歷史,還有本地人才知道的一些花邊和故事。這個叫做Peter‘s City Tour at Petersburg在網站上評分非常高,我很多時候在Tripadvisor會看看其他遊客的評價,基本不會太撞板。
行程一開始,導遊帶我們轉了一個彎,馬上就在街角停了下來,對我們說:「你們大概都看過 《罪與罰》吧,這就是小説中主人公住的地方。」説實話,那一刻,我本來還有點沒睡夠,一下子全醒了。 沒想到這個以爲只是走走看看的行腳團是以俄羅斯最拷問世人靈魂的作家:杜斯杜耶夫斯基為起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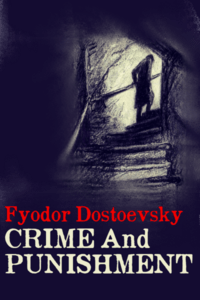
以杜斯杜耶夫斯基為行程起點
他手指的方向是這棟五層樓高的回字形建築拐角的一面牆,上端是杜斯杜耶夫斯基的黑鐵雕像,下方是一行俄文的大理石碑 : 「拉斯克尼科夫之家,彼得堡這塊土地上人物的悲劇命運由杜斯杜耶夫斯基創造,基於他對全人類激情地布道」。 拉斯克尼科夫是書中那個殺死了放高利貸老太的大學生,他雖只是一個虛構的人物,按照書中描述,就住在木匠胡同這棟樓五樓的一個狹小斗室中。 然而書成了經典,虛構的人物和住址恍如成了現實的一部分。

這個街區就是作家在小説中描述的當時聖彼得堡最貧窮最骯髒的區──乾草市場,無數最底層的人們住在這裏,妓院比比皆是,「街上熱得可怕,而且氣悶,擁擠不堪,到處都是石灰漿、腳手架、磚頭,灰塵,還有那種夏天的特殊臭氣。每個無法租一座別墅的彼得堡人都那麼熟悉的那種臭氣」。 如此真實和生動的描寫,是因爲當時窮困潦倒的作家就住在斜對面那棟粉紅色的公寓樓裏。 我們的導遊又指着運河的方向說,「其實作家在《罪與罰》所描述的每一條街,每一棟建築都是真實的,主人公就是沿着這條街走到運河邊,然後沿着運河走到那位高利貸老太的房子那裏。 」然後他又説: 「我們等一下也會走到那棟房子去。從這裏走過去,一共是730步。書中第一章就説他用不着走多遠;他甚至知道,從他那幢房子的大門出來要走多少步:整整730步…….有誰有興趣從這裏走過去數數看嗎? 」
「是的,是的,」人群中只有我傻瓜瓜地回應他: 「 730步!我記得!我想走喔!」 可惜,沒有其他人回應,導游聳聳肩,「那我就帶你們去集市吧。」
斯大林大清洗的歷史記錄
C,我的失望沒多久又被這位導遊的另一個分享給淹沒了。 從乾草市場的一個平民室内街市出來沒多久,走過陽光明媚的公園,他忽然又在一棟房子的牆外停下來,指着牆上那兩塊小小的金屬牌子問:「 你們知道這是什麽嗎?」 我們都搖搖頭,這時太陽已經開始熱烈起來,曬得大家有點暈暈的,誰都不知道他爲何突然要在這兒停下來。 「這是記錄上世紀三十年代斯大林大清洗中被逮捕或處死了的人名,在俄羅斯有一個這樣的NGO,叫做 Last Address, 他們專門找出大清洗中失蹤了的人被抓走時的住處,然後在住處外牆上釘上這塊牌子,記錄他/她的名字、何時被抓走,然後何時被處決。」
我當然知道殘酷的大清洗,但沒聽過這個NGO,於是打破沙鍋問到底,指着兩塊牌子問他:「那這兩位是誰?」「他們是一對夫婦,男的是老師,你看到他們被捕和死亡的年份差四年,那是因爲他們先被送去西伯利亞的監獄,幾年後在那裏被處決的,或者,都不用處決,凍死了或餓死了。你們一路走,可以再找找其他建築物外牆上的牌子,你們會發現有些被抓走和死亡就是同一天。 」導遊淡淡地答我。
好奇心上來了,我立即Google 了一番這個NGO( 是的,俄羅斯上得了Google 和Youtube),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也可以上這個網址https://www.poslednyadres.ru/ 看看。Last Address成立初衷就是為平凡人也立一塊紀念牌匾,組織的工作以「 一個名字,一個生命,一個標誌」 為座右銘,找出那些在斯大林大清洗運動中被逮捕的人,為他們釘一塊牌,記下他們的名字,讓後來的人都可以不忘記這一段歷史。
爲何平凡人不可以有紀念牌匾?
這個組織的起始在於問了一個問題: 爲何只有VIP 才有紀念牌匾? 平凡人呢? 爲何他們不可以有?這點上,他們有點像杜斯杜耶夫斯基:這位一生關注底層人民和為平凡人呐喊的作家,他在《罪與罰》中對所謂「平凡」和「不平凡」就有非常深刻的討論:
「不平凡的人有權利……也就是說不是有合法的權利,而是這種人有權利昧着良心去逾越……某些障礙,但只是為實行他自己的理想(有時對全人類來說也許是個救星)而有必要這樣做之下。
從遠古的時代起,到後來的莱喀古士、梭倫、穆罕默德和拿破崙等,他們無一例外都是罪犯,唯一的原因是由於他們都制定了新的法律,從而破壞了被社會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從祖先傳下來的古代法律。
人按照天性法則,大致上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人就是一種材料,他們大抵都是天生保守、循規蹈矩,活着必須服從而且樂意聽命於人。
第二類人,他們絕大多數都要求為着美好的未來而破壞現狀,他也能忍心踏過血泊──這要看理想的性質和規模。」
讀杜斯杜耶夫斯基的這段話,你大概也想到了中國人都知道的一句名言: 「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 拿《罪與罰》的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來説,因爲在赤貧邊緣掙扎多時,當他得知愛他的妹妹爲了要支持他而準備嫁給一個她根本不愛的人,他的良知終於敗在了他對社會不公的憤怒之下,他走了好幾次730步,掙扎再三之後,認定偉大的人物爲了自身理想和解救其他人,是可以跨越道德去犯罪的,最終舉起了斧子殺死了放高利貸的老太太。拉斯克尼科夫行兇前的心理鬥爭和行兇後的愧疚、恐懼、擔憂交織下的痛苦,構成了經典的對「罪」 的討論。 然而,你想想看,斯大林所發起的大清洗,光是1937至38年一年間,就無情處決了681,692人, 大清洗持續了近十年, 多少的家破人亡,人們從自己家中突然被克格勃逮捕,被嚴刑拷打,被折磨,幾十萬人最終被處決。 其實,那730步走向深淵的步子,也無非還是平凡人給自己設下的一個障礙,對所謂「 不平凡 」的人來説,去他的730步,該殺戮該處決,從來沒有覺得是罪。
C,我們的行程結束後已是下午3點,餓極了的我找了家涅瓦河邊的格魯吉亞餐廳坐了下來。 河對岸是列賓美術學院,餐廳旁邊則是當地最受歡迎的婚姻註冊處,連接兩對新人,和親友們從那裏步出,歡聲笑語中走到河邊去拍婚紗照。

《罪與罰》中的靈魂拷問和掙扎
那一刻我想起香港,這個我住了20多年並已深深愛上的地方,身邊多是平凡人,大概一直來只是希望生活如我現在看到的藍天下的新郎新娘一樣,平靜而幸福。 然而現在卻在面臨着如同《罪與罰》中的那種靈魂拷問和掙扎。
我並不是悲觀地想到這一點,我只是很無奈地一直在想杜斯杜耶夫斯基書中所描寫的那種「無路可走」,我只是還在被Last Address所震撼。 大多數平凡人,在這個所謂「互聯網新社運」時代,思考都可能獲罪,但所謂不平凡之人,他們依然在無情地踏過平凡人的血泊,他們依然無罪。人類歷史到今時今日,日光之下,從無新事。 我們不都該更深刻地了解有些「罪」是因爲無路可走,有些「罪」是無情的歷史中必然發生地?

我的信就寫到這兒吧,當你收到它的時候,我應該已經快回到香港了,我不知道接下來我們的這個城市還會發生什麽, 有些人看不到Last Address 今日能在這個前蘇維埃國家日光白白下存在的重大意義,有些人總是忘記了他們也不過是一隻鷄蛋而已,卻選擇了站在高牆一邊。
我明天會去杜斯杜耶夫斯基的故居和墓地,好好憑吊一下這位書寫和洞悉人類悲苦的偉大靈魂,或許還會從木匠胡同那兒再走到那運河邊的房子去,數一數是不是730步。
夏安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