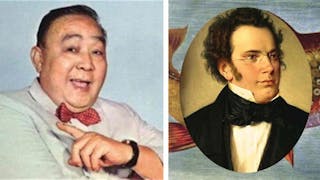東渡日本的蕭紅,曾經在寫給蕭軍的信中說:「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閒,經濟一點也不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是在籠子過的。」
難道這就是蕭紅的黃金時代?
筆者絕不敢苟同!
在愛與不愛之間:特立獨行的女性輓歌
蕭紅香消玉殞,引一眾才子仰天長歎。
聶紺弩憑吊:「何人繪得蕭紅影,望斷青天一縷霞。」
戴望舒口占:「走六小時寂寞的長途,到你頭邊放一束紅山茶,我等待着,長夜漫漫,你卻臥聽着海濤閒話。」
蕭軍哀歎:「生離死別已吞聲,緣結緣分兩自明!早有白頭吟約在,隴頭流水各西東。」
端木蕻良低吟:「生死相隔不相忘,落月滿屋樑,梅邊柳畔,呼蘭河也是瀟湘,洗去千年舊點,墨鏤斑竹新篁。惜燭不與魅爭光,篋劍自生芒,風霜歷盡情無限,山和水同一弦章。天涯海角非遠,銀河夜夜相望。」
可惜蕭紅在世之時,卻總是被拋棄、被傷害、被漠視。在愛情上,她是「棄女」,有「花自飄零水自流」的無奈,卻也是「烈女」,有「花開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任性,直面「比青杏還酸」的宿命。為了愛,她奮不顧身,永不放棄,最終客死異鄉,永不瞑目。蕭紅之死,何嘗不是對男權社會的控訴,對婦女解放的反思?

自由主義者的黃金時代
蕭紅的黃金時代,其實早在呼蘭河畔的後花園已經悄然萌芽:「花開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鳥飛了,就像鳥上天了似的。蟲子叫了,就像蟲子在說話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無限的本領,要做什麼,就做什麼。要怎麼樣,就怎麼樣。都是自由的。倭瓜願意爬上架就爬上架,願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黃瓜願意開一個謊花,就開一個謊花,願意結一個黃瓜,就結一個黃瓜。若都不願意,就是一個黃瓜也不結,一朵花也不開,也沒有人問它。玉米願意長多高就長多高,它若願意長上天去,也沒有人管。蝴蝶隨意的飛,一會從牆頭上飛來一對黃蝴蝶,一會又從牆頭上飛走了一個白蝴蝶。它們是從誰家來的?又飛到誰家去?」
那是《生死場》對於死生之間的「力透紙背」,以及女性作品「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的「明麗和新鮮」;
那是《呼蘭河傳》作為「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淒婉的歌謠」的經典存在;
那是童真文字的塗鴉、自由天性的囈語,以及袒露在苦難肉體之外,無邪靈魂的吟唱。
當電影《黃金時代》的畫外音悠然響起:
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裏,我不願意去;
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裏,我不願意去;
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的世界裏,我不願意去。
我只願蓬勃生活在此時此刻,
無所謂去哪,無所謂見誰。
那些我將要去的地方,都是我從未謀面的故鄉;
那些我將要見的人,都會成為我的朋友。
以前是以前,現在是現在。
我不能選擇。
怎麼生,怎麼死;
但我能決定。
怎麼愛,怎麼活。
這是我要的自由,
我的
黃金時代。
筆者如遭雷擊,深信不疑!
本系列文章:
北國娜拉——蕭紅的流浪者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