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關子尹教授前於中大通識沙龍講座主講「希臘悲劇與哀樂人生」。演講中有關「悲劇與哲學」、「希臘神話與天神觀」的內容於前一篇有述,「尼采論悲劇的誕生」、「命運與命限」、「悲劇對現代人的啟示」等部分摘錄如下:
酒神精神
談到「悲劇的誕生」,「誕生」二字本身當然是個比喻。尼采說,悲劇來自一個很原始的世界觀,「戴奧尼索士精神」,就是Dionysian Spirit,酒神的精神。所謂酒神精神,也可說是希臘人最原始的一些對生命的態度和看法。
這種態度如果要用一個字代表,那就是drukenness,醉。
為什麼?因為一醉千愁解。探究生命本身,我們在最底層可以發現充滿苦難,充滿挑戰,充滿種種挫折。尼采在這方面借用了酒神的故事來闡述,從酒神的坎坷身世開始講述。

酒神在前世已經受苦──他的前身角神Zagreos(匝格瑞俄斯)被人碎屍萬段;到了今世,他的母親懷胎時(母親是與宙斯相愛的凡間公主),因受情敵誤導,逼天神以真身與她相會,但天神真身是一束雷電,雷電也就這樣劈死了酒神的母親,劈開了她的孕肚,令酒神在胎兒時期還沒有成長健全就出生了。天神宙斯只能把他藏在臀間來養育,他後來又曾經意外跌進海裏,諸如此類,由此知道他的身世很可憐。
一些故事提到酒神的隨從一次在酒醉後洩露了「天機」──希臘人認為天神有過人的稟賦,但一旦醉酒,就失去法力,很容易為人所逼而屈服。國王逼他說出人世間最美好的事物是什麼,一開始他不肯說,最終卻禁不住說出了秘密。
他說:「人根本沒有條件追求最美好的事物。最美好的事物就是根本不要生於世上。」
他接着對國王說:「既然生於世上,人只可以爭取次好,次好是什麼呢?那就是一旦生而為人,不幸生而為人,盡快去死。」(眾笑)
他的智慧就是這樣直白,赤裸呈現。
日神精神
但是,Dionysian Spirit的智慧並不僅限於這麼悲觀的世界觀。而且,希臘人漸漸開化出一種「日神精神」(Apollonian Spirit,阿波羅精神)。
阿波羅精神就是太陽神的精神,阿波羅出身「根正苗紅」,僅次於神王宙斯。他不像酒神掌管酒,而是掌管文化、建築、藝術等等,尼采就曾說過,這些「人文世界所建立的事物」用一個字來說,那就是夢。
意思就是,製造種種美的事物,比如音樂、比如建築、比例、measures,令人在世上無論生活得多受挑戰、淒慘,卻不會有片刻餘暇,(苦厄)可以透過欣賞這些藝術稍為得到紓緩。
大家都知道──凡做過夢的人都知道一個簡單的道理,那就是凡是作夢也會夢醒,醒來後問題真的解決了嗎? 解決不了的話,我們又回到原點上了。這種精神在某種意義下是一種容衷,但是沒有解決希臘人所看到的、生命底層的悲情和感觸。

兩者合而為一
因此,雖然戴奧尼索士精神和阿波羅精神這兩種精神彼此激盪,但是得不到真正的安頓,直到終於產生了辯證的綜合──提到辯證,剛剛我們說到尼采受到黑格爾的影響──所以這裏辯證的綜合意思就是:一方面我們看到酒神精神控訴生命的苦楚,但另一方面又受到日神精神的滋潤,這樣一直到兩者終於合而為一,而且不是簡單的混合,而是像一種經由兩種物質發生化學反應而產生的化合物一樣,令酒神精神昇華(transfigured)為一種悲劇精神,蛻變成為一種另類的生命態度。

一言以蔽之,生命沒錯充滿苦難,但在刻苦的生存處境裏,只要懂得怎樣去活,活得其所,仍然能活得很美。
這種美再不是日神精神說的那種美,而是後來美學所說的“The Sublime”,一種壯美,生活受到激揚而生出勇氣,造就一種動態的美、動態的昇華。
第一要素:嘲諷感
我們可以做一個成分分析(componential analysis),分析(這種精神)當中的成素。我認為尼采分析出兩種很有意義的元素,第一種元素中文可以叫做「嘲諷感」,英文則翻譯成“absurd”,翻譯得不錯,但是很不充分。
什麼是absurd?如果你看德文的原文,那就是Lächerlichkeit。
這來自一個字:lachen,也就是「笑」。lächerlich就是「可笑」,「可笑的事」指的就是那些荒謬之事,例如我們的生命遭嘗橫逆,Lächerlichkeit就指出當中的荒謬感。德文原文並不只是像英文翻譯裏“absurd”這個字那樣、從負面情緒來將事情了解為「荒謬」這麼簡單。我早期曾將它譯為「荒謬感」,後來覺得不恰當,改掉了。
「嘲諷感」(Lächerlichkeit)這個字指出我們要先將荒謬、不合理的事情當成可笑的事物──無理可喻的遭逢令我們憤怒到某個程度後,要懂得一笑置之;用一個distantiate(抽離)的方法拋開荒謬,以一種不齒的態度直視不幸,將它視為一則笑話。
希臘人看到這是人類擺脫不幸詛咒的一個契機。如果你不懂用這樣的態度來看事物,只用一種負面的情緒處理,則會令自己愈加泥足深陷,不能自拔,承受不幸之中更大的不幸,自己為自身不幸加上一腳。
如果一個人遭遇不幸卻無動於中,這是很難想像的。我們遇到種種不合理、荒謬的事,每個人也會憤怒、不忿,這是人之常情。但是,不忿、憤怒之後若只能繼續用深深不忿的態度來處理,最後最受苦的就是自己。
(簡報中)這句引文很精彩:
什麼是嘲諷?這裏嘲諷是「嘲諷作為荒謬底可憎的藝術性的釋放」(“das Komische als die künstlerische Entladung vom Ekel des Absurden”/“the comic as artistic discharge of disgust of the absurd”),指的是將荒謬中可憎可厭惡的東西用藝術的方式釋放出來──“The comic as artistic discharge”.
要注意一件事,德文中對「嘲諷感」的這句解釋中已經出現absurd一字,荒謬之事(absurdity)就是我們要discharge(藉藝術釋放厭惡情感)的對象,所以如果用absurd來翻譯Lächerlichkeit,這裏就會出現重複,解釋Lächerlichkeit時重複用同一個字表達兩個不同概念。

第二要素:激越感
然後就是激越感(Erhabenheit),我們看德文裏面,這haben就是「提起」、「提起」的意思。如果我們將不幸的事情用藝術來轉化,那麼你就得以跳脫,不會沉下去,能夠升上來。
以嘲諷自己不幸的角度來看待事物,就能免於被負面情緒綑綁,終於能釋放自己。
「將怖慄用藝術的方式馴服」這句解釋激越感的話說得很好,讓人了解到所謂悲劇精神和力量所指的是什麼。尼采後來曾說,藉着嘲諷與激越,希臘悲劇成為一種「藝術、 ……救人的巫師、治病的專家」。
希臘悲劇的精神裏有一種comic的元素,這說明了深層的悲劇、最上乘的悲劇有一種(叫人)「發笑」的元素,所以最上乘的悲劇跟最上乘的喜劇其實可以合流,因為都是用藝術的方式處理生命中種種遭遇,只不過手段有差別,次序有不同。
合流之後,就有所謂「悲喜劇」(Tragicomedy),最經典的就是《唐吉軻德》(Don Quijote)。
探討命運與命限
最後,希臘悲劇對現代人有什麼啟示呢?首先,我們要理解希臘悲劇跟莎劇等等都有很多的共同點,但是也有差別。莎劇最強調的是人性的缺陷等等,希臘悲劇雖然有時候處理這些課題,但最重要的焦點在於人類如何面對人生的遭逢,那就是是existential crisis(存在主義危機)的問題,所謂命運的問題。
所謂命運,是什麼一回事?我們先來看命運的「命」字,中文的「命」字跟西方(希臘文還有德文),都不約而同有一個元素,就是涉及擬人化或者人格化的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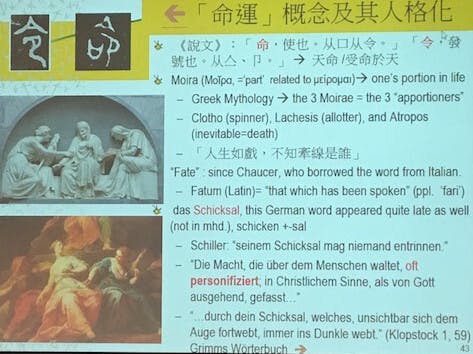
「命」字最初跟「令」在古語可以相通,《說文》對「命」的解釋是「命,使也」,使你做一些事情,「從口,從令」,那就是使喚別人做某件事。
那麼,「令」就是「發號也」,《說文》這樣解釋,我們可以從古文字看到,令字的上部是個倒轉的口,這跟飲字食字的口一樣;下面有一個人跪坐着,被另外一個他者向他說三道四,差使他要做某件事,所以當中有一個「他力」的意思。
人格化的命運之神
而在希臘神話中,Moirae(複數)就是指命運三神,可參圖中白色石像,指的是希臘神話裏面三個分配者。這個字的意思,是把屬於你的那一份、你的portion(命定的那一份)分給你,讓你得到自己的那一份。

這個三個天神來配給──他們未必叫做天神──第一個Clotho(“the Spinner”,紡織者)負責紡織那條(承載命運的)紡線,Lachesis(“the Apportioner of Lots”,分配者)代表派送命運,Altropos(“She who cannot be turned”,「不可抗拒的」,引申為死亡)則是終止分配。
恰巧,中文裏談及命運也有「牽線」一說,所以,可以說中西文化都有將「命運」擬人化的傾向,有以上這樣的依據。
在英文,在中世紀作家Chaucer(喬叟)以後才會用“fate”一字代表命運,而且這字借自意大利語,本來是“Fatum”,即“that which has been spoken”(指一些已經頒布的話語),來源自拉丁語。
東方西方談及命運,很多民族的字裏不約而同帶有隱含有「他力」這回事,但是各個民族也嘗試重新設想命運這回事。命運者,與其想像為由人操控分派,不如想像跟天志無關;將人世遭逢跟這種人格化的意志unlink(切割開來),視之為偶然發生,這就是另外一種思路。
中國傳統中,所謂「命」當然有外力的方面,但是也有一些經典的講法如下:
在《禮記》裏,子夏問什麼是三無私,孔子就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天不會蓋着誰有所偏私,地則不會有偏見、只托住你不托着我。另外,《呂氏春秋》也提到「四時無私行」。荀子也有提到:「天論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等等,由此見得,命運該如何去理解非常值得我們深思。
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嘗試理解fortune這個字。
命運女神的輪子與非人格化的命運
一開始,主辦單位問我這個講座的英文題目應該是什麼,當初的選擇不是現在這個英文題目,但我提議不如叫“Tragedy and Human Fortune”,可能好一點。
Fortuna是神話中的命運女神。她的attribute(屬性)就是拿着一個轉輪,由於轉輪可以攪動,本來在上的會變回在下,在下面的也會升上去,可以這樣週而復始,轉輪可以向左攪動、向右攪動,或者往回轉動,任命運女神怎麼攪動也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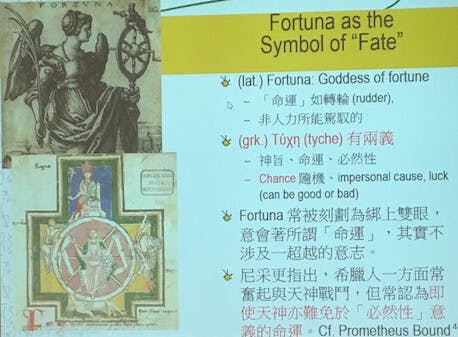
一方面,你可以將此看為命運女神的作為,但是你也可以將它看為非人力駕馭的。大家可以看看這個轉輪,輪子上一個人成為君王,另一個變成地痞,負責轉動輪子的Fotuna由一條布條蒙眼,跟正義女神相像。
在希臘文裏,這有兩個意思,一方面可以指涉及天志,但另一方面可以指純粹的機緣。而且,希臘人認為天神也不是為所欲為的,而是在一定的必然性之下要屈服,要遵從自然命運的秩序。比如說,普羅米修斯之縛中,他詛咒宙斯也快要被人disown、趕下寶座。即使是希臘人,也認為天神不能贏過necessity(必然),也會受到一些難以駕馭的法則所支配。尤其是我們一將命運非人格化之後,將它跟外在意志脫鈎,人生於世上儘管還是有得失順逆,但不必再耿耿於懷、在意是否有天意加之於自己。
所謂的「命」在這樣的情況下,只不過是人力所無法完全駕馭的種種限制,有種種難以理解的原因,不用再歸咎於超越的意志來解釋。
這個意義的的「命」我們可以稱為命限。以上分析了希臘悲劇探討命運的問題,發現我們很容易設想命運跟外在力量支配有關,但是分析到最後,我們不需要再這樣理解。
面對命限的思索
今天,我們要悲劇再發生一定的意義的時候,大概也不能夠好像古代希臘人那樣相信有些天神在「整古做怪」,就算這樣說出來也無法取信於人。但是,只要我們能將人生遭逢理解為命限,那已經足夠。不過,命限也是要去面對的,不如意的事情總要面對。
了解了命限這個議題後,我們人生存在世,免不了好生惡死,趨吉避凶,但是我們對一切的得失成敗榮辱也能有比較深刻的反省。
關於生死,我們與其只懂得好生惡死,我們還可以「捨生取義」(《孟子》)。
得失──《莊子.秋水》教我們「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
成敗──「千年成敗俱塵土」是文天祥的詩句;
榮辱──大家都聽過《老子》13章有一句話是「寵辱若驚」。但是,近年復旦大學的裘錫圭先生寫了文章,指出這是長久以來的誤解;他們發現那不是「驚」而是應是「寵辱若榮(䁝)」,這樣才能跟下句的「貴大患若身」意思打通;意思就是,我們面對屈辱只需好像面對榮譽那樣肯定它、接受它。這種是很高的智慧。
禍福──人人都求福避禍,但《老子》教我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貧富──「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
希臘悲劇對現代人的啟示
悲劇讓我們得到什麼教益?我會說,這讓我們在「義」、「命」二者之間取得一個「破折號」──有機會可以借勞思光先生一個很重要的講法「義命分立」來解說。這裏的命不再是命運,指的是命限,指種種無法由人主宰的外在限制和遭逢;義則是人類價值判斷的一種自由──儘管我們受到種種約束和限制,我們仍能自己肯定自己行為。這個破折號讓我們在實踐的限制之內得到最大的自由。
義命二者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有種種關聯,但應該分為兩個領域──分為兩個領域並不代表兩者完全無關,在種種命的約束之下,仍然有義的空間,有多少義就行多少義。
這可說是希臘悲劇給我們很有價值的一個機緣,讓我們思考這些關鍵議題:人類的禍福遭逢、生存世上應有的行止。
「希臘悲劇與哀樂人生」系列二之二
延伸閱讀:
〈關子尹:希臘悲劇與哀樂人生──聽尼采談天神之惡與悲劇之美〉
講者簡介
關子尹教授,德國波洪魯爾大學哲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任教逾三十載,現為哲學系榮休教授,兼人文電算研究中心主任。歷任美國杜鏗大學、瑞士聯邦理工學院、英國劍橋大學、國立臺灣大學等校訪問學人,現為德國柏林自由大學訪問教授,曾以中、英,及德文發表專著及論文多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