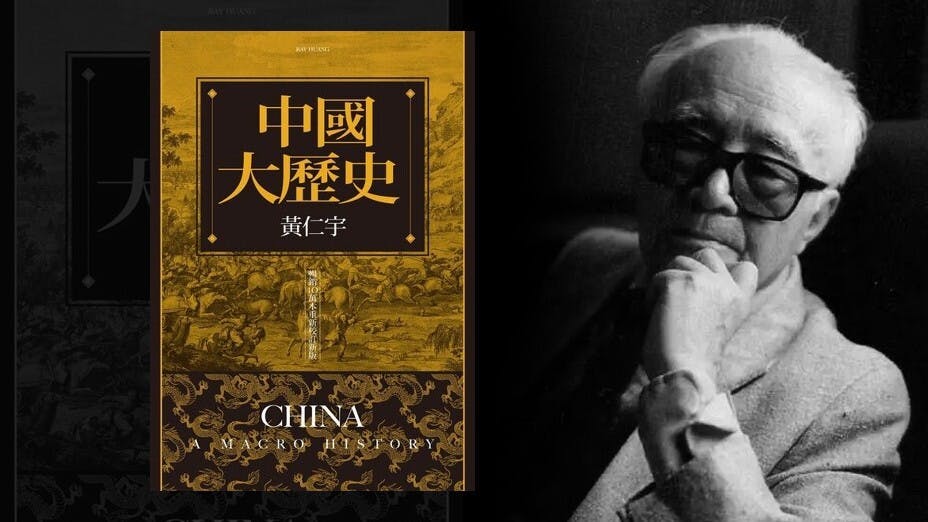《中國大歷史》是史學家黃仁宇所作,乃黃氏體現其大歷史觀的專著。此書既從經濟學、地理學的角度分析中國歷史,又用歐洲歷史與中國歷史互相比較,可謂厚積薄發,知識面廣。此書不只是寫給學者專家看的,而是為廣大民眾而寫的歷史著作。由於此書深入淺出,論點新穎,用300多頁的文字,將中國數千年的歷史用宏觀的視角呈現在讀者面前,因而廣受矚目,引起人們的共鳴。
嶄新方式詮釋歷史
黃仁宇突破了過去「教條化的歷史概念,使人們可以從一種嶄新的角度去認識和詮釋歷史。黃仁宇在書中並沒有使用那些舊有名詞,如「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等,並且指出將清朝說成是「資本主義萌芽」的階段,實無意義,等於說不稱一個小孩為「小孩」,而勉強叫他做「預備成人」。他質疑「封建社會」一類概念,打破了史學的「範式思維」,在中國思想解放運動中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更為重要的是,黃氏主張應該壓縮卷帙浩繁的歷史資料。「我們應當廣泛的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和西歐史與美國史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才談得上進一步的研究。」
黃仁宇之所以運用歸納法,是由於中國歷史資料浩如煙海,若不將其高度壓縮,則會有「毫無體系」、「互相矛盾」之感。而且,在歷史上,有許多「技術上的變數」,對歷史的發展,可說是微不足道,把這些東西加進去,反會使得讀者惘然無緒。因此使用歸納法就是要把握主體,摒棄雜蕪。如今學術界普遍重視微觀研究和繁瑣考據,黃氏的「大歷史觀」無疑為歷史研究另闢蹊徑。黃氏強調研究歷史要抓大放小,因為「大歷史」不僅是一種治史的眼界,也是史學家應有的胸懷。
還有,黃仁宇力圖從地理、氣候和經濟等角度,探討中國歷史的進程,打破了「治亂興亡」、「朝代興亡」的思維定式,例如他認為秦朝的統一終止了青銅時代,開創了中央集權的統治,大業所成是自然力量的驅使,包括易於耕種的纖細黃土和豐沛雨量的季候風。
黃氏又運用比較法研究歷史。他使用今天的概念與歷史上的觀念比較,從而指出某一歷史事件的特性,並發表了作者的議論。例如他在敍述宋代王安石變法時,運用今日的財政、金融管理觀念去作比較,於是得出王安石的改革基本思想「與現代讀者近,反而與他同時人物遠」的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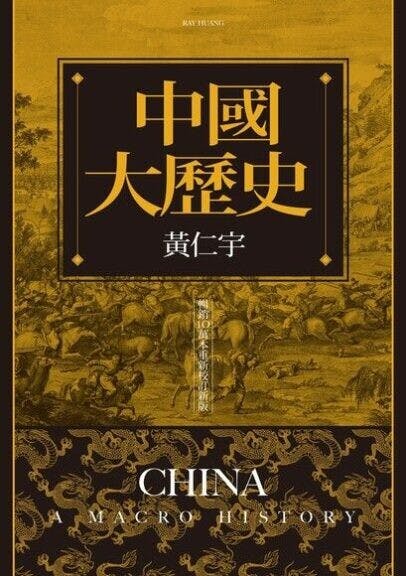
通過中國歷史 助學生安身立命
另外,從研究的目的去劃分,歷史學大體上可以分為純研究和求務實兩大派。前者標榜避免現代人的價值侵入研究,力求還歷史的本來面目;而後者則相反,為解決當代人的問題去研究歷史。黃氏的研究顯然屬於後者,他質疑學習歷史是否能夠學以致用:
「而一旦授有學位,作為人師,在美國學子之前講解中國歷史,深覺得不能照教科書朗誦,尤其每次復習與考試之後,不免捫心自問:他們或她們須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與他們日後立身處世有何用場?難道他們或她們必須知道與Han Fei Tzu(韓非子)同受業者有Li Si(李斯)其人,他曾鼓勵Shih-huang-ti(秦始皇)焚書,後又為宦官Chao Kao(趙高)所構殺?Empress Wu(女皇武則天)的一生事蹟僅是『穢亂春宮』?對我的學生講,除了用她與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凱薩琳二世)比較,或與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比較,這段知識尚有何實用之處?」
他希望通過講述中國歷史,幫助學生「安身立命」。他把現代社會提出的重要問題放在首位,透過研究不同題材,為現代人尋求歷史的答案。這也是此書的寫作目的。 然而,「大歷史」強調用較長時段來觀察歷史,注重事物之間的因果關係,只是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歷史的一種方法,我們決不能將其視作能夠解釋一切的萬應靈丹,如在歷史研究中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和人口決定論一樣,它們都有其合理性,但亦有其局限性,故絕不能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更不可以偏概全。例如秦能統一六國,氣候因素只是諸種因素之一,但不能片面強調此點,而忽視其他因素,例如秦自商鞅變法以後,法度嚴明,生產力大有發展,而六國君主為求苟安,割地賂秦,終為其分化瓦解,逐一消滅。
重經濟輕理念 排拒意識形態
黃氏的「大歷史觀」重經濟輕理念,排拒意識形態,界定一個國家和地區落後與現代的準則是用「數位」而非道德治理。以一個世紀或朝代為單元,用歸納法綜合之。既然遠觀百年的發展,只看最後的總賬,對整段期間內個別的人和事大可一笑泯恩仇。
黃氏這種歷史觀的缺點是過分強調經濟的作用,忽視道德和人情在推動中國歷史進程中的重要作用,更為重要的是,這種過於「宏觀」的治史方法,有以百姓為芻狗的非人性化之弊。以此視角觀之,則人類遭受的種種苦難,不過是大歷史締造過程中的偏差,就如天然災害之不可避免。日常的矛盾衝突更是歷史長河中的微波,即使導致人命財產的嚴重損失,也轉眼即逝,無關緊要。黃氏斷言人類的行動在大範圍內展開,只循着若干因果關係,不能被各人的意願所左右,更難因着他道德上的希望而遷就。 這種輕視人命,忽視統治者責任的歷史觀實在值得商榷。
在「歷史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前提下,人類所能為力的相當有限,這無疑否定了人類行為對歷史發展的影響,這就容易抹殺了歷史偉人所起的關鍵作用和傑出貢獻了。 所謂「歷史的長期合理性」是否確實存在也是一大疑問。到底要多久,才算是「長期」?在「歷史的合理性」終於展現之前,到底還要付出多少犧牲?
因為「歷史的長期合理性」不在乎時間長短,只以「最後」的結果衡量歷史的功過是非,而那所謂「最後」,是可以不斷延長的。只要「最後」達成了某個目標,不論付出多少代價,耗費了多少光陰,從長期來看,都算是合理的。這種觀點容易落入「目標只要高尚,手段可以不計」的誤區。
對中國文化理解的偏頗
此外,黃氏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也有偏頗之處,如他認為《紅樓夢》帶着唯美的色彩,過度地追懷過去,過於感情化,過於女性味;《儒林外史》極端諷刺,卻好像一部論文集。在歷史研究中如此評論文學作品,未免有些不倫不類。眾所周知,《紅樓夢》既然是一部古典小說名著,自然要飽含感情,而且它以描寫女性人物為主,故不存在過於「感情化」和「女性味」的問題。至於《儒林外史》的文學價值也決不會低到像一部論文集,如它描寫范進中舉就把科舉制度對讀書人的戕害刻劃得維肖維妙。
此外,他在談及明初歷史時,說朱元璋的文官組織充其量也不過8000人,薪給之低,即依中國的標準看來,也算特殊,因為朱元璋自己以農民而為天子,在他的心目中,官僚之為人民公僕,就必定要照字義上成為公僕。在類似情形之下所有稱為「吏」者,也另成一系統,尚且是官僚組織之下層。多數的吏員是奉召服務,一般不給酬,如果他們有薪給的話,最多亦不過維持家室的食米而已。
誠然,明朝官員的薪俸是中國歷史上極低的,但說朱元璋視政府官員為「人民公僕」,則絕不可能。因為當時顯然沒有「公僕」的概念,官吏是老百姓的「父母官」,他們不是「為民服務」,而是「為民作主」官與民的關係是尊卑分明的。明朝官俸為歷代最薄,導致官吏往往憑藉權勢壓榨人民,吏治相當腐敗。此外,他將中國歷代王朝劃分成三個帝國,這不但抹殺了不同朝代之間的差異,而且中國歷代從來沒有帝國之概念。中國歷代王朝只是以天朝上國自居,要求諸國俯首稱臣,確立宗藩關係,對這些藩屬國並無領土野心,與那些侵略、瓜分弱國,擁有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可等量齊觀。
總括而言,此書最大的貢獻,在於打破傳統史家以人物和斷代為中心的研究方法,首倡以「大歷史」的宏觀視角觀察歷史,並且用經濟學、地緣政治學等跨學科切入研究中國史,提出了「數目字管理」等新概念,對此應予肯定。但其缺點是過分重視技術層面的因素,在摒棄意識形態之餘,將道德和人情都拋棄了,這是不應該的。畢竟,歷史是人類構成的,如果研究歷史不着眼於如何增進人類的幸福,批判禍國殃民的統治者和苛政,則歷史研究必然失去其應有的意義。
作者簡介:
馮天樂,台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香港浸會大學中國文學、語言及文化文學碩士(優異)、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中國文化研究院「燦爛的中國文明」專題作者、香港電台節目《講東講西》客席主持、《協進之聲》編委。馮博士曾主持香港電台節目《中國點點點:閱讀中國》、新城電台節目《大中華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