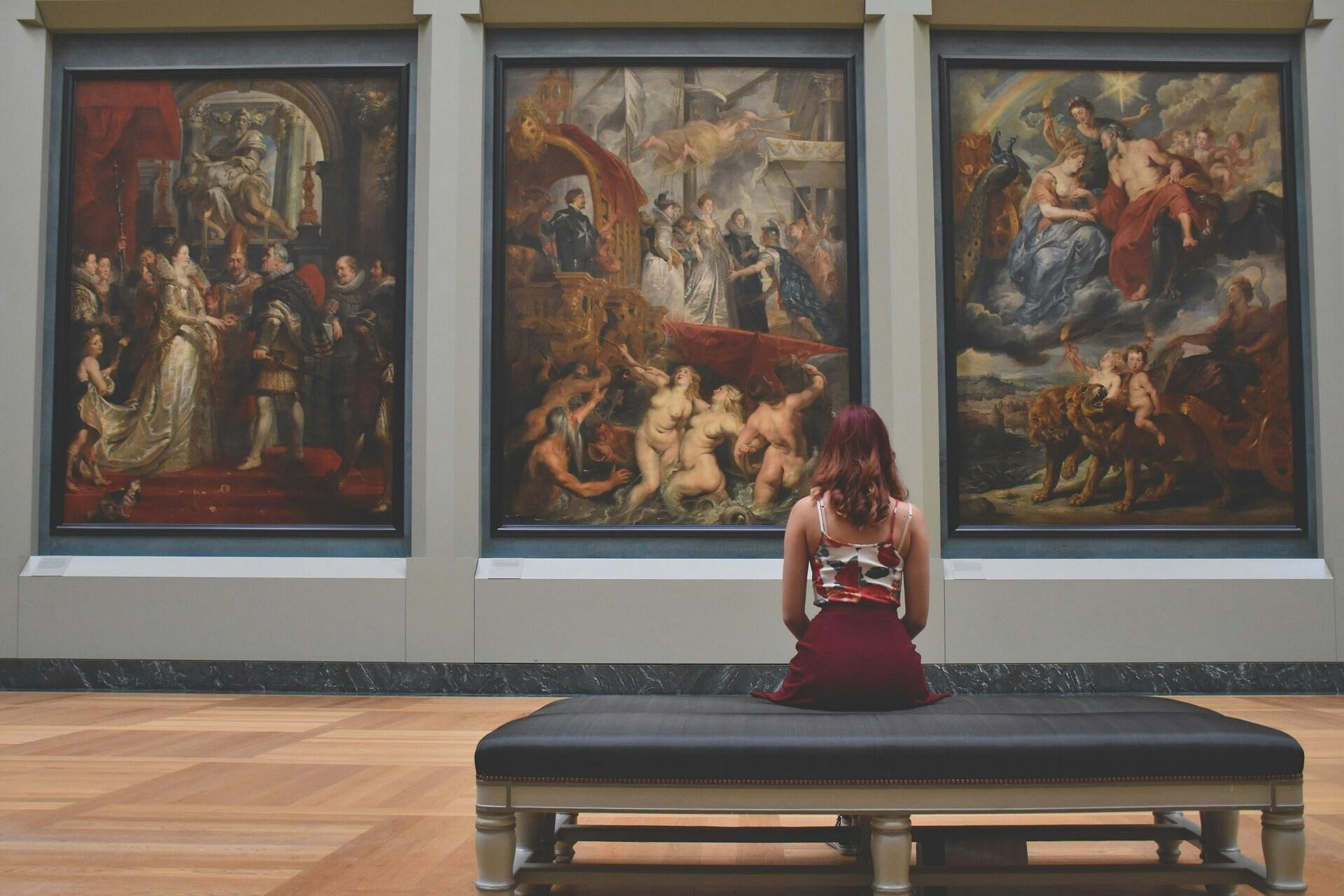這個全球各國都被逼關閉國境的時刻,旅行突然成了不可能的任務。各地的美術館都在Google地圖上顯示暫停營業的狀態,成了最遙不可及的他方。雖然很多美術館都慷概大方地將自家藏品搬到了網上,和Google的合作更將網上看展變成了虛擬實景體驗。然而,我還是多麼懷念那些去美術館看藝術品的美好時光啊!
前些天,北島在他的公眾號上轉發了王安憶去年的一篇文章──《朝聖》,開篇就是一句:「去博物館看名畫名作,很像朝聖」,這句話,莫名地就撩動了我這麼多年在世界各地參觀美術館的種種回憶。
第一次朝聖
和大部分人一樣,從小最向往、最想去的博物館應該一定是羅浮宮。因此我人生的第一次藝術朝聖毫無懸念地設定在了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館。
比王安憶的經歷稍好一些,我去的時候不是暑假,沒有在《蒙娜麗莎的微笑》面前被擠在裏三層、外三層的外圍。讓我驚異的是這幅畫的尺寸和它完全不起眼的第一印象,簡直感覺自己從小到大被欺騙了好多年,到底這幅畫有啥好的地方?當時還不是智能手機年代,這個展廳裏也不准用相機,所以我先是在這幅畫前站了一會兒,仔仔細細把這張畫好好端詳了一遍,想把它裝到我的記憶中。然後我又退到一邊讓別的觀眾能仔細觀賞,在外圍遠遠靜默地站了一刻。腦海裏奔騰着我從小看這張畫介紹的種種神秘之處:金字塔結構啦,利用視覺的錯覺啦……blablabla。最後我自己也微笑了,鬆了一口氣,像是朝聖的人抵達了目的地放下背負的行李般的無比輕鬆。 我知道,我並不喜歡這張畫,而我是幸運的,第一次朝聖已經悟到真正愛看藝術,試着不要在美術館按圖索驥,不要被大師或大作聲名所困,尋找自己的藝術喜好才是最重要的。
既然人在巴黎,實在有太多可朝聖的美術館和名作等待着我。想看印象派,去奧賽;想看現代藝術,去蓬皮杜。結果,那一次在巴黎真正的「朝聖」是去了兩位藝術家的舊居:羅丹美術館和莫奈在巴黎郊區的故居。羅丹,這位雕塑大師,拿今日的社會標準來審,那一定是「渣男中的戰鬥機」。然而在左岸的這座美術館參觀者眾,要進去還真不容易。那時候還沒有網上預約這回事,一早在巴黎的細雨中走去排隊。只記得派籌還沒開始,排的地方又不像是真正的門口,搞得我心裏毛毛的,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排錯隊。最終進去了,還得順序魚貫而入,按路線和時間段參觀。百般辛苦,卻真是不虛此行,那是人生視覺上最強烈的一次衝擊。羅丹作品中的力量讓那些雕像如同活着一樣的震撼,怪不得當時有民眾看了他逼真的作品被嚇到,謠傳他的作品是在真人身上直接灌上泥漿倒模而來。我流連在他美得不可方物的《吻》和《手》這兩尊雕塑前不捨離去,卻被無情的管理員催促着趕緊離開室内去花園參觀。
花園裏也放置着很多作品,包括著名的《巴爾扎克像》和《雨果像》。然而,我的眼睛被六米高的《地獄之門》深深地吸引了過去,這是羅丹40歳開始,死時仍覺得不滿意的巨作,它以但丁的《神曲》中的地獄為主題,足足構思創作了30多年。這個大型雕塑作品全黑,安置在花園的花崗岩墻上,彷彿推門就能進入另一個黑暗的世界一般。 坐在門中間正上方的正是著名的《思想者》。將他放置在地獄之門中,我們才會了解為何思想者的身體和面容扭曲,因為他正在地獄入口,同情地俯看在地獄中受苦的人類。他苦思卻不能解答人類的種種問題,陷入極度痛苦和無盡的思索之中。看此作品,你會真正明白為何羅丹一生不羈卻又不愧是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他擁有的想像和技藝簡直就是超人,是人類能創造出的思想藝術文化中最燦爛和輝煌的一部分。

之後一天去莫奈的故居則是完全不同的經歷,也許是巴黎市區值得看的地方實在太多,遊客沒時間花大半天倒騰公共交通工具來到這個小村落。除了我這種骨灰級藝術粉,前去的遊客不多。當時還是窮學生一枚,坐了火車又轉坐公車轉折到了故居,卻被告知上午人數已滿,還得坐等下午才放人進去。然而,這趟旅程辛苦的朝聖比預期還要值得,莫奈畫中的睡蓮、小橋、楊柳、光影,莫奈的世界根本就在他的花園中。那次朝聖之後,無論在紐約MOMA看莫奈,還是在日本國立新美術館看莫奈,我的腦海裏會一下子閃回到他的秘密花園中。初夏花園的氣味,傍晚植物散發的氣味和光影餘輝,都和他的畫一起成為我藝術記憶庫中最深刻的一篇。
巴黎之後,我的全世界藝術朝聖之旅正式啟程,也堅定了我一個信念:觀賞藝術品最好是直接找機會看原作,而原作又最好不是在美術館看,而是去藝術家的故居或創作有關聯之處。比如要朝聖梵高,阿姆斯特丹的梵高美術館的下一站就一定是南下法國,在阿爾勒的陽光下,才能理解他作品中那明亮的黃色,被風吹到螺旋狀的樹木和深藍色的星空。
朝聖米開朗基羅
和王安憶一樣,要説得真正符合「朝聖」這兩個字的藝術之旅肯定是去梵蒂岡美術館看米開朗琪羅的《創世紀》。哪怕你不是天主教教徒,仰望西斯廷禮拜堂内這幅名作大概都有點向上帝朝拜的味道。那進舘前長到看不到尾巴的隊伍,進舘之後的單向移動的壓抑,都讓你未到西斯廷禮拜堂,就已有十足的儀式感。我那次是帶家裏孩子和老人一起去,排隊的時候把老人孩子都安置在咖啡舘。然而,即使如此,他們都還是被那幾個小時的等待累到了,進了西斯廷,沒仰望幾眼《創世紀》,就全坐在僅有的兩張長椅上,再不肯動彈。當我興奮地指着一幕幕熟悉的畫面,特別是《創造亞當》中的上帝和亞當手指接觸的瞬間,他們都只是敷衍地應和了我幾句,他們實在是累壞了。那是一場對體力極高要求的藝術朝聖,估計我的家人對畫的印象並不深,但對當時的疲累大概到今日還心有餘悸。
然而,我這個真正的米開朗琪羅粉絲,並沒被那次朝聖嚇到,只要有他雕塑的地方,還是跑着排着都要去朝聖。其中印象最深的當屬在佛羅倫斯美術學院朝聖《大衛像》。佛羅倫斯典型的窄巷子裏,因為要先預約登記,一早來排隊的人並不多。可明明到了開門時間,卻每次只放小貓兩三隻進去,隊伍愈來愈長,門衛慢條斯理的,完全不理我們在巷子裏的悶熱。經常有不知情況的遊客見到我們在排隊就也走來排,一會兒和我們聊起來,才知道自己沒預約,排了也沒用,於是又去和門衛探詢,得到的結果當然沒有驚喜。我們一開始還會提醒一下新來者:預約了嗎?一兩小時下來,就都有點麻木了。長久的等待後,終於,我們也被請進藝術學院那道大門了。
這家鼎鼎大名的美術學院是全世界第一所美術學院,校友包括達芬奇、米開朗琪羅和伽利略等多位大師。然而在藏品方面,學院除了這尊《大衛像》其實沒有其他藝術品。就如同米蘭的恩寵聖母教堂只有一幅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一樣,獨沽一味,卻獨步天下。不管票價的貴,也不管排隊的長,每年還是上百萬人湧來朝聖。再次證明這世上,真的是偉大的作品,一件就夠。

《大衛像》被放置在學院其中一個廳的穹頂下,大約有五六米高,因為是大理石,既沒有特別的保護措施,也用不上一般博物館的恆溫設施。參觀者可以走到最近去細細觀賞細節,側着看,腿上鮮活的肌肉,生動的脚趾;仰望,則是俊美的臉,漂亮的捲髮,線條柔和地不像是石頭質地。然後慢慢退遠了看整體,完全想像不出來,為何一塊堅硬的石材會變成了如此生動的胴體。也完全想像不了,為何米開朗琪羅能用石材雕刻出體内血管下彷彿血液奔騰的感覺。 《大衛像》就像是被神靈幻化成了石頭而已,彷彿隨時會醒來一般。
每年成千上萬的遊客到了佛羅倫斯,大部分卻都止步於領主廣場的那座小複製品,卻錯過了真正的《大衛像》原作。對藝術領悟的一點點醍醐灌頂,往往始於對一件原作的震撼。那怕是普通遊客,如果有機會進到佛羅倫斯這條窄巷子裏的美術學院,也許他的醫術朝聖之路也會從此開始。我們和藝術的緣份其實一直在那裏,和世間其他的緣份一樣,需要的只是一次偶遇,一次打動心弦。
現代藝術的朝聖
對現代藝術的朝聖其實比看那些文藝復興巨匠、印象派大師的作品還要艱難。因為很多人不喜歡現代藝術,常常覺得看不懂,看不懂的意識下又如何找到朝聖之心?殊不知,自我認知所不及的區域正是應該仔細研究,打開心懷領略的部分,這和朝聖的另一層意義:在未知中探索,最後心悅誠服其實非常相近。
我對現代藝術的朝聖是挺偶然開始的,不是在巴黎的蓬皮杜,也不是在紐約的MOMA,而是在威尼斯的「佩琪·古根海姆美術館」。很多年前在威尼斯,坐河上TAXI在大運河經過一座米白色的獨特建築和庭院,隱約中還見到庭院的雕塑,心動之下就在下一站下了船。過了一座木橋沿河邊摸過去,轉眼看到一座頗有味道的宅子,這就是紐約古根海姆美術館在威尼斯的分舘,也是古根海姆家族的著名成員–佩琪·古根海姆的故居。
進了庭院,真是一處妙地。前院和對着運河的後院都放置着一些雕塑,室内和長廊佈置有低調的奢華,則懸掛着佩琪收集的眾多現代藝術家的作品。客廳裏掛着一幅只有墨點和色彩的兩米多高的畫作,我一下子就被俘虜了。這正是波洛克的Enchanted Forest。那一刻,你並不需要知道藝術家在畫什麼,卻被畫中的激情和表現力直接擊倒了。那是完全不同於看米開朗琪羅的感覺,你感覺不是崇拜,而是被燃燒,被舞動,在心裏被激起了一些莫名感動的東西。當然,這裏還有達達主義大師杜尚那張《火車上憂傷的年輕人》。此畫和他另一張名作《下樓的裸女》齊名。以前看糟糕的印刷品所犯的嘀咕到了這張原作前立即一掃而空,因為杜尚想要表現的人隨運動的物體所表現的動態,簡直像是要奪畫而出一般,而他從這些畫中所掀起的對傳統繪畫的視角的革命更讓人激動。最近挺紅的一套英國電視劇──《平凡人》中有一幕就在這幅畫前拍攝,男主角是窮人家的孩子,終於拿了大學全額獎學金,經濟稍寬鬆一些之後來歐洲旅行,女主角提議他來威尼斯古根海姆看這張畫,認為他可以在這幅畫前發呆大半天。想起來,我當時大概也發呆了至少一小時。

這個威尼斯大運河邊的美術館是進入現代藝術世界的浪漫通道,沒有一般美術館的廳堂之感,處處見到佩琪的一生足跡和她個人情感及喜好。難懂的現代藝術,停留在畫冊上的各位現代藝術家在她的家裏都鮮活了起來,親近得彷彿可以觸摸到一般。
王安憶在《朝聖》中提到,日本文化學者加藤周一先生認為:「古典藝術的輝煌在於有一個他者,就是神,現代藝術則以自我為出發,現代藝術家每一個人都在發揮個人風格,結果是,彼此相像。」對此評論,我有點不敢苟同。我倒認為現代藝術面貌各異,藝術家各自找尋和創造不同風格,從無相像之感。也許加藤的意思是在一個他者的塑造中,古典藝術家容易從比較大的角度去創造傑作,而現代藝術比較局限於自身的情感和宣泄,因此格局較小,面目不會如前者般那麼大江大海。然而,我大概是一位對個人更有興趣的觀者,所以對現代藝術家更有認同和親近之感,而對古典藝術的廟堂之作反而有些疏離。比如我極其喜愛亨利摩爾,對我來説,他是羅丹之後另一個神般的存在,他的雕塑沒有細看讓人起雞皮疙瘩的驚人細節,只有渾然的塊面,抽象而淳樸的形體,儼然是更接近自然,更有哲學意味,更有象徵美學的藝術,對他的朝聖因此有了更接近生命本質的思考。我曾在東京箱根雕塑公園的一片雪地上對着積雪的亨利摩爾雕塑發愣,頗有面對神靈之感,絕對是真正意義上的「朝聖」。
中國藝術的朝聖
中國藝術方面,稱得上帶着朝聖心情去看的大概只有這幾處:台北故宮、敦煌、雲門幾處石窟、大英博物館和大都會美術館。當然世界各地不時也有極高水準的中國藝術展覽,去參觀就更帶着朝聖之心。比如去年日本國立東京博物館的《顔真卿特展》。展覽梳理了中國各朝代的書法大家及原作,台北故宮更借出了已經十多年未展出的天下行書第二之《祭姪文稿》。我千里迢迢地趕去東京,因為深知錯過,不知又要等到何時才能再見這些中國書法品的絕品。我到的那天,來接我的朋友就告知我昨天剛接了姜文夫婦,陪他們直接去了看展覽。當時就想:哦,原來像我一樣來朝聖的傻瓜還真不少。

筆者之前已經寫過《顔真卿特展》朝聖之行,在此就不再贅述,還是藉機寫寫幾年前的敦煌朝聖吧。我們一行人因為是深度參觀,經申請,也交了特別的附加費用,觀賞了幾個平常不向遊客開放的洞窟。這些石窟中或雕像,或壁畫,都是精品。進入洞窟不可以有強烈照明,我們只能憑講解員的微弱電筒,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些美麗的造型和線條,如何喜歡都好,也不能長時間在洞内,因為我們呼出的二氧化碳都會改變洞窟内的濕度和溫度,對這些千年的壁畫有不好的影響。如此這般進了254號窟,有一位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員正在做數據測繪工作,開了一盞紫外線燈。即使在那樣的光線下,還是看到了一幅和其他幾個石窟完全不同風格,讓人震撼的壁畫。254是敦煌石窟中的早期石窟,屬於北魏時期。壁畫上是著名的佛教經變圖──《薩埵太子捨身飼虎圖》,描繪薩埵太子捨身飼虎的故事。北魏在唐之前,因西域的交往頻繁,壁畫中人物的塑造深受健陀羅藝術影響,造型線條簡潔抽象。色彩方面,則因年代久遠,礦物顔色剝落,壁畫上只留下了褐色的底色、黑色的線條及一些殘留的青綠色,如此反而令整個畫面有一種原始而強烈的視覺。這張壁畫在構圖上也是非常的現代,它並未以一般壁畫以故事發展順序繪製,比如常用的卷軸式敘事法,在畫面中有明確的時間線,而是以故事的幾個高潮點作為畫面主體,整個故事融合在一起,將時間和空間放在同一平面上,畫師大概希望觀者自己在畫面中判斷和尋找故事的軌跡,從而產生出更豐富的精神體驗,到達更深層次的覺悟。這完全是現代繪畫的構圖想法,與畢加索反映戰爭的名作──《格爾尼卡》非常相似。
在敦煌,研究歷史的看到歷史,研究民俗的看到當年民俗,研究音樂的看到各種樂器,研究佛教的則看到恆河星沙般的佛教寶藏,研究藝術的更敬畏於如此豐盛而大美的藝術作品。這個經歷了幾朝幾代的石窟群,包含了不同的藝術風格,反映了不同的時代,真的是一處研究歷史,社會和藝術的寶庫,而我們的朝聖其實只是窺見了它神秘面紗下的一小角而已,這樣的觀藝行程大概是朝聖中的「朝聖」,五體投地,心生敬畏。
中國古代藝術還有很多不朽之作,卻因戰火和一些歷史原因,流落全世界各處。到大都會博物館的會驚嘆於那張宏偉的《藥師經變》壁畫,到大英博物館的會被三層樓高的隋代阿彌陀佛像所震撼。不管如何,就帶着對藝術朝聖的心情而去,看看這些在歷史中有名字或無名的藝術家們所創造的極緻的美,他們的思想和精神似乎穿越時間,隱隱約約,穿越而來。而我們如王安憶的慨嘆一樣:「一旦走進美術館,滿壁的畫,撲面而來,你簡直招架不了,什麼美術史、個人史全抛在腦後……你就只管看好了。」
歷史已然,不可知的殘酷未來正在迎面呼嘯而來。藝術大概是將來唯一幾艘能普渡我們人類的方舟之一。疫情中,光是想着那些美好的藝術品就像已經得到了慰藉。然而,我還是祈禱着能踏上藝術朝聖之旅的日子快快到來。
附錄:疫情後推薦朝聖的五家美術館
疫情讓人敬畏生命和無常,困坐愁城,心中大概會暢想疫情後一定要為自己做點什麼。藝術朝聖在你計劃中嗎?
主流的美術館人頭濟濟,過了一個廳又到一個廳,不僅是個體力活,而且看者其實是眼花繚亂,基本上也就是沿着展館地圖上標注的大師作品按順序走完算數。這種朝聖只有敬畏,卻少了真正和這些藝術品交流的可能性。一兩趟下來,既沒真正朝聖到藝術,卻添了很多對美術館的畏懼。因此,筆者要在這裏推薦幾家能讓人朝聖而又容易找到焦點的美術館,它們都不在太主流的旅遊地點,都不大,旅途都稍有曲折,然而它們都值得成為你開始藝術朝聖的第一站。
- 丹麥哥本哈根/路易斯安那現代藝術美術館
漫步在這座被稱為最美的現代藝術美術館,朝聖賈科美蒂雕塑 - 日本滋賀/美秀博物館
尋訪桃花源般,朝聖貝聿銘的建築設計和館内大量健陀羅藝術收藏品 - 西班牙李嘉特港/達利故居博物館
徜徉在達利的奇思妙想中 - 日本直島/地中美術館
朝聖安藤忠雄的建築之餘,朝聖神殿般陳設的Walter De Maria作品 -《Time/Timeless/No Time》 - 法國尼斯/馬蒂斯美術館
遇見住在蔚藍海岸的馬蒂斯,感受野獸派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