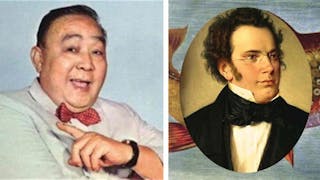旅日作家李長聲日前在香港書展開講,題目是「村上春樹如果不進京,可能不會寫小說」。這位作家僑居日本凡30年,有人譽為繼周作人後「文化知日第一人」;內地女作家章詒和形容他「寫飲酒、寫捕鯨、寫街景、寫浮世繪、寫辭世歌,也是精彩、精緻又精闢。敍事,娓娓動聽;狀物,不厭其煩;寫人,道地白描功夫」。(〈他那支筆是怎麼練的?〉)他接受本社訪問時,不諱言早年從台灣人的著作了解日本,並談論日本人趨之若鶩的「司馬(遼太郎)史觀」,見解獨到。
李長聲自言,出國前,他對所謂「公害小說」比較感興趣。「其實中國的環境保護起步並不晚,上世紀70年代,各地紛紛成立環保局、環保研究所、監測站,但是很可惜,只是多了吃飯的大鍋和當官的交椅,環境狀況卻每況愈下,以至於今。」
「我和我日本老闆喝酒,他問我想讀什麼書,我說我想讀《苦海淨土》。這是一本揭露水俁病問題的著作,(話說)熊本縣水俁市一帶工廠向海裏排放廢水,還有水銀,造成一種公害病,叫作水俁病。患者手腳麻痺,有語言障礙,不是衰弱致死,就是留下後遺症。書的作者叫石牟禮道子,本來是一位家庭婦女,在醫院遇見了這種疾病的患者,她就以探望的方式進行採訪,用了40年的時間寫了三部曲,(今年)90歲去世了。我的日本老闆就是熊本人,聽說我想讀那本書,他面露驚異之色,說:「那本書可不好讀。」我當時以為他指的是有關工業污染的一些知識,但是我從圖書館借來了這本書之後,一看就傻眼了。本來日語水平就不高,這本書用的是九州方言來寫!這是我初到日本時有關讀書的一個小故事。」
方言為何不見了?
李長聲的小故事道出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現在讀日本文學,特別是小說,不大會讀到方言。「這不是因為日本作家不使用方言,而是被我們的譯者給抹殺了。譬如我們讀夏目漱石的小說,明白如話,一點都沒有100年前的感覺,這是拜譯者所賜。但日本人讀夏目漱石,可能比我們讀魯迅還難,夏目漱石的文體屬於『漢文系統』。有一位日本評論家推薦漢字入門書,就列舉了夏目漱石的《虞美人草》。他寫《草枕》前,重讀了《楚辭》,因此小說滿紙漢字詞;我們傻傻地看字面,都覺得美,卻難為了當今假名(ひらがな)橫行的日本年輕人。潄石是美文家,魯迅說他『以想像豐富,文詞精美見稱』,我們從譯本固能領略其想象的豐富,但『文詞精美』卻成了虛言。」
東京盛產作家?
「日本文學有個特點,那就是東京出身的作家非常多,例如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三島由紀夫,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作家都是東京人。外地出生的人,例如川端康成(大阪)、大江健三郎(四國愛媛縣)、村上春樹(生在京都,長在兵庫縣),但是他們也都集中在東京。以前日本有自然主義的作家,都是從其他地方來到東京的;而反自然主義的作家則幾乎都是東京人,比如森鷗外、夏目漱石、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芥川龍之介。像一直住在大阪的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這樣的作家不是很多。總之,日本文學好像是東京的地方產業。不像中國,不僅是北京,哪裏都有作家群,比如說香港、上海,還有台北,都有可以跟北京作家群相抗衡的作家群。」
東京話是村上春樹第二語言
「(京都伏見區出生的)村上春樹是關西(指京都、大阪、神戶一帶)人,如果他18歲沒有來到東京讀早稻田大學,而是一直在關西,或許就不會寫小說。這裏有一個語言問題。村上在關西長大,說的是關西話。但來到東京生活了七八年,就會想:不能用第二語言東京話寫小說嗎?大概村上春樹就在東京新宿區神宮球場看棒球時這麼想的。村上春樹使用標準語,小說幾乎感受不到地方性。人們又會問:怎麼不說關西話呢?」
「2014年,村上春樹把6個短篇出了一個合集《沒有女人的男人們》,其中有一篇叫〈昨天〉,這個篇名也(像《挪威的森林》那樣)取自披頭四一首有名的歌曲(Yesterday)。小說中的「我」姓谷村,是關西人,到東京唸早稻田大學文學系,完全不說關西話,這正是村上本人的履歷,所以這個短篇就像寫他自己的『私小說』。大二時,谷村在打工的地方認識了木樽,二人同是20歲。木樽是東京人,卻能說一口完美的關西腔,泡澡時愛用關西腔唱披頭四的歌Yesterday,但歌詞是他自己編的。……不過翻看海峽兩岸出版的譯本,都沒有翻譯出木樽說話的關西腔。〈昨天〉討論了關西話的問題,譬如關西人到東京說東京話是常識,但東京人在東京說關西腔卻是偏執……文化的價值應該是相等的,東京話並不比關西話高貴,但但明治維新以來,東京話大體上成為日語表現的基準……」
李長聲指出,村上春樹在其他文章寫到他不說關西話的理由,大致如下:「我來到東京,完全不說關西話,有幾個理由:我到高中畢業,一直都用關西話,一次都沒講過東京的語言;但是到東京一個多月,我就發現自己很自然,很流暢地讀着、講着這種語言,吃了一驚。我自己沒有發現,或許本來就是變色龍的性格,也可能語言的音感比別人好。總之,說自己是關西人,周圍也沒有誰相信。還有,就是想變成和以前不同的人,這是我不用關西話的一大理由。把以前一筆勾銷,在東京開始新生活……」就是說,要在東京造就一個全新的自己,有藉着環境改變自己的意圖。
李長聲認為,日本文學出了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樹,改變了以往只是以日本讀者為對象的地方文學的創作態度,而是以全世界的讀者為對象,這種文學態度也促使語言不能侷限於地方,必須使用標準語,進而翻譯成世界各地的語言,走向世界。村上春樹從高中開始讀英語書,養成用英語讀書的習慣;從關西話到東京話,再到英語,多元化的語言環境造成了他的文學風格。

中國人和美國人創造的日本神話
除了公開講座外,李長聲還接受本社記者訪問。一開始,記者以為這位去國30年的「知日」作家會像日本人那樣,說幾句話就會點頭鞠躬,不料這位東北大漢原來性格豪爽,說普通話還帶有濃濃的東北口音。
李長聲自言,1988年7月他離開中國,至今在日本生活了30年,他覺得日本人喜歡精緻,性格仔細,人際關係比較緊張,沒有中國人的「大氣」;但中國人的「大氣」發展下去便成了「馬馬虎虎」,然而,「中國人也必須馬馬虎虎,你看這偌大的一個國家,還有56個民族,不馬馬虎虎沒法團結呀!日本是個小國,他們還自稱是單一民族,仔細一點沒有關係。」這是他的看法。
記者:「長久以來,中國人對日本人是否很好奇?」
李長聲:「是啊!最早給日本人創造神話的是中國人,『神山』、『蓬萊』都是中國人想像出來的。然而二戰後給日本製造神話的是美國人,『日本第一』什麼的,但美國人製造日本神話,心態上跟中國人不同。中國人憧憬的『扶桑』是『日出之處』,是在虛無飄渺間追求的『仙山』;美國人就像(美國佔領軍司令)麥克阿瑟說的:『雖然都是戰敗,但兩國完全不同,德國就像一個40歲左右的成年人,而日本還是一個12歲的孩子。』傳統上歐美對日本都是看低的。因此,當美國人製造『日本第一』的神話時,就像是看到『熊孩子』忽然長大了的心態。」
記者:「讀了您去年出版的《送誰一池溫泉水:李長聲日本妙譚集》,覺得您真的是在全方位觀察日本,不是信口開河。」
李長聲:「我在日本生活,一定會遇到一些不懂的地方,很想去了解一下,我的方法主要是讀書,同一題目讀幾本書,因為不太相信通過談話便可以真正了解。例如我經常跟日本朋友喝酒,問他們一些問題,他們都會隨便的說;正如日本人問我京劇,我也會說一大通京劇,但其實我並沒有進戲院看過京劇,但中國人對京劇是有常識的呀!你如果說未看過,不懂京劇,日本人便會覺得奇怪;正如你問日本人能劇、藝伎,日本人都能說得頭頭是道,但又有幾人真正懂得能劇和藝伎文化呢?」
記者:「您覺得海峽兩岸對日本人的觀察有何不同?」
李長聲:「中國人從唐代開始跟日本人交往,歷代也出現不少了解日本的人物,例如清末的黃遵憲(寫過《日本國志》)、民國的戴季陶、周作人等等,但中國出現出國潮是80年代以後的事,內地中國人對日本人的認識恰恰在中間數十年出現了斷層,也就是說,台灣人在60、70年代對日本人的認識。我到日本後,開始讀台灣人寫日本的書,例如崔萬秋、李嘉等人的著作,可以說,我對日本人的觀察,受他們的影響很大──當然,我讀他們寫的,主要是談文化的部分,與政治無關。我認為,像李嘉作為中央社駐日記者,對日本的觀察主要是從中國作為『戰勝國』的角度出發。80年代開始,中國人對日本的看法,主要是從友好角度出發,強調『絕大部分日本人民是好的』。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都經常接見日本友人。因此,中國人沒有打敗日本的感覺,只有『打敗一小撮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感覺。我覺得,80年代中國人寫日本人,沒有超過前輩周作人和李嘉的。在這以後,中國人寫日本人的文章,我基本上已沒有讀,因為別人看到的我也看到了。」
「政治的事我不懂,但我覺得現代中日關係基本都是政治上的,不是文化上的。從地緣上看,兩國距離太近,發展起來的文化都是互相竸爭的,除非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否則,「友好」便只是一個詞兒,一個美好願望罷了。郭沫若說中日「兩千年友好」,只是一廂情願,事實上唐朝以來,兩國就多番兵戎相見,不打的時候,就是閉關鎖國,誰也不理睬誰。日本所謂的「遣唐使」,到中國來搬文化、寶物、佛經,對「友好」又能有多大作用?」
記者:「故鄉對您是什麼概念?」
李長聲:「父母在就是故鄉,父母都不在了,對故鄉也就不大在意了。或許這就是我可以在日本活得比較自在的原因吧!」
「文革時,我屬於『逍遙派』,不參加『革命』,也不當反革命,這種閒散的心態一直存在着,到日本以後,這種心態擴大,就變成完全的自由了。我不是日本人,沒有選舉權,也沒有被選舉權,不會角逐首相大位,也不炒股票,這樣就更自由了。」
司馬遼太郎史觀不足取
記者:「中國作家有在日本受歡迎的嗎?您怎麼看在中國受歡迎的日本作家?」
李長聲:「中國作家基本上沒有在日本很紅的,以前80年代因為中日友好,有中國作品翻譯成日文推介給日本人,近年也少了。中國作家的作品日本人也看不懂;其次,歐美流行的東西,日本人很快就模仿過來,村上春樹就是模仿美國小說的大家,中國作家一般不擅長模仿。至於在中國受歡迎的日本作家,在日本也很受歡迎,村上春樹、東野圭吾、渡邊淳一就是表表者。」
「不過,日本作家若要靠稿費過活,只會愈寫愈糟糕,有些作家是先約好電視台寫腳本(劇本)再動筆;有些則同時在幾個報刊連載小說,這樣,文學性難免會差些,再者,得過『芥川奬』之類有影響力的作家,多到大學當教授,拿固定工資,寫文章反而成了副業。只有極少數的流行作家,完全可靠稿費和版稅過活。因此,先前有記者問我對村上春村《暗殺騎士團長》的意見,我說我沒有讀過,我不是文學評論家,作家的作品沒有必要全部讀過。」
記者:「您說過在日本寫武士小說的作家,學歷都比較低,這是為什麼?」
李長聲:「這是過去的現象,例如吉川英治、山本周五郎,甚至後來寫推理小說的松本清張,都只有小學程度。一方面,那時候不太講究學歷,另一方面,那時候小學就像私塾一樣,培養作家已經足夠。到後來時代改變了,很多日本作家是學外語的……(記者:「司馬遼太郎不是寫過《新選組血風錄》嗎?」)那是早期作品,後來司馬遼太郎得了直木獎,便改寫歷史小說了。」
「司馬遼太郎的歴史小說涉及所謂『司馬史觀』,就是認為明治時期都是明亮的、特別好的,大家就像攀上坡道看雲彩(《坂の上の雲》)一樣,昭和以後打了敗仗,便是不好的,這便是『司馬史觀』的基本精神。司馬遼太郎沒有活在明治時代,卻肯定那個時代;夏目漱石活在明治時代,但他對日本所謂『近代化』(西化)持否定態度──過於模仿西方只有死路一條。司馬遼太郎把日俄戰爭視為『衛國戰爭』,是要防止俄國南下,這種史觀是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