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樂評人吳贛伯先生於香港進入21世紀的始肇年頭,發願為香港上世紀的中國音樂史做一個以斷代史為體例的整理和總結,寫成《二十世紀香港中樂史稿》(以下簡稱《史稿》)。為完成《史稿》一書,作者不惜走遍坊間,訪故尋源,翻查舊典檔案,網羅資料,忘憂忘食,其銳意為香港中樂歷史立言的宏願,實在令人敬佩。
年前返港,得吳先生以宏編相贈,囑咐閱後投書片言隻語,同為香港中樂事業捐獻力量。有感其誠,雖然自知對香港中樂的歷史認識有限,也只好以管椎之見,略進蕪言。本文題為管評,採取天馬行空式的縱筆點評,謬發誑語,立論自然難言公允。隨意敷陳,志在拋磚引玉,期待各方鴻碩的指正。
綱舉目張,條理分明
《史稿》全書近27萬字,洋洋灑灑,把香港上世紀100年內中樂發展的綿衍歲月盡收筐囊之內,不失為一部以時代資料彙編為經緯的鉅著。通篇為零碎的史料疏理成妝,編列為史,為日後有興趣探究香港中樂發展史的朋友提供大量參考材料,實在功不可沒。
《史稿》全書分上、下兩篇。上篇按既有文獻資料,羅列整理20世紀上半葉香港中樂發展的足跡,把流行一時的不同類別、型態的民族音樂,分成獨立章節鋪陳歷史資料,闡釋其承傳流播的背景,把上世紀前期香港中樂醖釀萌芽的重要人物和活動,裁剪分案,以大標題和小標目突顯輕重從屬的關係,舉重若輕,意圖把這個時期的中樂生態一網打盡。這種提綱挈領以展示歷史重點和發展沿革的編寫方式,非常適合史學論文的撰寫手法,可見作者對編輯史書的認識和功力,已臻閑熟自如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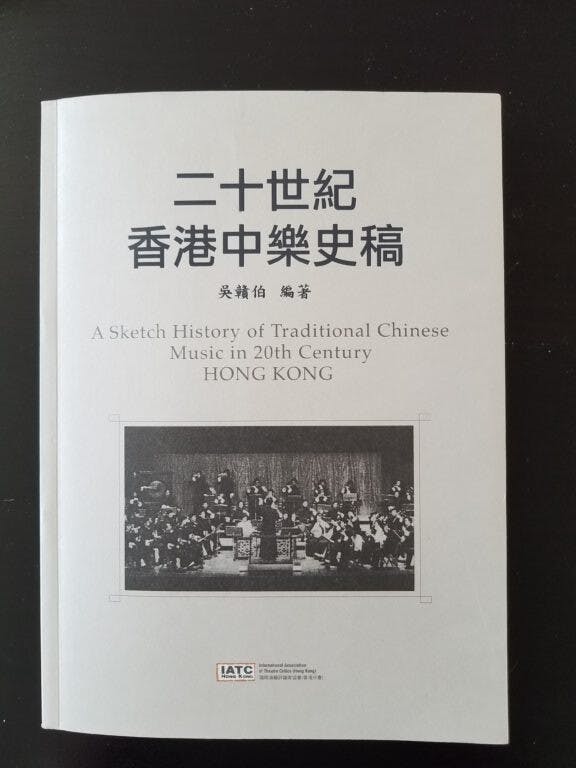
以樂種為經,以人物為緯
上篇第一章談漢民族傳統音樂在香港的流播和發展,以樂種為經,圖文兼備,資料性強。第二章談粵樂在香港的發展,以人物為緯,敘述性廣。由於20世紀粵樂在香港蔚然成風,有關粵樂的推動者和愛好者不絕於路,留下研究粵樂的資料相當豐富。《史稿》作者花了不少功夫搜集、轉載和整理了有關的資料,以代表人物的生卒為序,縷述香港粵樂發展的不同時期,條理清晰,脈絡分明,收一目了然之效。
稍感不足的是上篇資料對於香港本地鄉土音樂所涉較少。除木魚、板眼(能否獨立成科,存疑)、龍舟、粵謳、蜑家漁歌外,諸如客家山歌、圍頭民謠、福佬山歌可算是香港原住民的傳統音樂,每年不論祭祖祀神、春秋廟會、以至鄉事盛宴,佳節歡歌,都離不開這類擊筑狂歌的音樂生活。傳統的小型伴奏,主要是使用鑼鼓、二弦、凸胡、三弦、竹簫等五項樂器。這類源自本土,流行新界圍頭客家的原住民音樂,應與粵曲、潮樂以至北調南侵的中原音樂在上世紀的香港音樂史上佔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論影響力,甚至要比衛仲樂的香港之行更為重要,值得以獨有專章詳加闡述,以補坊間治香港中樂發展史的不足。當然,若著書之先早已把香港專業中樂團體(特別是交響化的樂團)的出現看成香港中樂發展史的沿革主流,則這一大堆民間土謠未受重視,就是正常不過的。但若持守兼收並蓄的客觀原則,或許更容易取得突破性的發現。
破竹建嶺,願境恢宏
治史不能忽略史論,中國傳統史學有別於西方,由漢代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開始就奠定了中國史論的楷模。所謂「春秋史筆」、「一字褒貶」、「撥亂反正」、「寓主意於客位」,成為中國史學的金針。其精粹在於通過縷述搜集所得的材料,確立是非成敗,得失正誤,讓讀者通過歷史發展的真像衡量有關人、事的功過,從而總結和啟示未來發展的應有方向。
此書定名為《史稿》而非《史料彙編》,顯見作者有意在此書中透過所搜集的音樂資料,達到分析和評價歷史興衰流變的目的。《史稿》取名似有步武前賢音樂史家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和張世彬《中國音樂史論述稿》的謙遜虛懷。書的扉頁和底頁之摺幅,作者特意以大號的字體寫出著書願境。扉頁銘句:「一個只會向前看不會向後看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民族。因為,一個民族不清楚自己的來路,就不可能明白自己的去路。」底頁銘句:「在中國音樂發展的過程中,以洋為重的所謂中西結合,我們得到的只不過是並不時髦的包裝,而失去的則是中國人在文化上的尊嚴。」這兩則擲地有聲的金句誠然標示着作者意欲通過歷史資料表揚過去100年間曾為香港中樂篳路藍縷的達人佳話,也有勇氣針貶香港中樂發展的失衡和流弊。豪情壯語,令人深惟而端出無盡的期盼。
評彈港中,着墨較多
下篇該是全書的重點,第一章作者集中闡述洋式管弦化(吳大江稱之為交響化)的民間中樂團隊由50年代開始,如何被界定為「初釀」、「發展」、「確立」三個不同的時期,不斷趨歸成熟,哺育「香港中樂團」(下簡稱為「港中」)的誕生。若從歷史發展的先後序次而言,此說仍可理解;但若冠上「初釀」、「發展」、「確立」三個標題,就立即變成「港中」的「生活史」,早已認定民間的音樂組織和一切音樂活動都以促成「港中」的成立為最大使命。這種預設的隱性命題,是否成立?會否矮化民間各懷願境和理想的中樂團隊的存在價值,着實有商榷的餘地。「港中」的成立在歷史上是「偶然性」的產物還是「必然性」的結果?它成立後,對原來的已遍地開花,爭妍鬥麗的業餘樂隊所造成的衝擊實際上起了什麼影響?對香港整個中樂生態產生怎樣的變化?為何香港的業餘樂團未能出現台灣現象,在第一個專業國樂團「台北市立國樂團」之外,接連有「實驗國樂團」、「高雄市國樂團」、「台南市立民族管弦樂團」等等的專業樂團不斷孳生,反而要在苦撐苦扎的困境下逆境自強?這與香港政府獨尊「港中」、一團獨大的政策有沒有關係?「港中」經過70年代的蜜月期,由80年代中至90年代中,曾經出現長時間的蕭條不景,上座率低見三、四成,曲不高而和者寡,這種不尋常的現象,落在具批判精神的史筆下,應該可以總結出一些原因。
為港中斷代,推吳大江為分嶺
第二章兩節分列「港中」的發展為兩大階段:一是吳大江時期,二是後吳大江時期(包括吳以後的總監或指揮關迺忠、夏飛雲、石信之、閰惠昌)。吳大江為創團總監,其建樹已受肯定,的確可以立為專章。唯繼後的總監亦各有建樹,其中尤以關迺忠和閰惠昌表現更見突出,關氏任期雖短,但才華出眾,憑着一首又一首的織體豐富、意象恢宏的新作品,迅速把「港中」上提到一個光茫四射的平台,足以媲美任何海內外的中樂團而毫不遜色(不過,《史稿》一書引用「港中」團員和某些樂評人對關氏的微言,以及台灣報章對「港中」的一些偏頗言論,對關氏的評價持相當保留的態度)。而繼吳大江之後任期最長的總監閰惠昌,以不斷貼近時尚的策略,為「港中」爭取最大的知名度,其業績也不能少覷。若把關、夏、石、閰四人全納入後吳大江時期,至少對這兩位卓有成績的總監有欠公允。平情而論,在吳大江之後,另立關迺忠時期和閰惠昌時期,也許並不為過。
論史以質不以量。談吳大江時期,指其建樹在於建立三大制度。作者對「確立樂師考核制度」的評論算是中肯,優厚的薪酬待遇的確能對樂團的穩定性發揮一定的作用。不過,考之於全世界的專業樂團,莫不如是,吳大江此一建樹實在難言創舉。其二是「客席指揮制度」,這制度也是因襲陳腔,設立主、客席指揮制度遍現於西方管弦樂團,唯一分別是專業樂團請來的客席指揮大多是卓有成就的專業指揮,作用是為樂團提升演奏視野和能力,而由吳大江以還,「港中」所邀請的客席指揮有不少非以指揮為專業,邀請對象多半是首演新曲的作曲家,以及較活躍樂界的友好,指揮能力有限,客席制度流為酬酢聯誼的手段,團員既未能通過指揮的啟導而提升樂曲的演譯和表達技巧,反之暴露了在制度的推行上未符專業要求。其三是確立「委約作曲制度」。作者只總結吳大江在任期間的委約作品數目(達110多首)和列出部份樂曲名稱,羅列資料多於評論,評估成績就稍欠深度了。若能總論每一樂季委約作品的主題方向、創作手法、曲式變化、技巧提升、配器拓展等,指出其中具劃時代意義的代表作品,庶幾乎可以為吳氏八年任內的委約作品制度勾劃出一個蛻變升格的藍圖,這就更容易令人明白這個委約制度成功的原因。
吳贛伯《二十世紀香港中樂史稿》管評系列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