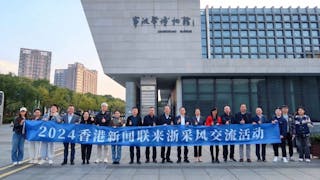作為創業者,必須有探索和冒險精神。在香港土生土長而成為世界知名的探險家黃效文,集齊各種我渴望磨練出的素養。十年來,我透過不同渠道認識他的故事,但我們始終緣慳一面。
見不到真人,能夠前赴他在雲南香格里拉的中國探險學會,跟隨其他探險家認識這「神秘」專業,我已感滿足。遂於4月,與幾個朋友及老師結伴「探索」這批探險家的工作,並從他們口中加深認識黃效文,更添我對這位前輩的敬意。
投身保育工作的探險家
我的第一個震撼,是發現探險家並非一般人(包括無知的我)想像中的危險、古代和撲朔迷離,更非Indiana Jones和盜墓者等云云荷李活電影中的形象。不過,探險家似乎真的需要精通十八般武藝,即現代學術上說的多學科訓練(multi-disciplinary training)。
黃效文曾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雙主修新聞學及藝術,當過著名雜誌《國家地理》的旅遊攝影師,之後成立「中國探險學會」,於上世紀80至90年代的幾次考察旅程中,首次發現長江、黃河、湄公河及怒江的源頭。
我聽得嘖嘖稱奇的是,他並非只做攝影師,把照片寄給雜誌便算,還要撰文報道探險中遇到的瀕危動物、少數民族的獨特生活習慣、快被現代化淹沒的文化遺產等,在過去30多年,平均每年出版一本著作。此外,探險隊每次出行也有20、30名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如生物學家、地理學家、地質學家、人類學家、醫生等,可想而知,他有深不可測的魄力、號召力和組織力。他們出發找尋河流的源頭前,須事先蒐集資料,做足科學研究,包括借助美國NASA的衛星圖片,估計地理位置。
回港後,我終能與黃效文見面。他博學多才、談笑風生,我笑稱這一頭白髮的68歲探險家為「周伯通」,他卻覺得自己更像外號「東邪」的「黃藥師」。
我生命中出現過好幾個金庸筆下的人物,諸如洪七公和江湖七怪;也遇過自命為南帝「一燈大師」的人,卻原來是岳不群!遇上黃老邪,乃我生平第一次,心裏立時提醒自己「handle with care」。
金庸筆下的黃藥師是「正中帶有七分邪,邪中帶有三分正」。認識黃效文,先要認識其正道(為人類作出的貢獻)和邪氣(他的顛覆性思維)之間的強烈個性,才能了解他的生命哲學和卓越成就。
還未認識黃效文本人之先,我不明白他為何會投身保育工作。多次長談中,他不諱言:「探險家固然熱愛探險活動,發掘新地方、新事物。以往的考察浩浩蕩蕩出征一次便是數個月,好不過癮!然而,路途上總遇上一些弱勢社群或瀕危動植物,難道真能置之不理嗎?一旦伸出援手,便是保育工作的開始,並且是長遠的工程。」
我還是一知半解,他續說:「保育工作不是停下來做一兩天義工那麼簡單,我們須經常回去跟進工作。為了責任感和承擔(commitment)而重複返回舊地,可說是一種違反探險家激情的負擔,卻又正正是理性上義不容辭的做法。」
保育為探險帶來更大意義
我進入了他左右腦的感性理性角力中,只聽他說:「雖有掙扎,卻因保育工作令探險工作帶來更大的意義和價值!如果我跟年輕人只說動聽的探險故事,而不同時帶出保育的承擔感,那是不完整的論述。」
正當我以為明白了他的「俠義精神」時,他的「邪氣」便滲出來:「我生性喜愛挑戰規範,不屑規條,不敢當別人的模範。我們的工作從來都隨着很多偶然的機遇而變化;探險隊遇上出人意表的情況,有時令我們改變原來的計劃,或帶領我們闖出新天。有否聽過布袋和尚的一首詩:『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六根清靜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插秧只是比喻,真義在於倒退以成就使命……我從不夢想成為探險家,這工作生涯是一個意外的演變結果。從前被封為探險家,我會感到無比為難,待出道良久後,我才肯接受。」
我經常撰文激勵大家探索精神,更夢想製作一齣以他的探險故事為題材的電影。雖然「十劃未有一撇」,還是按捺不住諮詢他的意願。他又給我一個很深奧的答覆:「拍攝電影有可能助長虛榮感,而虛榮感會令我分心。」
什麼都見識過經歷過?
「還未啊!」
我一時不知怎樣回應,他又說:「不過,我經常跟年輕人說,如有人問你是否什麼都見識過和經歷過(been there, done that),千萬不要答『沒有』,而是說『還未啊』——把潛在負面的答案變成中性,盼能扭轉為正面。」即係點?對着黃藥師,我真不知如何下結論。幸好,他補上最後一句:「我持開放態度,看看我們是否結緣。你也不要強求,或許待我死後才攝製電影,你們才有創作空間。」
探險是一份工作或職業,而是一種藝術
於是,我在剛過去的8月,夥同有意合作的電影製作隊,一起到香格里拉深入認識中國探險家的保育項目。須親赴黃藥師的「桃花島」,才能真正明白他的畢生哲學和探險工作。
我們看過世外桃源般的美景,也見過窮困家庭和高原生活的艱苦,更見識了中國探險家學會經營多年的部分保育項目。我們嘗試想像這批中國探險家,如何被一座幾百年歷史的殘破寺廟觸動,仗義為幾名藏族僧侶籌款,並帶來法國建築師開展修葺工程。他們講解如何為自然生態環境、為瀕危的金絲猴、西藏羚羊和黑頸鶴等提供保育工作,為高原老百姓改善經濟而開發氂牛芝士產品。
再跟黃效文談論時,他說:「中國探險學會成立之初,並非野心勃勃,連一份經營計劃書也沒有撰寫過,只讓事情自然地、有style地演變出來。或許這聽起來很禪,但都是事實。我不覺得探險是一份工作或職業,而是一種藝術,保育亦然。唯一最困擾我的是要遵從法則、規則和律例,頗違反我的個性,但也是必須承受的義務,否則我會成為outcast。」
我進入了他的內心掙扎,有點感同身受。他繼續有感而發:「我只作最低程度的conformity。『正』人有太多繁文縟節和掣肘,需要『三分邪』來跳出主流思維的框框。Purity is too zen!正邪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貫通天文地理的探險家黃效文,既是作家、攝影師、保育人士和創業家,但骨子裏,他是一個藝術家和詩人!正氣為道,淘氣與邪氣為策,離經卻不叛道。如有人問我是否認識黃效文,我只能說:「還未啊。」或曰:「只認識零碎的黃效文。」
「心度遊」系列 五之三
本系列文章: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