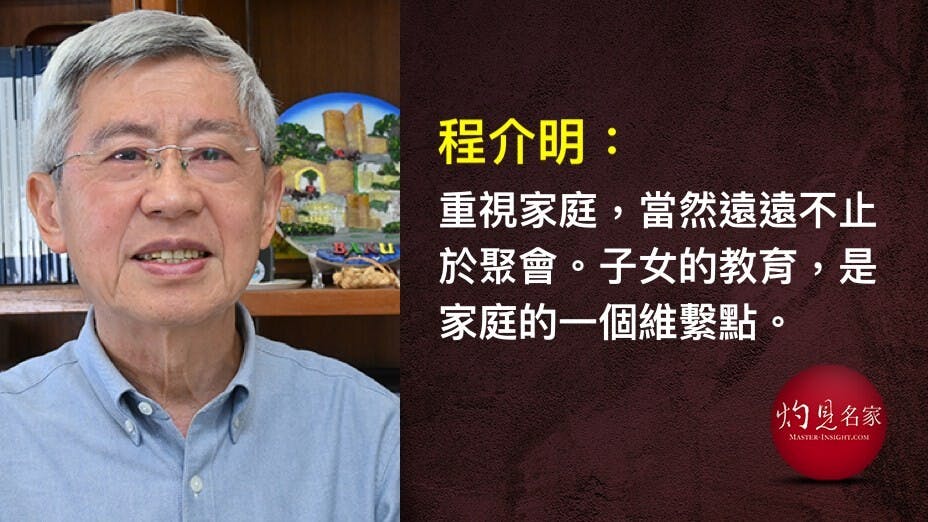上周提到費孝通的「差序格局」,誤作「差距格局」,幸得讀者提醒,特此道歉。另有讀者指出,費孝通的「差序格局」,與筆者的「豎直結構」,不是一回事。那也對,費氏的「差序」,既有上文提到的上下、長幼、貴賤(尊卑)等豎直的「差等」,也有平面的親疏、遠近、鬼神的社會關係。概括來說,就是中國人說的「人倫」,比筆者引用Hofstede(霍氏)的「權威距離」,要廣義得多。也感謝讀者與朋友的提醒。
費氏原話中的差序格局:「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繫成的社會關係……就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從己到家,由家到國,由國到天下」。因此,「己」是中心,「推己及人」、「克己復禮」、「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從「己」出發。費氏把這稱為「自我主義」,以有別於「個人主義」。
這就進入Hofstede(霍氏)的文化價值觀第二個維度: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或者如費氏所稱的「群己關係」。霍氏的「群己關係」,主要看人們與工作有關的價值觀。他開宗明義認為,大多數的社會都屬於「集體主義」,這也許是很多人無法同意的。另一方面,很多人會認為華、日、韓、越這些「筷子文化」,都是集體主義的社會。
中國社會 己耶群耶?
但是費孝通的「差序格局」,卻是認為中國人以「私」為本。他一開始就舉蘇州河的變髒為例,「一說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說大家可以佔一點便宜的意思,有權利而沒有義務了。」
再有,就是著名的美國華裔人類學家許烺光,他可以說是西方用人類學的角度(也就是文化角度)研究心理的始祖,認為中國人沒有「自我」(self)這個概念,「我」是屬於社會結構的一部分,而且是從小到大的結構,所以有「小我」與「大我」。「小我」服從於「大我」。因此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之說。與費孝通的「圈圈」不謀而合,不過觀察的方向剛好相反。
費孝通認為,西方社會是「團體格局」,每個人屬於一個(或者多個)裏外分明的「團體」。而「個人主義」,是假定了有團體,成員把個人的利益放在團體利益之上,才算「個人主義」。這剛好又印證了上述許烺光的觀察。也就是說,許烺光是從西方的框架,來觀察中國社會。因此費孝通認為中國的社會是「自我主義」,有別於「個人主義」。
以上旨在說明,所謂「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可以有不同的闡釋。甚至同樣的現象,可以在字面上有相反的闡釋。霍氏也看到這個問題,認為「己」與「群」的關係,從個人看,與從群體看,會很不一樣。費孝通說得更加徹底:「在差序格局裏面,公和私事是相對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裏,向內看也可以說是公的」;沒有說的是:向外看就是私。
家庭為重 立足克己
費氏舉出具體的現象,在西方社會,國家是一個明顯也是唯一突出的群己界線。要謀求個人的利益,「於是他們有革命、有憲法、有法律、有國會等等。」也就是要塑造或者改變這個國家,就要「克群」。在中國的差序格局裏,要「使群不致侵犯個人的權利」,「可以着手的,具體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最重要的德性」;「他們不會去克群」。
這樣有關公與私、群與己、個人與集體的概念討論,可以沒有止境,也許令人愈看愈糊塗。但是放到現實生活,卻比較容易清晰。
霍氏試圖把「群己」的相對關係用來解釋家庭和教育裏面的現象。他認為大家庭出身的人,比較注重與人的和諧相處;不同意的時候,也盡量不說「不」;即使說「好」,也不一定表示同意。相反,在家庭成員少的情況下,直言是美德,也不介意對抗。在出現意見分歧的時候,前者崇尚從眾,後者讚賞堅持。
大家庭孕育集體性的文化價值觀,小家庭孕育個人性的文化價值觀。相反亦然:文化價值觀傾向集體的,比較重視家庭的聚會、團結、沉默與和諧;文化價值觀傾向個人的,則講究獨立、交談,不介意離散。霍氏舉的「聚會」的例子,在香港很容易看到:疫情之中,限聚令讓香港人感到不方便的,就是不能一桌子三、四代人一起吃飯。電視宣傳中國文化,也舉一家人一起吃飯作為範例。
重視家庭團聚的,當然不只是香港,不過香港人全家一起飲茶,幾乎每周如此,即使是其他華人社會也會驚羨。意大利人也重視家庭,幾乎每天都要一家人一起吃晚飯。許多拉丁美洲的家庭,也有這種文化習慣。其他社會也有類似中國的風俗,把商店或者手工作坊的徒弟,視如自己的子弟,納入自己的家庭;但這種風俗正在隨着經濟活動的變遷而逐漸消亡。
重視家庭,當然遠遠不止於聚會。子女的教育,是家庭的一個維繫點。在華人社會,父母為了子女的教育,辛勤工作掙錢之餘,還不惜借貸。在香港,不少當兄、姊的,為了讓弟、妹能夠上學,寧願自己提早輟學,打工賺錢。這種為了家庭成員的教育而不惜犧牲,與學業有成而光宗耀祖,正是同一種文化價值觀的兩種表現。直至今天,還會看到中國邊遠的鄉村,每年掛起大橫額,指名道姓祝賀本村子弟考中北京名大學。我們外人看來,有點誇張;但是卻說明了這條村子,這個「群」,在過去花了多少努力;對村中的子弟,寄予多大希望。有子弟「高中」,就是有下一代魚躍龍門了!
親疏有序 內外有別
霍氏還認為,「群己」之分,還可以用排他性(Exclusionism)與同視性(Universalism 一視同仁也)劃界。排他性文化,很重視「自己人」與「外人」的界線。對自己人,愛護、優待,一切都可以容忍,甚至犧牲。對外人,首先是警惕、提防,不能隨便給以好處,甚至動輒視為敵意。不是說「肥水不流他人田」嗎?不止這樣,而且如費孝通所說,有一圈圈的親疏關係,愛護與提防,有高低不同的圍牆。同視性文化,則沒有這條界線,對人的好、惡、親、疏,是按照當時的交往情況與利益關係而發生的,沒有預設的內外界線。
這種排他性,在中國文化裏,也許是家族親戚的界線,也可以是家鄉地域的界線。同鄉會,在西方的文化,是很少聽說的。一方面也許很多是移民社會,家鄉來源複雜;另一方面,他們沒有強烈的「同鄉」這個「群」、這個「圈」。當然,就如費孝通說的,他們唯一的有界線的「群」,就是國家。要是法國人與法國人在異鄉相遇,一定是親熱一番。
但是,這種國家的界線,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民族遷徙──以色列的復國、蘇聯的統一、西方國家大批接納移民、中國和印度的人才外流,以及近年的北非難民湧入歐洲,純粹單一種族的國家已經很少,經濟發達的國家更是絕無僅有。「國家」這個群,裏面出現了很多種族「次群」。種族之間的「排他性」,逐漸出現。
即使現在,在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都在為學校裏面的種族問題而掙扎,例如教學語言、母語學習、民族服飾、宗教自由……即使是美國,是在1960年代,才逐步立法廢除黑白之間的種族隔離。而其中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就是1954年的Brown案件,黑人學生才開始可以進入白人學校,打開了黑白同校的序幕。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