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那天,天氣稍涼,微微有點秋意。
車子飛馳在薄扶林道上,窗外的景色,一路迆邐過去。
踏進張曼儀老師的家,她早已將準備好的書刊,齊齊整整的放在茶几上。
那是學者的一絲不苟,也是詩人的心細如塵。
她給我端來普洱茶,我們坐在沙發上,便聊將起來。
與文學結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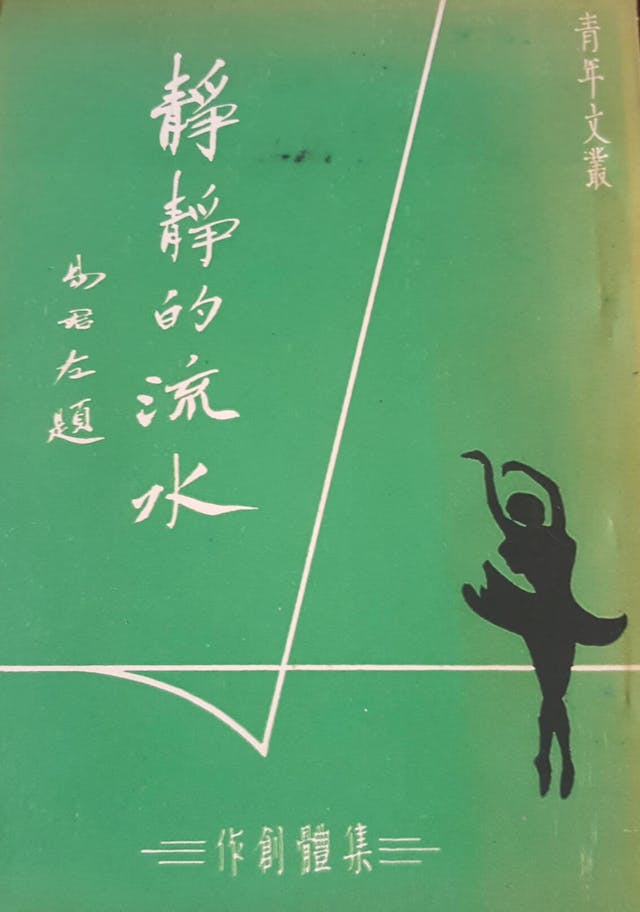
認識張曼儀,始於《八方》創刊時,她當時已在香港大學任教。
一直以來,她積極推廣現代文學,也是研究卞之琳的專家。
想不到,話匣子打開,談的不是卞之琳,也不是新詩,而是她寫作的舊體詩。
她剛印出的《瀟碧軒詩》,集子收錄了逾半世紀的作品,從1959年至2014年,共百餘首詩。
「瀟碧軒」之名,為其師吳天任先生所賜。她在尊德女子小學唸二年級時,已開始讀四書、《古文評註》等古籍,至高小時,偶然從坊間購得《離騷》及詩詞集,雖然是一知半解,但她卻欣然捧讀。升上中學後,她先在聖方濟各唸初中,高中時升上聖心書院,預科時學校不設中文科,為報考香港大學的公開試,遂往吳天任老師處研習中國文學,並隨他學習寫作舊體詩。
自此數十年間,她對於舊體詩,雖時寫時輟,始終不離不棄——「偶有所感,發諸吟詠,仍多取舊體詩」。

「正如同年代的寫作人,我是從《中國學生周報》走過來的。」
1956年,她第一次投稿《周報》,散文便獲即期刊登,還得到編輯約見,而且聯絡不輟,後來總編輯黃崖先生往馬來西亞主編《蕉風》,還約她繼續供稿。在中學及大學時代,她寫的多是散文,另兼及小說,新詩和舊體詩。她認為新詩創作要求高,不易寫得好,每一首都是「內容和形式有機的新結合,舊體詩卻有格律可循,可以隨意發揮,放心多寫」。
她最緬懷的,是那時候與文友的交流活動,一班年輕人編《靜靜的流水》散文集時,經常在銅鑼灣的「紅屋餐廳」聚會,還到過道風山旅行。
張曼儀一直珍存着當年的學生創作選集《靜靜的流水》(一、二集)和《曙光》。《靜靜的流水》(一、二集) 分別於1959及1960年由自由出版社及文海出版社出版,集子內收錄的都是當時年輕人的作品,作者之中,有張曼儀、黃俊東等熟悉的名字,還有易君左先生寫的序。《曙光》則由《中國學生周報》編輯,收錄刊登於《周報》的學生作品,由友聯出版社出版。
張曼儀取出當年的照片,在道風山之旅中,年輕的胡菊人(當時叫胡秉文)也在其中,當年的他,果真「人淡如菊」!
唸預科時,她的一篇小說取得徵文比賽的冠軍,獲贈三個月學費。由於她會考成績非常優異,可免交學費,所以她可以自由享用這90元。
當年,她最愛讀《人人文學》,尤其喜歡百木(即力匡)的散文,還有黃思騁、齊桓(即孫述憲)的小說。獲獎後,她便用一半獎金買了一些文藝書籍,連同早前在灣仔軒尼詩道新月書店買的一套《人人文學》,捐贈給灣仔小童群益會圖書館。原來她唸初中時,經常到這間圖書館借書,便藉此機會以回饋。
1962年,港大畢業後,她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唸研究院。1966年回到港大,最初在中文系做行政工作,當時的系主任羅香林教授有意把一年級的翻譯課擴充為學位課程,便於1967年聘任她為助理講師。其後又協助馬蒙教授擬訂和開設現當代文學課程。她在港大任教翻譯及現當代文學近三十年,到1994年退休移居加拿大為止。
上世紀70年代中期,她曾跟文樓、黃繼持、小思、古蒼梧等合編《文學與美術》雙月刊及《文美》月刊。當時,她多以「淨沙」之名撰寫散文,發表在這兩份刊物。「淨沙」出自詞牌《天淨沙》,她很喜歡「淨沙」這個意象,更愛其含義——「個人只是三千大千世界中一世界的一粒沙子,何其渺小,能得到風風雨雨的淘洗,使之純淨,是沙子的造化。」,便以此為筆名。
《現代中國詩選》
「我一生與詩結了不解緣,讀書、研究、教學、翻譯都集中在詩。」張曼儀如是說。
早年,她曾與文世昌、黃繼持、古蒼梧、黃俊東、余丹等幾位朋友,合編了《現代中國詩選:一九一七——一九四九》。當時,大家有感於新文學的作品,散佚零亂的情況很嚴重,想做些資料蒐集和整理的工作,於是先從新詩做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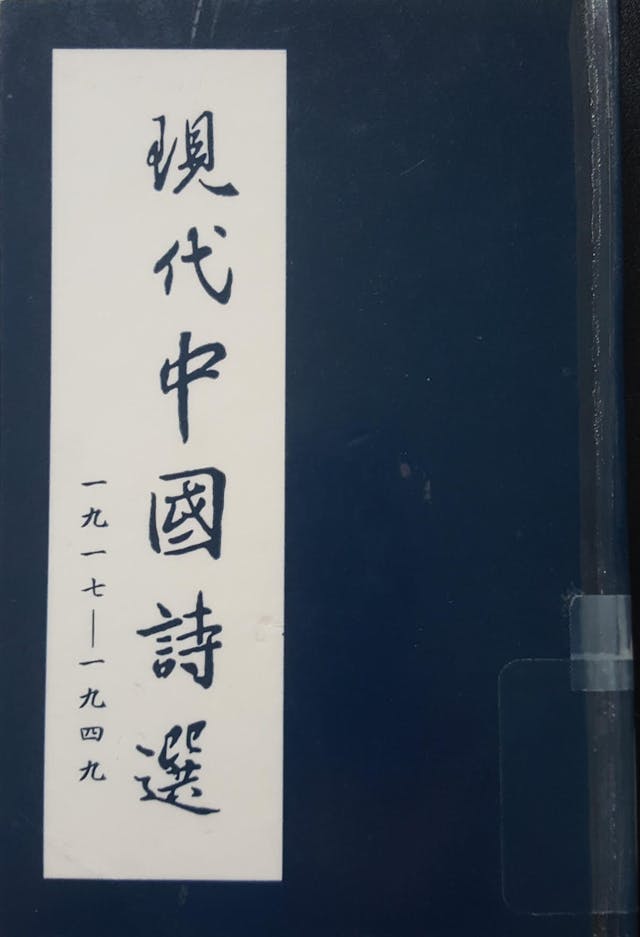
《詩選》的編選工作,從1967年8月開始,差不多每隔一兩個星期,他們便開一次編輯會議,整理資料,編訂書目,定出詩人詩作的名單。在編選的過程中,往往須從海內外蒐集資料,有時甚至要為了入選的一兩首詩,翻查大量的史料,才找到出處。
編選工作進行了兩年便差不多完成了,在交稿前夕——那是1969年7月,為了如期交出,日間有好幾位港大的同學和朋友輪流來幫忙謄寫,連單周堯教授(當時是中文系本科生)也曾來幫忙抄稿。到了晚上,大家還須繼續努力,直到曙光初露才完成工作。
《詩選》編輯之初,原是為了紀念「五四」50周年,後來耽擱了,至1974年才正式出版。此書厚達1,800頁,分成兩冊,需用超薄的聖經紙印刷,故售價亦比較昂貴。
《詩選》的出版,為中國新詩保留了許多珍貴的史料,對新詩的研究作出了相當大的貢獻。同時,此書對詩人和作品的評價,其分析和闡述,亦甚具參考價值,尤其是40年代部分的作品。這時期的新詩技巧比較成熟,思想較有深度,內容也較為開闊,既重視詩人的社會責任,也沒有忽略新詩的藝術性。
張曼儀說九葉派詩人袁可嘉先生屢次表示《詩選》收錄了他們的作品,並給予肯定的評價,是最早讓這個詩派在文學史上佔一席位的。
上世紀40年代詩人的創作方向,是將社會性與藝術性結合起來,《詩選》對此給予正面的評價。這個評價對後來新詩發展的方向,實在帶來很大的影響。
卞之琳研究
「想起卞之琳便會想起張曼儀,想起張曼儀就聯想到卞之琳」。小思老師所說的,實在一點都不誇張。
張曼儀一直醉心古典詩詞,早年對新詩興趣不大。在60年代初期,她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唸研究院時,偶爾在圖書館發現了卞之琳的《魚目集》,才對新詩發生興趣,這是緣起。她回到香港後,編《現代中國新詩選》時,便開始對卞之琳的詩作比較全面的研讀。她特別欣賞卞之琳,大抵與她的性情有關。
1978-79年間,張曼儀放「學術假」。1978年秋天,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她開展了卞之琳的詩歌和翻譯研究。
為甚麼研究卞之琳?主要是因為他在解放後,近三十年間,受到國內外毫無道理的忽視。張曼儀認為卞之琳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天分極高、成就卓越的詩人和翻譯家。
研究之初,她從卞之琳在海外的朋友和學生入手,訪尋他生平事跡的旁證,並且在北美各大圖書館搜索,發掘他已入集和未入集的著作。
她先往加州灣區,訪問了卞之琳在西南聯大的學生許芥昱先生。
1979年初,她開始跟卞之琳通信,第一次收到他的回信,自言是最好的「生日禮物」。同年五月,她到新港(New Haven,亦稱紐海文) ,拜訪了卞之琳的老朋友——「民國最後的才女」張充和女士。12月,她飛往北京訪問卞之琳。這位睿智謙和的長者,不單解答了她對他作品上的疑難,核實了自己的生平事迹,協助她到北京圖書館找資料,還贈送了自己珍藏的孤本給她。
卞之琳當時已年近七十,但精神還不錯,帶她四處參觀,重訪舊地。他們走過北大紅樓、漢園公寓小樓和東齋故址、何其芳住過的大豐公寓和張充和住過的小公寓舊址,還有《文學季刊》和《水星》編輯部的所在地北海三座門⋯⋯
「這位『老北京』可真『能走』!」——張曼儀笑着說。
由於卞之琳受法國象徵主義的影響甚深,為了方便研究,她雖然曾經唸過法文,那時亦在威大上了一個學期法文閱讀課程“Reading Course in French” ,重溫一下。
她對學術研究的專注和認真,於此可見一斑!
追尋卞老足跡
她看了很多期刊雜誌,還有「微型膠卷」,將卞老的舊作逐一鈎尋出來,重建他的創作過程。她說——這不是一個「純」研究,而是個學習的過程,亦可不斷提升自己。箇中有痛苦,也有快樂,當然也很充實。卞老是個完美主義者,當然不想一些不成熟的作品被發掘出來,但也無奈接受。
休假期滿,張曼儀只完成了他抗戰及抗戰前期資料的蒐集,寫出了他早期詩歌研究的英文稿,後來改寫成《卞之琳著譯研究》的第一章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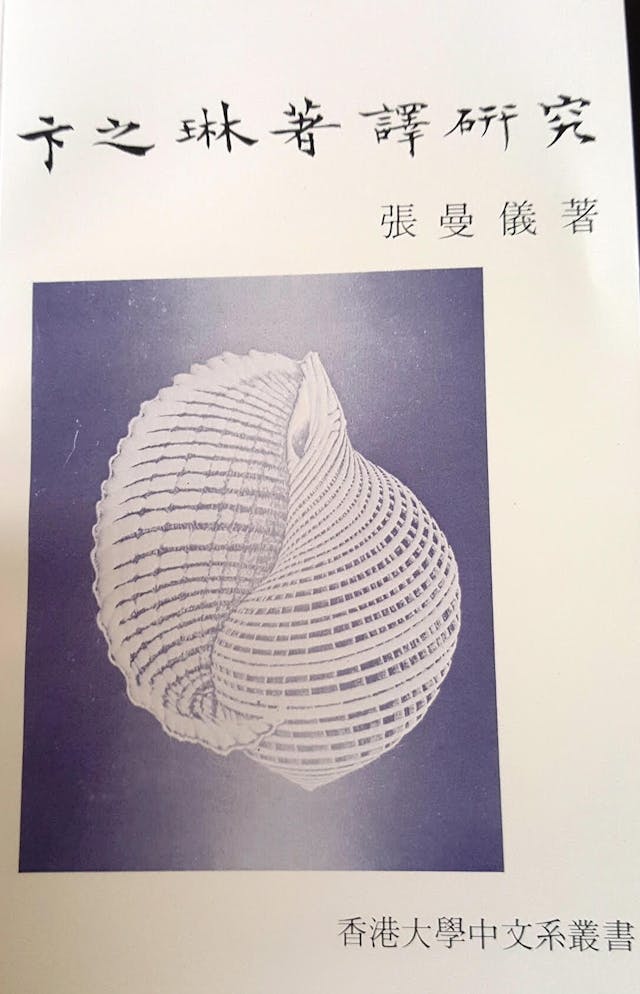
教學工作實在很忙,直到1984年春,張曼儀再度休假,才有充裕時間縱覽全局,擬訂全書各章的大綱細目。結果,她花了八年時間,至1986年底,才陸續完成全書,了卻一個心願。
「過程比結果重要!」張曼儀一再強調——「不是作品的文字,而是文字背後的精神,使我的生命得到啟發」。
「在研究過程中,我對卞老愈來愈欣賞,而且也更佩服他。」曼儀老師指出,卞老凡事要求精確,為人認真不苟、正直不阿,更令人對他生出敬意。
兩年前承石磬文化事業公司幾位文藝青年的雅意,張曼儀出版了《揚塵集》一書,主要輯錄其創作,例外的是在「懷念卞之琳」一輯中收錄了幾篇論文。她在自序中道出心聲:「因為跟卞先生的通訊以至論交,是我生命中的一道陽光,映照了我20年的生活,跟我的成長分不開。」
張曼儀已將自己與卞老在1979-2000年間的通信,他的手稿、初版書、照片、錄音,以及他與張充和的通信等,悉數捐贈香港大學圖書館。
翻譯與佛學

張曼儀在翻譯方面的經驗非常豐富,早在唸書時代,她已開始翻譯文學作品。
在1967、68年間,她翻譯了《塞伯短篇小說選》、《奧亨利短篇小說選》,由今日出界出版社出版。1985年,她與陳載澧合釋《莫扎特之死》,其後,曾替商務編選了《現代英美詩一百首》,同時亦翻譯了書中部份作品。
然而,在翻譯道上,她一路走來,都是「英譯中」而已。
直至1994年,移居加拿大後,她才開始踏上「中譯英」之路。
在加拿大時,張曼儀居於美麗的小城——哈利法克斯,浸會大學翻譯研究中心的張佩瑤教授,曾請她英譯了一些中國作家談翻譯的文章。
2000年9月,張曼儀回港定居。2001年的國際詩歌節,她英譯了一些香港本地作家如王良和、胡燕青的詩作,外界的反應非常好。
自此,為她開拓了一個嶄新的天地,也令她漸漸萌生了翻譯卞詩的念頭。卞之琳曾自譯其詩作20多首,亦多次跟她討論其詩歌的英譯問題。張曼儀為了完成卞老的心願,於是開展了這項艱鉅的翻譯計劃。
透過中大翻譯研究中心《譯叢》主編孔慧怡女士,她找到一位合適的伙伴David Lunde(倫戴維)。倫戴維是紐約州立大學的榮休教授,有翻譯中國古典詩詞的豐富經驗,本身也是詩人,實在是位理想的合譯者。計劃從2002年秋天開始,至2005年春天才完成,先由張曼儀選出篇目,然後合作翻譯,大部分作品選自《雕蟲紀歷》,故譯詩集名為The Carving of Insects(《雕蟲》)。出版後獲美國筆會2007年度翻譯獎。

翻譯的過程,讓她好像親身經歷了卞之琳詩歌創作的過程,對他的認識又加深了一層。雖然卞之琳畢生探索的是新詩格律的理論和實踐,但他們英譯卞詩,原則上卻不講求格律上的摹擬,只求在詩質上無愧於原作。她強調——「我們的英譯,不期望也不可能可能跟原作一樣,只嘗試為卞詩在另一個語言文化的土壤裏培植一個新生命。」
張曼儀從事翻譯工作多年,近年開始涉獵佛學,領悟到世事總存缺憾,人生重要的是過程而不是結果。她說:「譯者如果追求完美,要求譯文與原文百分之百相等,首先就不會提起譯筆。這也與佛學暗合。」
她與佛學結緣,緣起加國。她第一次「禪坐」的體驗,就在哈利法克斯。當地她一位教車師傅,是專業編輯、英語教師,也是通曉梵文和藏文的佛門長老。因為藏傳佛教在西方創辦的佛學中心Shambhala Centre,先一年從美國遷至哈城,不少資深教友亦隨之北移。她因緣際會,也曾在佛學中心聽課。她從加拿大回到香港後,曾往志蓮淨院進修佛學課程,亦曾與斯里蘭卡籍的阿那律陀長老(Kākkāpalliye Anuruddha Thera)和蕭式球老師合譯了原始佛教的佛典The First and Second Buddhist Councils: Five Versions (English Translations from Pāli and Chine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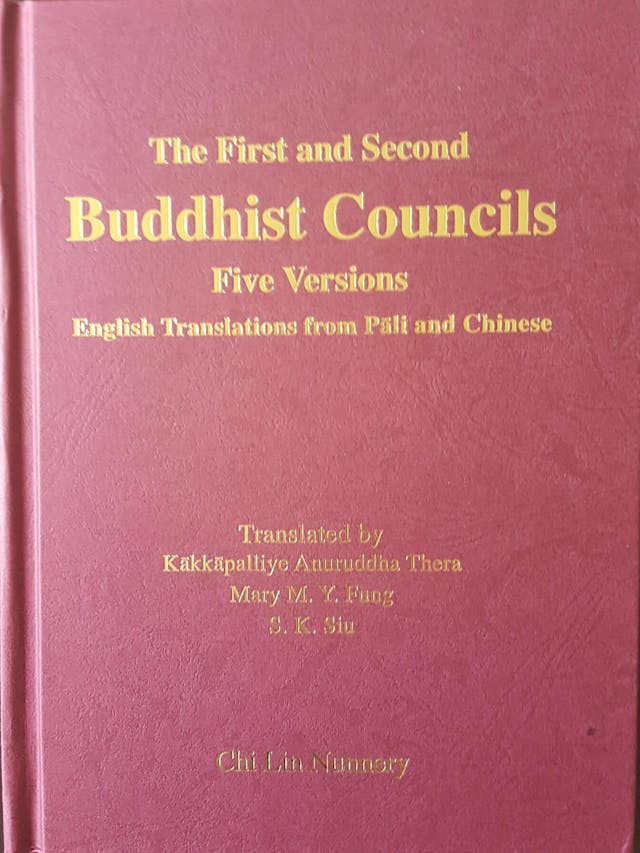
近幾年,張曼儀嘗試將佛學與詩歌結合起來,與倫戴維合作翻譯「禪詩」,於去年出版了A Full Load of Moonlight (Chinese Chan Buddhist Poems)一書。此書精選了180首中國古典詩歌,翻譯成英文。詩作的選取,主要取決於詩中的禪意,還有文學藝術上的價值。除了禪師的作品,亦兼及唐宋著名詩人,如王維、李白、白居易、蘇軾的詩作。
張曼儀的翻譯工作,一直沒停下來,現正忙於英譯徐志摩的詩選,而她早前寫了一系列有關翻譯理論的文章,亦即將出版。
活在當下 喜樂隨緣
最初在電話中約定,這個專訪大約只談三個小時,但訪問那天,在曼儀老師家中竟逗留了大半天,她還請我吃了一頓美味的午餐。我們從十一時開始,談了接近近兩小時,吃過飯後,又繼續聊,直到三時多,我才離開。雖然談得很開心,但耽誤了她休息的時間,實在不無歉意。
在小巴站候車之時,曼儀老師溫婉的聲音,她那纖瘦的身影,依然在腦際盤旋,訪談雖已結束,但一段因緣才真正開始。
禪悅新耽如有會!
她的一首新詩《喜樂》,忽爾在心頭湧現——
雨過天青,
朵朵蓮花浮出水面:
撒一把飼料,
紅的黃的錦鯉
齊來噬食——
魚樂。
靜坐在時間之外:
讓思緒飄進來
又漾開去,
細觀心如何波動
以至安住——
禪喜。
「活在當下,已得禪宗真意」——想起了曼儀老師在禪詩集子上給我的題辭。
禪是一種心境,也是一種生活方式。

待何時有緣,我也可以到志蓮淨院,聽佛學課程去。
文章原刊於2016年1月《大頭菜文藝月刊》第5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