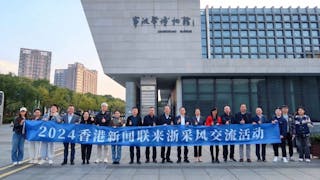從外蒙古旅行回來已多個月了,仍不時想起烏蘭巴托的喇嘛廟、博物館,哈拉和林廣闊無垠的牧區、草原上星群密布的夜空,還有荒原上孤寂的黑城遺址……
「紅色英雄」烏蘭巴托
外蒙古即蒙古國,於我來說,是一個廣闊而神秘的地域。據資料介紹,現時的蒙古國約有300萬人口,而國土面積卻是香港陸地面積的1,400多倍,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低的國家,而首都烏蘭巴托全年平均氣溫為零度,最寒冷時溫度更低至零下40多度,可說是世界上最寒冷的首都。
坐在香港機場的候機室朝外看,停機坪上,「蒙古航空」飛機的標誌就像一頭奔騰的駿馬,雖然仍身處香港,思緒已飛馳至蒙古的大漠草原。
飛抵首都烏蘭巴托的成吉思汗機場,已接近6時,入境手續相當順利,步出機場,天色還是相當明亮,原來太陽到9時後才開始下山。

烏蘭巴托,意即「紅色英雄」,這個「四山之間」的城市,舊名庫倫,曾是藏傳佛教的中心和王公貴族居住的地方。不過,今天的烏蘭巴托,已由昔日的宗教中心變為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在烏蘭巴托的幾天,主要的參觀點,大部分都是寺廟和博物館,離不開宗教與政治。此行的第一站,就是位於市中心的國家歷史博物館。展館介紹了蒙古從石器時代到二十世紀的歷史,重點展示了成吉思汗如何統一蒙古,其後蒙古帝國的興起、元朝的建立、四大汗國的發展……,以至蒙古獨立後的情況。

認識一個國家,這是個相當好的開始。
十三世紀時,藏傳佛教開始成為蒙古統治階層信奉的宗教。至十六世紀,藏傳佛教的「黃教」傳入,佛教大盛。時至今日,大部分蒙古人都篤信藏傳佛教。
過去的庫倫,曾是哲布尊丹巴的駐錫地,寺廟特別多,外蒙獨立時,仍有上百座,至上世紀30年代末期,在鎮壓統治下,遭大肆破壞,幾乎全被摧毀。少數寺廟保留為博物館,如興仁寺。此寺建於公元1904年,原是哲布尊丹巴八世之弟喬金喇嘛的寺廟。館內藏有大量的藏傳佛教文物,包括藏戲跳神用的面具、禮佛法器,以及唐卡、佛像等。興仁寺在都市中被高樓大廈包圍,但整個建築群都很中國化,而且多是木造的。寺前的照壁精雕細縷,刻有中國八仙之四仙──藍采和、曹國舅、李鐵拐、呂洞賓;前面的圓石座則刻有五隻蝙蝠,取其「五福臨門」之意,展現了濃厚的中華文化色彩。


至於博格達汗冬宮博物館,則是蒙古末代帝王博格達汗──哲布尊丹巴八世,在冬季居住的宮殿,於公元1903年建成。宮殿的布局呈三院結構,前庭廣場牌樓上的大匾額,以蒙、漢、滿、藏四種文字,寫着「樂善好施」四個大字。正殿和兩側的房子,分別展出珍貴的唐卡、佛像和法器,令人大開眼界。末代帝王住過的居所,是一棟古舊的二層樓房,裏面門窗緊閉,空氣非常混濁,氣氛也顯得有點陰森,藏品大多是王公貴族的華麗服飾,以及各國使節贈送的貴重禮物;還有一些的動物的標本,是博格達汗的個人收藏。展品中最觸目的,大概是由150張美洲豹皮製成的蒙古包。

有人說過:「如果沒去過甘丹寺,就等於沒到過蒙古。」甘丹寺是此地最古老的寺院之一,建於十九世紀初年,可說是烏蘭巴托的起源地,有「極樂之地」的意思。大殿內原有的觀音銅像,早被熔掉,化成兵器砲彈。目前寺中這座寶像,是公元1997年才完成的,高25公尺,法相莊嚴,全身鍍金,纓絡被體,望之令人心生敬畏。甘丹寺每天都有大批的信眾朝聖燒香,人擠人的,置身其中,有一種透不氣過來的感覺。步出寺院的廣場,有很多的灰白的野鴿子,或踱步、或飛翔,加上身披紅衣的小喇嘛徐徐走過,好一道亮麗的人間風景。


除了廟宇,美術館亦離不開宗教。札那巴札爾美術博物館,得名於哲布尊丹巴一世(俗名「札那巴札爾」),他是蒙古的第一位活佛及政教領袖,也是位多才多藝的藝術家,被視為蒙古的「達文西」。館內有一幅他的自畫像,散發出聰慧的氣質,綠度母菩薩是其代表作。館內的藏品,包括傳統的宗教、民間藝術,以及大量的佛像、佛畫、唐卡……,還有不少近代蒙古畫家的作品。在這裏,你可以欣賞到薩滿教和佛教的藝術品,亦可以看到反映遊牧生活細節,以至與馬有關的畫作。我最喜歡的一幅,是《在蒙古的一天》,洋溢着濃濃的生活氣息。
位於市中心的蘇赫巴托爾廣場,亦是遊客必到之處。偌大的廣場上,正中的雕像是革命英雄蘇赫巴托爾馬上的英姿。廣場是典型的蘇聯式建築風格,有點像天安門。翻查歷史,當年蘇聯捧出這位精神領袖,目的就是消弭蒙古人對成吉思汗的崇拜。時移世易,蒙古政府在廣場以北,以白色大理石建成的政府大樓,中間坐着的,就是巨大的成吉思汗雕像,頗有君臨天下之勢。城外的成吉思汗山上,也有巨幅的成吉思汗畫像,佔據了整個山的側面,正正表達了蒙古人民對成吉思汗崇敬之意。


登上南郊博格達山,北坡上翟山紀念碑,原為蘇聯建造,藉以紀念蘇蒙的友誼,以及二次大戰中犧牲的無名英雄。在山上游目四顧,土拉河靜靜地向西流去,市區的水泥大樓,山邊的蒙古包,全都一覽無遺。

除了參觀活動,其中一天的傍晚,是在國家劇院觀賞國家歌舞學院的演出,既有唱歌、舞蹈、軟骨功,以及宗教傳說的表演……,還有龐大樂團的演奏。印象最深刻的,是蒙古人特有的「喉音歌唱」,聲音從喉底裏發出來,配合馬頭琴的伴奏,有種獨特的神秘感。對於這個演出,大夥兒原先並不抱太大期望,欣賞後卻深受感動,想不到蒙古傳統藝術是如斯的精彩絕倫。
在烏蘭巴托只有短短數天,大部分時間在市內活動,看來要往哈拉和林的牧區,才可一睹「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草原景色。
「自由之都」哈拉和林
隨後,我們便向哈拉和林進發。奔馳在公路上,無垠的草原在窗外掠過,牛群、羊群、馬群在自由徜徉……偶爾還看見大鷹在空中盤旋。

哈拉和林位於鄂爾渾河河谷,是成吉思汗欽定的首都。公元1235年,窩闊台正式定都哈拉和林,開始修築城牆,至公元1264年,忽必烈才將首都遷往大都。元朝滅亡後,哈拉和林才被明朝軍隊夷為平地。哈拉和林的興衰就是蒙古歷史的一個縮影。
路上草原風光怡人,但是路程漫長,中午在一間渡假村停下來,吃了一頓傳統的美食──「石頭烤羊肉」,我對羊肉興趣不大,但與之共烹的紅蘿蔔和馬鈴薯,卻好吃得不得了。
飽餐之後,我們繼續往「哈拉和林博物館」進發。開館只有5年的博物館,看上去規模不大,外型卻很現代化,展覽的中心是一個微型的城市模型。據資料記載,當時城中有佛教的寺廟,還有清真寺和基督教堂,可見當時蒙古的首都,是個自由的都市。館內的展覽主要分為三部分,包括石器時代、青銅時代、蒙古帝國前史及蒙古帝國。由於時間緊迫,我們還需趕往額爾德尼召寺,故此只能在最後一個展區轉了一圈,看了成吉思汗、窩闊台的銀幣,忽必烈的御匾,以及相關的歷史文物,便得匆匆離去。
十六世紀末,蒙古部族出身的達賴四世,在故城的原址,以殘磚敗瓦建起了蒙古最早的黃教寺廟──額爾德尼召寺。其後,陸續的增修重建,被108座白塔圍繞着的廟宇,曾多達100座。上世紀三十年代時,在宗教迫害下,其他的建築全被摧毀,倖存的就只有3座殿堂。我們參觀的時候,眼前所見的法器、佛像、唐卡,已有數百年的歷史,據說是當時的居民,偷偷冒險埋藏起來的。


當年的皇城四周,各有一座烏龜石鎮守,象徵「長壽無疆」,寺廟附近的山上,現在還留有一座。烏龜石的下坡,有個被欄杆圍起的陽具石,原用作提醒年輕的喇嘛不要犯戒,現已成了婦女求子的奇石。

走上附近山坡上的紀念碑,站在青青的草坡上,可遠眺壯闊的鄂爾渾河流域,亦可俯瞰白塔圍繞的額爾德尼召寺。紀念碑的外面圍以環形的三面牆,牆上用馬賽克瓷磚,標示出蒙古不同時期的版圖,藉以懷緬過去那段輝煌的歷史。第一面是匈奴時期,有麋鹿與馬的圖案;第二面是突厥時期,牆上畫的是草原石人;第三面是蒙古帝國時期,繪上成吉思汗與蒙古騎兵的畫像。

鄂爾渾河全長1124公里,流經外蒙古北部,在蘇赫巴托附近和色楞格河匯合後,然後繼續往北注入貝加爾湖,想到幾天前到過的貝加爾湖,感覺還是蠻奇特的。
晚上入住的蒙古包渡假村,就在的鄂爾渾河畔,蜿蜒暢流的河水,見證了草原上無數王朝的興衰。第一次住蒙古包,我感到非常雀躍。可是,走進蒙古包內,便發現那只是徒具外型的營帳,裏面的布置,有如一般酒店的房間,中央沒有生火的爐子,不用燒牛糞取暖,卻有供應暖氣的「空調」。看來,許多傳統的東西都無法躲過被「現代化」的命運。

原以為晚上可以觀星,可惜日落之後,村內的路燈仍很明亮,天上的星兒稀疏寥落。幸而半夜醒來,步出帳外,被一大片黑暗包圍着,卻見天上繁星燦然……至今仍是宛在目前。

離開渡假村後,我們又直奔草原,尋覓「黑城遺址」去也。蒙古國的基礎建設仍在起步階段,哈拉和林許多地方還沒有柏油路,其實根本就沒有路,車子直接在草原上奔馳,隨便駛過去就是路,在崎嶇不平的路上顛簸了個多小時,司機還要一再停下車來,向草原上的牧民問路。折騰了半天,車子終於停下來了,只見草原上的古城牆,就在不遠處突兀而起,大夥兒難掩興奮之情。

烈日當空,我們步行穿過起伏的草地,爬到城牆上,沿着城牆漫漫而行,極目四望,四處荒草鬱鬱蔥蔥,地上亦見磚瓦殘片。這座草原上的孤城,建於公元751年,原是回鶻汗國的首都,至公元840年,因吉爾吉斯人的突襲,回鶻汗國就此滅亡。如今,在這個古城的遺址,考古學家仍在發掘文物,據說曾找到唐代風格的蓮花紋瓦當。
離開古城之後,又繼續上路,也許路上滿布坑坑洞洞,車子在途中突然停下來,原來輪胎磨破了,幸而及早發現,沒有造成意外。司機雖然年輕,但經驗豐富,車上帶有修車工具,以及後備輪胎,附近牧區的牧民,目睹車子拋錨,也跑過來幫助,不多久車子便修好了。也許,仗義每多「屠狗輩」,應改為仗義每多「牧馬人」!
我們的下一個目標,就是一方石碑。
唐朝時期,活躍在蒙古高原的遊牧民族是突厥人。刻有突厥文與漢文的《闕特勤碑》原立於和碩柴達木湖畔,現已移進展覽館中。石碑是突厥汗國的毗伽可汗,在公元732年,為紀念其亡弟闕特勤而建立的。《闕特勤碑》一面為漢文,是唐玄宗親自撰寫的銘文,描述了突厥和唐朝的友好關係;另外三面卻是突厥文,在突厥文的銘文中,除緬懷闕特勤、記載其功績外,字裏行間,卻充滿了對唐朝的仇恨,以及對漢人的懷疑。銘文內容的截然不同,戲劇化的對比,反映了當時兩國間微妙的關係。

蒙古草原曾是古代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回紇、契丹、黠戛斯、韃靼等多個遊牧民族生活之地,最後一個是成吉思汗統一的蒙古部族。3,000多年以來,草原上的遊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之間,既有不少衝突,亦有融合之處。
外蒙於公元1921年,在蘇聯支持下脫離中國獨立,並於公元1924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直至蘇聯解體後,在公元1992年,外蒙開始民主化,改名為「蒙古國」。這個草原之國,從傳統走向現代,在發展的過程中,亦出現不少問題。
鑑古知今,想起今時今日的中蒙關係,箇中可有值得反思之處?
原刊於2018年4月《城市文藝》第94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