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視區域研究
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始於冷戰時期的美國,可以被視為東方學的近代改良版。美國在19世紀沒有參與在亞洲和非洲爭奪殖民地,所以美國學界雖然熟悉歐洲和美洲,卻沒有東方學的傳統。1950年之後,美蘇兩大陣營尖銳對立;雙方都想了解對方,也都想爭取新近獨立和即將獨立的亞非國家進入自己陣營。
這時美國精英階層體認到,美國政府和商界亟需大批通曉世界各國語言、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的人才。1951年,福特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邀請20幾間有實力的大學齊集會議,建議它們成立以不同區域為物件的跨學科專業,如東歐研究、中東研究、東亞研究等。這個建議與美國大學傳統上的學科分類不相符合;美國大學一般以學科內容分院系,每個系的重心放在一種或兩種專業知識上,比如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和人類學、經濟學等。過去美國學者對於東方的研究是在某個專業下進行,因此研究中國政治的人一般是在政治系裏,研究日本經濟的學者則屬於經濟系。
一些學者起初抗拒把不同專業混雜起來培養學生的方式,認為這會讓學生專業素養不足。但是福特基金會認為美國需要許多對各地區有一般性認識的人才,所以拿出巨額款項在這些大學設置了區域研究獎學金,鼓勵學生進入這些新領域;不久美國政府也通過國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撥專款資助學生學習某一種語言或是某一國的歷史文化。當時有學者調侃地制訂出一條法則:The Golden Rule of Science is he who has the gold makes the rule!(科學的黃金法則是誰有黃金誰就定法則!)
東方學的演變
1965年以後,歐洲人開始的東方學在北美洲兌變為區域研究;要培養的是對某一個地區(或國家)有一般性認知的人。到了1975年,北美洲的一流大學幾乎都建立了若干區域研究的專業。
在1965─75這段時間裏我與北美洲三間大學的區域研究有過交集;之後的20多年裏我又在四個大學裏認識了不少從事區域研究的學者。
我修讀碩士和博士的史丹福大學和西北大學是早期建立區域研究中心的大學。史丹福大學位於太平洋東岸,因為第一屆畢業生胡佛(Herbert Hoover)總統曾在中國開灤煤礦任工程師,所以很早就重視對東亞的研究;我經常去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e)的中文圖書館翻閱從中國特別訂購的書報。西北大學有一個很強的非洲研究中心,當時有不少蘇丹交換學生,一位早我一年得到工程博士的同學回國不久後就當了國防部長。1969─75年,我在紐約州立大學任教,眼見反越戰的浪潮和大學對於東亞研究的重視。1976年我轉到加拿大的麥吉爾大學醫學院任教;大學裏有一個頗具名聲的伊斯蘭研究院(Institute of Islamic Studies),是1952年在福特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建立的。1981─82年我在巴黎大學醫學院任訪問教授,有機會目睹法國在東方學方面的投入和成就;有關伊斯蘭和東亞、南亞文明的博物館收藏及出版物確實美不勝收。
1984年到1990年我在南加州大學任教授及系主任;有三年時間被選入大學的長期聘任與升級委員會(University Tenure and Promotions Committee),參加過對區域研究教員的評審,因此涉及到區域研究的學術價值與評審標準。
區域研究只屬專才專利?
當時學界的主流意見認為,從事區域研究者必須在某個專業領域(如政治學)有優秀表現,不然在得到長期聘任後不太可能做出有分量的學問。因為我的專業是生物醫學工程,素來要求每個教員必須精通某種工程專業(如儀器設計)並兼通某部分生物醫學(如心血管系統),所以我在大學委員會甄審個案時不贊成讓「Jack of all trades, master of none(樣樣通,樣樣鬆)」的人升級。
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區域研究作為正式學科的時間不長,還不能為「某區域研究」訂出學術標準,但是學者終歸會對這寫當初由外界力量帶進校園的新專業,賦予足夠的知識內涵。過於實用而缺少學術內涵的課題應該由政府、民間智庫、商業機構去做。對區域研究人員的評審不宜太嚴苛,以免把未來可能成為優秀學者的人過早淘汰出局。
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強力推動經濟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輿論界乃至學術界彌漫着天下即將一統的樂觀情緒。
正當此時,我應聘擔任建校已經300年的匹茲堡大學的工學院院長兼醫學院教授,受命以新興的生物醫學工程協助振興這個美國的工業老基地。除了醫學院十分強,匹茲堡大學的另一個強項是區域研究。
我在匹茲堡時常往來的有中國上古史專家許倬雲教授和通曉滿文的羅友枝教授(Evelyn Rawski;第四代日裔美國人)。1995年夏天,羅友枝教授夫婦在家裏請我吃烤肉,她向我透露她即將震撼東亞史學界的「新清史」觀點:滿清王室並沒有同化於漢文化,而是用不同身份統治一個多民族多文化的大帝國;漢族為主的中國僅是清帝國的一部分。我直覺上不贊成這個觀點,但是沒有能力反駁她,因為她說她曾閱讀過大量軍機處的檔案和清宮內廷的記錄。這說明,如果要對中國歷史做出新論述,必須要有相當的功力與準備。但是關於蒙古、新疆和西藏並不屬於中國,我就做了回應:辛亥革命後,列強要求中華民國政府承認清政府簽訂的所有國際條約;既然中華民國要承擔清帝國的條約義務(包括賠款、租界),為什麼不能繼承清帝國的領土呢?這又說明,區域研究人員既需要專和精(比如通曉滿文),也要從不同角度看問題(比如外交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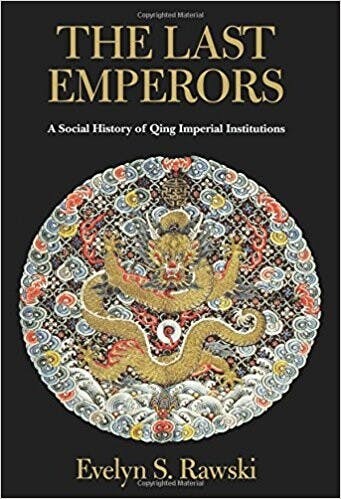
我和羅友枝教授辯論「新清史」觀點時,一場更大的辯論正在美國進行。那就是區域研究是否應該繼續發展?
有些學者在冷戰結束後把注意力轉移到人權、民主,難民、環保,發展模式等問題,認為區域研究有局限性。今天區域研究在美國的確已不如30年前那樣受重視,但是我認為,只要區域特徵對未來發展仍有影響,區域研究就不會過時。問題在於,研究結果是否客觀而可信。
寄望絲路探索
40多年前,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認為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是第一世界,歐洲各國和日本等是第二世界,亞非拉國家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應該聯合起來反對超級大國霸權。鄧小平1974年在聯合國大會上宣講這個理論時,我就坐在旁聽席上。當時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都欠發達,大多數國家的內部有民族和宗教矛盾,許多都和鄰國有歷史恩怨和領土糾紛。這些國家要怎樣才能團結起來反對超級大國,一直沒有答案。
2013年秋,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和印尼先後提出了建設「絲綢之路新經濟帶」和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這個被稱為一帶一路的倡議反映了世界的新格局,表達了中國對國際關係的設想。它提倡加強亞洲各地區之間、亞非之間以及亞歐之間的經濟和文化聯繫,並為進一步發展各地區和各國的經濟和文化,而增建各類基礎設施。為了達到以上的目標,各國應該共商共建共用;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的創立,就體現了這個原則。
一帶一路倡議或許可以被視為「三個世界」理論的現代版和具體化。兩者的共同點是把重心放在佔世界人口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不同之處則是後者以合作共贏取代前者的鬥爭對抗。

絲綢之路(Seidenstrassen)這個名詞是德國地理學家馮·李希霍芬於1877年首先提出來的,其動機是想要修建從德國到中國的鐵路。140年後,連接中國和德國的鐵路已經成為現實。但這只是促進絲路沿線國家經濟文化聯繫的初步成績,要真正實現一帶一路倡議,除了需要大量資金和技術,中國還需要大批通曉絲路各地情況的人才,以有利於各國的合作。
依我看,首先需要大批對絲路某地區、某些國家的地理、歷史、語言、宗教、政治、經濟等具有一般認識,又長於其中至少一項的人才。這樣的水準應該可以在本科畢業時達到,關鍵是課程的設計和教學品質的保證。其次,需要數量頗大的,能在一個特定領域研究某個區域或國家的人才。這應該需要完成碩士學位;通過訪問、實習或在地任職,他們應該能夠具有與某一國家或地區的人民和政府順暢交往的能力。最難培養的是將來能在政府、智庫、工商企業和高等院校工作的有專精知識,能提出新見解的人才。這些人應該需要攻讀博士學位,最好再經過一段博士後訓練。
目前中國高等院校關於西亞和非洲的人文課程,主要是傳授18─20世紀歐美學者所積累的知識。但是近幾十年來中國的考古和歷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外語教研方面也有出色的表現。在這個基礎上,中國學界應該與本地學者合作,在絲路各國展開考古與歷史的深度研究。亞洲和非洲比歐洲的文明史要久遠,亞、非洲各地一定擁有大量未曾發現的考古資源和歷史資料。今後在絲路國家修建基礎設施和進行地下勘查時,一定會有考古遺址出現;中國學者應該積極參與考察和保護這類文化遺產。此外,絲路沿線各地區和國家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民間組織等也都有待進一步釐清。
在社會科學領域,目前並不存在適合各國情況的普遍理論和統一實踐。任何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現代化都會受到地理、歷史和文化因素的影響。中國學者若要認真地進行對絲綢之路國家的探索,就應該從一帶一路的具體建設中獲取啟發與資料,開闢新課題和做出新論述。這不單是做學問,也是獲得絲路各國精英階層贊許的不二法門。
中國知識最大挑戰
我認為,擺在中國知識介面前最大的挑戰,是通過對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地區深入的觀察與分析,參照發達國家與中國自己的發展經驗,建構一套「發展中國家,應以合作互補,來促進彼此發展」的政治經濟學,闡述在當今科技水準和國際新形勢下的發展途徑。
無論是在人文還是社會科學方面,中國的高等院校都需要加強合作。但可能更急切的是校內不同院系之間的合作。目前各大學校內的組織架構和資源配置方式往往使不同的院系或是惡性競爭,或是不相往來。希望今後一帶一路研究不會這樣。絲路探索所需要的方法論和組織形式與各大學的傳統科系架構一定會有差異。根據我在不同國家不同大學的觀察,建立有學生名額指標並有相應預算的跨學科的絲路探索團隊(中心、所、院)是一個合乎實際的選擇。
有關部門可以參考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美國福特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經驗:投入可以有效使用的新資源是激勵大學調整架構的有效誘因。因此教育部,各相關政府機構,以及在國外拓展業務的企業,都應該協助各高等院校完成培養人才和創造知識的使命。
雖然大學需要財力資助,有一點至關重要:高等院校的基本職能是培養人才和創造知識,不是擔任政府或者企業的智庫。不容否認,一如當初美國的區域研究,今天進行絲路探索,確實具有現實性和戰略意義。但是絲路探索必須以治學的嚴謹方式為之;在進行與政策或時事有關的課題研究時,必須通過對資料的悉心搜集和科學分析得出客觀結論。希望從事一帶一路探索的學者們能在紮實的學術基礎上把自己的研究與現實相結合;切忌只對官方政策表態支持,甚至把研究報告視為寫「策對」、上「奏摺」。否則,這些學者就枉費了多年積累的專業知識,錯失了為中國,為絲路各國做貢獻的機會。
原刊於《財經》,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東方學、區域研究、絲路探索之二
本系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