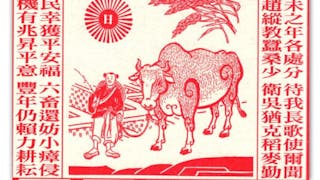9月30日以來,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有紀念張愛玲(1920—1995)冥壽百年活動。玲迷(張迷,即張粉絲)熱議她的情愛小說,更因她年輕時的傳奇而衍生對人生的遐想;對她深深思念並增添敬慕之情,恰如三國曹植(192—232)《洛神賦》云:「思綿綿而增慕。」
港大有網展 許地山學生
香港的紀念活動,由張愛玲母校港大的文學院比較文學系、美術博物館主辦,網展她在港大的相關文獻。1939年9月至1942年5月,她就讀於中文系,師從作家許地山(落花生,1893—1941)。
9月30日,比較文學系主任黃心村教授對媒體表示:「作為……她文學創作道路的起步點,港大及文學院有責任協力保存她的珍貴文獻。這個線上展覽只是一個開始。」
北上廣的主辦者,是北京的《新京報》,上海的澎湃網,廣州的《南方周末》。外國的BBC也有評論,還有視頻特輯《張愛玲百歲冥壽:香港戰火練就華文文壇巨人》(葉靖斯、關美青攝)。香港的報紙、網絡,卻沒有編印特輯。
就紀念上海/香港作家而言,這次的紀念活動規模最大。2018年徐訏(1908—1980)冥壽110年時,上海有《風蕭蕭》熱,把小說搬上舞台演出。
紀念張愛玲在四大城市舉行,是作家群的「自發推動」,官方未出面。北上廣的三家媒體都「姓黨」,但在文化層面相對比較包容,特別是《新京報》和《南方周末》;他們曾因與官方「主旋律」的差異而受整。
主辦者各自「幹活」,並無連線之說。北上廣的評論者,都避開被查禁的長篇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中篇小說《浮花浪蕊》,小心翼翼、避免惹怒當局。
在政治生態劇變下,四大城市能同時舉辦紀念,頗令人有「意外」感。其因之一,是與當前的政治主旋律不合拍,留下日後可能被秋後算帳的懸念。
夏志清推薦 張愛玲熱起
毛時代的「官修」新文學史(或稱現代文學史),不管是王瑤、劉綬松還是丁易的著作,都向黨性作家傾斜。1930年代或1940年代的上海作家、後來移居香港的徐訏和張愛玲,不入文學史;黃震遐(1910—1974)則因涉及民族主義受魯迅、瞿秋白圍攻,才入文學史受批判。
張愛玲作品的「復活」,得力於夏志清(1921—2013)教授的名著《中國現代小說史》。它的「社會功能」之一,既「搶救」了一批有才華的作家,如錢鍾書、沈從文和張愛玲,又讓大陸的讀者了解被封鎖的文學作品及其時代腳印。
夏氏稱張的小說特色,是「意象的繁複和豐富」,「處理人情風俗的熟練」(中大版342頁)。他推薦張的《金鎖記》和《秧歌》、《赤地之戀》,說《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343頁)。
徐訏作品的「復活」,則靠上海、成都等地一批教授和碩、博研究生的論文。
他們的「復活」,網絡粉絲之形成,研究他們的學術新浪,在在說明知識界和年輕「愛書者」尋求突破黨性文學的框框,嘗試擴大文學視野,從而了解真正的民國時代。這是尋找社會真相、追求知情權的社會激流。

上海風情畫 思索價值觀
在北上廣,張愛玲熱已積累了20年以上的動力,玲迷之多折射年輕一代的閱讀取向。對於出現此熱的因素,本文的解讀歸納為四點。
首要的因素,是歷史視野和上海風情。
在極權主義的社會,從列寧、斯大林的蘇聯,到後來東歐、亞洲的共產國家,都把文藝定位於為政治服務的工具。政治是指執政黨及領袖的權力地位、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舉措。黨性文藝之弊,是內容的偏向化(歌德)、單一化(階級鬥爭為綱)。
1980年代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使許多人對「外部世界」略有了解,且有持續了解的渴望。張愛玲小說描寫的時代跨度,從晚清到民國的上海、1950年代的香港。其中上海風情和富個人色彩的「傳奇」,頗吸引年輕人。較之黨性文學的階級鬥爭場面,上海風情引發的「往日情懷」,才是許多年輕人的「最愛」。
另一重要因素,關乎價值觀,特別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差異。
張的小說,着墨於人的獨立個體,個人追求自由、享受情愛、躲避政治災難、集體主義使人工具化的苦惱。
對於有思考力的讀者群來說,價值觀的探索啟發他們「再思考」。
破落貴族家 苦澀的夢幻
第三個因素是夢幻。
張生長於破落貴族之家(外曾祖父李鴻章是晚清大臣),承受家變、戰亂、紅色政治運動的折騰,面對前景不確定的困惑。她以文學為載體營造夢幻,如同曹植以《洛神賦》表達對洛水之神宓妃的夢幻:品嘗她「柔情綽態」,說「余情悅其淑美」。筆端有輕快的舞步,讓讀者也有夢幻的快感或糾結。
張的小說,寫了不少美麗或苦澀的夢幻。大都涉及命運無常、自由消失的憂患、人身安全的期望,這是現實生活承受壓力的一種釋放。套用佛洛依德(1856—1939)的分析,這是對現實不足的「補償」。她也以美夢寄以對價值觀的執着之情。
這些夢幻,讓當今追夢者略緩解現實生活的緊張,或「自我麻醉」。
寫浮花浪蕊 港人有聯想
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是小說的現實聯想效應。
前面提及的三部「禁書」,觸及「免於恐懼的自由」之命題。小說人物的對話,往往引起有機會閱讀者的現實聯想,昇華為作者的「預警」或溫馨提示。
《浮花浪蕊》是自傳式小說,背景是1950年前後的上海。它提到一位自由派女子對上海被接管的恐懼:
「她想是世界末日前夕的感覺。共產黨剛來的時候,小市民不知厲害,兩三年下來,有點數了。這是自己的命運交到了別人手裏之後,給在腦後掐住了脖子,一種蠢動蠕動,乘(趁)還可以這樣,就這樣。」(《惘然記》43頁)
從網絡留言來看,這段話引起香港網民「似曾相識」之感。這正是回視歷史下的現實聯想。
本文原題〈思綿綿而增慕 北上廣愛玲熱〉,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