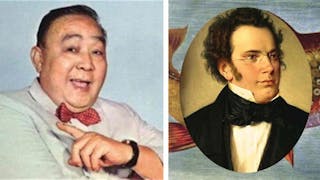浴火重生的鳳鳥
董啟章在2013年患上焦慮症,大半年後才好轉,「一半是由於寫作方面的問題,另一半可能跟兒子有關,照顧他多年,已覺得很倦,當時兒子開始念初中,成績較差,由於擔心兒子,積累多年的壓力,讓身體受不了……焦慮,主要是神經失調的問題。」
「第一次發病,病了半年,那段日子吃不下東西,血糖很低,弄得身體非常虛弱,常進出急症室。七月時書展有活動,也臨時被迫取消,因為進了醫院。」出院後,他恢復運動,游泳、散步,也做禪修……身體逐漸復原。
2014年,董啟章獲選為香港書展年度作家,「既又要接受媒體訪問,還要出席書展三場分享會,活動對寫作是干擾,可能太疲累,結果又發病。」
他一直抗拒服食西藥,害怕副作用,也擔心上癮,「我最恐懼的,就是吃藥會影思考能力,導致不能寫作。」他嘗試過很多不同的療法,看過中醫,也嘗試針灸,還試過禪修,「禪修是好的,可惜未能治病,我身體最差的時候,中醫對我也無效,全身乏力,走路幾乎也要扶着柺杖,說話也沒氣力……」當時他在中大擔任兼職講師,由於沒氣力講書,只好在家裏錄音,幾分鐘便要停一停,然後帶着錄音到課堂上播放……可見身體多虛弱。
直到2015年,逼不得已,他才踏出第一次步,看西醫吃藥治病。
對症下藥果然奏效,「不過,單靠藥物,並不能恢復健康,同時要調整個人的心態,必須盡量放鬆自己,以前我對寫作的要求好嚴格,拼命盡力去寫,故負擔很重。」經悉心調理後,結果康復了。
從陰霾中步出,2016年,董啟章開始重新上路,寫作開展順利,他對自己的要求,已經不一樣了。「對於寫作,我已沒有什麼包袱,比較輕鬆自如,個人的心態轉變了,多少有點『浴火重生』的感覺。我覺得每本書各有意義,亦有不同的目標,達到即可。寫作沒有絕對的標準,不能永遠追求『勁』,也不能不斷的追求超越……當下的經驗,已是自足。」眼神漾着笑意,他輕快地道出心聲。
重回寫作的軌跡
隨後幾年,董啟章寫作不輟,小說一本接着一本的出版——《心》(2016)、《神》(2017)、《愛妻》(2018)、《命子》(2019)……除了《愛妻》獲第八屆「紅樓夢獎」決審團獎,其餘三本在「香港書獎」都榜上有名。「我是獲得『紅樓夢獎』決審團獎最多的作家,一共三屆!」他不忘自嘲。
去年出版的《命子》,小說的第一部分〈命子:果〉寫的就是兒子的執着,為人父母的甜蜜無奈。談到兒子,「他不擅社交,朋友不多,在家對着我們,卻滔滔不絕,面對陌生人也不會感到害羞。後來上到高中,卻交了幾個好朋友。他很固執,興趣專一,不愛閱讀,喜歡搭巴士,異常地沉迷於研究巴士的型號、路線……」新果今年已18歲,剛進科大念理學院,雖然入不到心儀的地理系,但他選讀的科目,全是與地理相關的,如環境保護、地球資源、海洋生態等。

「兒子不像預期一樣,對父母的刺激當然很大,我們感到很苦惱,但換個一角度,可以看闊一點,人其實可以有很多可能性,他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有自己的發展,也可以為我們帶來啟發。」從孩子身上,可以學習到很多,甚至為他帶來創作靈感。
驀然回首,剛寫小說初期,在90年代,他自言受到卡爾維諾的影響,「遊戲式的想像力,將一些東西推到很遠很遠……」
到了2000年前後,他開始受到大江健三郎的衝擊,「我在作品中,注入政治社會的元素,此後十多年,仍深受他的影響。」此外,他也喜歡夏目漱石,欣賞那種「不刻意的幽默感」。
至於香港文學,他視劉以鬯、西西和也斯,為三大小說家,認為「《酒徒》、《我城》、《剪紙》三大經典,是香港文學的標記。」
董啟章的碩士論文,研究普魯斯特,當然也喜歡其作品,「我一直鍾情長篇作品,可能就來自他的影響。我覺得『長』才能表達我想說的東西。我不直接受意識流手法影響,但會特別注意,他寫生命片刻的觸覺,其中的幽默感也很吸引。同時,在小說中,他融入很多知識,如文化、藝術……以一種大融合的方式呈現,對我的影響甚大。這種影響,不是表面的風格,亦不是行文、語氣、腔調……」
他閱讀的作品,不計其數,亦從中汲取不同的養份。他愛在作品中,融入很多知識,他認為閱讀是一種再創造,「透過閱讀,我豐富自己的知識,再利用知識去寫這個世界,將知識融入小說中。寫《家課冊》時,我選了十科來寫,自己念文科,於是就買回一大堆理科教科書,例如化學、生物、物理等,然後擷取書中的素材,寫成故事。」他創作的思路,就是將知識轉化為想像的東西,知識、思想,構成了說故事的動力。
從「南大」到後人間
剛出版的《後人間喜劇》,是董啟章最新的小說,也是他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當駐校作家時開始醞釀的。從2018年8月初到12月底,他住在大學校園裏,南大湖畔一棟白色舊式小樓房的三樓。
他本來已停藥大半年,也許因為環境的轉變,焦慮症又來襲,「事實上,當駐校作家,於我來說,全無壓力,獨在異鄉為異客,是表面的誘因,主要是因為體質弱了。2009年,我也曾到過美國幾個月,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完全沒事,可能當年還年青,無論如何緊張,對身體也沒多大影響。」
小說的大部分靈感,是在駐校期間產生的。他初到南大,人生路不熟,整天困在校園,無意中看了幾齣韓劇,其中一部《鄰家律師趙德浩》,是常見的通俗劇,情節卻甚為精采。
除了教一門創作課,他大多留在宿舍裏,苦讀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腦中冒出了按照康德的先驗論,打造一台「康德機器」的可能性,一部科幻小說的雛形便在腦海中出現。同時,他也開始閱讀「模控學」(Cybernetics)的書。大概到了駐校的中段,思緒中突然出現「胡德浩」這個名字,無庸置疑,名字是從《鄰家律師趙德浩》來的,但胡先生不是律師,他是研究「模控學」的科學家。如此這般,既有科幻部分的概念,亦有了故事部分的人物,一部新小說的胎兒慢慢成形……「我當時的主要任務,是要讀完康德的三大批判。這個任務,持續進行到第二年的年中,回港之後半年。」

2019年的6月,社會形勢急劇變化,思想的衝擊和情緒的波動,令他無法專心寫作,準備好開筆的小說,也一拖再拖,「故事本來已經構思好,但在如此紛亂的情況下,如何處理這部小說,令我費煞思量。一是完全拋開香港當前的經驗和感受,寫出完全虛構的故事;或將故事置於當下的心境寫出來。最後,我索性將小說抽離現實,但保留若干的聯繫,這是個相當新的嘗試。」
董啟章早就決定把主要場景設定在新加坡,但對於香港部分,卻舉棋不定,他決定把兩邊寫成平行世界,主角則從一邊跑到另一邊,經歷了如夢似幻的人生。
「這是我第一次主要場景不是香港的小說,也是第一次全面動用了通俗小說的形式。書中的主要人物,無論名字、外形、性格,全脫胎自《鄰家律師趙德浩》,好像我請了那批演員,去演一部人物相似、題材卻完全不同的戲。」小說從去年10月中開筆,到12月底完成,共24萬字,只寫了70多天。

「小說要處理的社會問題,跟2019年下半年的社會狀態,亦有所呼應,我雖然沒有直接寫香港,也不深入處理香港的問題,可是,小說要探討的問題,就是——什麼是理想的社會制度?究竟要高度管治,還是要聚焦經濟的發展?能否通過科技去建構理想的社會?」對於新作,他細細道來。
新加坡人民的日常生活,安穩而舒適。前總理的影子,在小說中呼之欲出,「我已盡量寫得比較含蓄一點,希望不會冒犯他們吧。」他微微一笑,繼續說下去。
對於新加坡,董啟章比較熟悉,在駐校之前,已到訪多次,因為兒子在十多歲時,開始喜歡這個城市,一個很有條理、很整潔,也有特色的地方。「兒子不愛看古蹟,也不愛大自然,他不會欣賞歐洲古老的教堂,也不會欣賞奈良京都的寺院,但他喜歡保育得很好的歷史建築,如博物館。」
小說中經常出現大段哲學性、思考性的文字,他說:「較之於自然史三部曲,我已經忍手。」這倒是不爭的事實,有目共睹!

文學創作二三事
董啟章很謙虛,自稱不懂哲學,「我愛閱讀哲學書,好像小說般去看,透過構思,將哲學的片段,化為情節、意象……例如一邊看康德,一邊構思小說。我以前最愛看的是科學理論,屬科普層次那種書,例如演化論,從達爾文開始,直到當代主要的著作。」
談及寫作,他直言不諱,「寫作當然來自生活,加上思考。看書是為了思考,寫作是不同層面的結合。」頓了一頓,他繼續說,「寫作總離不開個人的經驗,而個人受到社會的影響亦相當大。小說跳不開人的親身經驗與社會狀態。作家,不是隨意所之,愛寫什麼便寫什麼,碰到什麼就寫什麼,時代與個人的經驗很重要,個人的經歷,亦與社會分不開,私人空間與集體層面的東西,一定互有影響。」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說:「時代賦與我題材」。
昔日,他寫小說,沒有特定的讀者對象,「總之,我就是寫成這樣的了,喜歡看的便看……」近年,他的心態已有所轉變,希望吸引多一些讀者,寫作時會想一想「這個位應該收斂一點」,又會考慮,「讓這個位有趣一點」,甚至嘗試在小說當中混入通俗的元素,帶點喜劇的味道。
「創作自然史三部曲時,曾經有過獲獎的期望,我要求自己寫出來的東西,『勁』到與當代的名家可以比拚。」由於前兩本書在「紅樓夢獎」中落敗,所以寫第三部曲時,他就考慮是否還欠些什麼,「能否寫得『勁』一點,落重啲藥,打低高手……」他承認這就是心魔,給寫作帶來負面影響。
前幾年,他在病中學禪修,有一陣子,也看些佛學書刊,如一行禪師、詠給明就仁波切的書。後來,他覺得莊子的思想比較適合自己,於是轉看《莊子》,學會「坐忘」,他解釋:「最舒適的時候,就是忘記自己正在做事,忘記煩惱,帶來釋放。」
董啟章提到《莊子‧雜篇》中列禦寇的故事,他是神射手,已臻「不射之射」的境界,「對於我來說,希望能做到『不寫之寫』,不着緊自己寫什麼,不為別人的讚賞,也不為贏取獎項而寫。」然後,他拈出契訶夫的作品為例,「他的短篇小說寫得極好,但不易分析,亦難以學習,也許,這就是『不寫之寫』。」
作為小說家,「對於自己的作品,我往往會『貪新忘舊』,最喜歡的,當然就是最新的作品。其實每部作品都有其優點,我從不會否定以前的作品,凡事總有進步和演化,我最滿意現在的自己。」所謂「當下即是」,大抵就是如此。
「小說筆下的主角,多少有自己的影子,至於其他人物,基本上都有原型。我寫小說,好像電影導演casting演員一樣。在日常生活中,我通常不會太注意周邊的人,偶然留意到某些人物,他們的形象、外貌、神情、氣質,特別吸引,便會認定這是我的potential actor,碰巧有適當的角色,便call他們出來,納入小說中。如《後人間喜劇》中,女兒的形象,就是由兩三個人混合而來的。」說到小說人物的塑造,他娓娓道來。
至於人物對話,「我會visualize兩人相遇的場面,好像置身現場中,人物會互動,一問一答,對話自自然然就會寫出來。」
不少作家,作息有時,生活規律,董啟章也不例外,「以前帶兒子上學,習慣早起,現在也如是。7時多起來,到公園散步45分鐘,然後吃早餐。回到家裏,9點多開始寫作,到1點前,才出外吃頓午飯。稍事休息後,下午會繼續寫作……晚上,通常在11時多便睡覺,最遲不會超過12點,我絕不會捱夜。」
每個人,總有自己心目中的好小說,而站在小說家的角度,什麼是好小說?
「這是個不易回答的問題,很難一概而論,簡單來說,我認為好的小說,就是既好看又有意思的。有些小說很有意思,但不好看,例如一些現代主義的巨著,艱深冗長的句子,必須經過特別文字訓練的人,才能欣賞,一般水平的讀者,難以進入其中。另外,也有些通俗作品,讓人可以享受閱讀的愉悅,但沒有帶來衝擊,引發深入的思考。例如我的『自然史三部曲』,有意思,但不易看……」他指出二者兼備,才是好小說。
「小說家不能拒人千里,不是要討好讀者,但我希望吸引他們進入我的小說世界,而且獲得享受,享受之餘,也要有所啟發。」他一再強調,「我現在就朝着這個目標寫作。」

繼續以小說發聲
認識董啟章,久矣!
然而,跟他面對面暢談文學,倒是第一次。眼前的小說家,衣著素樸,深藍上衣、栗色長褲,頭上戴着帽子,一如往昔。他談吐溫文,說話時聲音很輕,真摯的眼神,誠懇的話語,讓人感受到認真的精神。也許,我們的文學興趣相近,竟聊了三個多小時……
他與一眾文友,近年在灣仔創立「香港文學生活館」,提供文學課程,舉辦文藝活動,為推動文學而努力。最近,他還粉墨登場,拍攝視頻,推介世界名著,如《源氏物語》。
從去年起,他開始閱讀牟宗三先生的著作,「我已看了八九成,他的書很好看,好吸引。我可能會借用他揮灑的形象,塑造一個小說人物……」
董啟章很欽佩牟先生,「他專注個人的研究,作品一部部的寫出來,全是哲學巨著,可說圓滿地結束。」仰之彌高,那一代的大師,如唐君毅、牟宗三等,已一一離世。
有人說,這是個沒有大師的年代。董啟章卻不盡同意,「事實上,是這個時代,這個社會,不容許大師存在。社會將人變成營營役役的文化生產者,不追求高度,也不鼓勵你去追求,只要求你很快地生產一些所謂『有用』的東西。現在的社會制度扼殺了人才,不讓他們變成大師。」確是一語中的。
現時,他正在醞釀新作,計劃寫一本有關儒家思想的科幻小說,「我希望透過作品,帶給讀者全新的經驗,當人的想法改變,人生就會隨着改變。」
文變染乎世情,作家要反映時代,更要超越時代。
我深信,董啟章一定會繼續以小說發聲,探索和回應世界,為讀者寫出更好的作品。

董啟章專訪二之二
本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