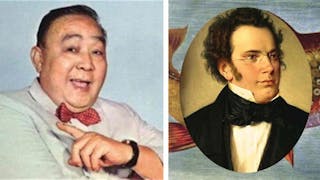踏入虎年,偶閱《明報》副刊,區聞海醫生的專欄「明明如月」赫然入目……
自大學時代開始,閱讀《明報》多年,已成習慣。仍記得,區醫生以前的欄名是「大夫小記」,他停寫《明報》專欄久矣,想不到多年後,又再執筆。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
「明明如月」出自曹操《短歌行》,「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區大夫真是性情中人!
「再來時,自己走了十年人生路,香港經歷了多少急風驟雨?」在復出首篇〈再來時〉,他如此剖白。久別相遇,不禁令人衍生「世事茫茫難自料」之慨。
第五波疫情像巨浪滔天般洶湧襲來,面對病毒Omicron,人人難免「猶兮若畏四鄰」,區醫生在報章上發表的文章,也多涉及他對疫症的看法……至3月初,閱〈模模糊糊退休〉,始知他第二次退休在即。
我撰寫專訪,始於2015年,訪問的對象,大多是文藝界圈中人,卻從未訪問過醫生。區醫生是位專欄作家,曾出版多本醫事散文,還有其他的著作。在2019年3月,他陪伴西西到University of Oklahoma接受紐曼華語文學獎,支援她作長途之旅……有緣「伴西西同行」,真是一個好故事!
就在這瞬間,我決定要訪問區醫生。我不認識他,於是請一位在中大任教的好友幫忙牽線,輾轉聯絡到他。他很爽快,當下便答應了邀約。
然而,那一陣子,疫情嚴峻,每天的確診數字,高達幾萬宗,大家只能透過視像見面、交談。我們約好日期、時間,便在ZOOM線上,從小時候的經歷聊起……
花果飄零,靈根自植
區聞海原名區結成,早年居於荃灣區,在大窩口的小學念書,中學時入讀喇沙書院。那些年,中學分文理科,成績好的學生,一般都被編入理科班,喇沙書院亦如是。「從中三升上中四,選擇文科或理科,多少是由成績決定,成績偏向那方面,便走向那方。當時,我並不懂得規劃,只是順着潛規則而行,說不上有清晰的意向。」
「讀A-Level時,我只能選擇Engineering或Biology,沒有第三條路,前者做工程師;後者則念醫科。」他自言作出了負面的選擇,一直以來,他都不喜歡純科技的東西,不太喜歡機器。「在中四、五時,很多同學已開始去深水埗買零件砌『原子粒收音機』,我砌出來的收音機亦會響,但我不大享受這個過程。」就因為這樣,他走向「生物」一途。考完AL大學入學試後,他估計當時的成績,大概也能入讀醫學院。
當時喇沙設有一文科班,學生多是非中國人,有英國人、葡國人,也有南亞裔的,如印度、巴基斯坦等,他們不讀中文,念法文。「我有很多相熟的同學在那一班,從他們得知外面的世界,原來有一種大學,課程比較寬廣開闊,實施Liberal education!」同學申請外國大學時,他亦嘗試申請。
區聞海家中有八兄弟姊妹,他排行第五,有四位姐姐。父親在荃灣開一間小店,做點小生意,家境並不太好,「大姊是當年的文青,成績非常優異,可以升讀大學,但她選讀師範學院,然後出來當教師,幫補家計。」他讀中學的時候,在書架上找到姐姐的藏書,開始閱讀余光中的散文、新詩,然後看白先勇的小說。
當時,擺在他眼前的,有兩個選擇,一是進入香港大學讀醫科,另一就是往外國念書。「到外國留學,學費比較昂貴,雖然有獎學金,但也感到吃力,家人對我一個人在外地,亦有點擔心。」
年紀輕輕的他,卻渴望跑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藉以增廣見聞。「我選擇到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升學,主要是想接受博雅教育,不想太快便跳到醫科這個專業。」順着自己的好奇和嚮往,他走上這條路。

到外國念書,不單止是大學的問題,而是要面對文化的轉變。他說:「第一年是蜜月期,主要因為自己想往外闖,那時亦大開眼界,可修讀人類學、社會學,甚至哲學……樣樣都『掂』下,而且又可結交一些美國同學。」
過了2、3年,他對美國社會的新鮮感已淡出,開始思考不同文化、不同價值觀的社會之異同,探索當中是否有矛盾衝突之處。
在外國生活的時候,他看的課外書,大多是中文的,「也許,有一點思鄉的情緒,同時,我亦想『尋根』。那是火紅的年代,縱使不談政治,也會引發很多文化上的思考。」他多閱讀一些論及中西文化異同的書籍,例如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的著作,還有其他有關文化的書籍。
閱讀之餘,加上個人親身的經歷,因而對不同的文化或價值觀,有比較深入的體會,亦開始思考身份認同的問題。唐君毅說過「花果飄零、靈根自植」,對此,他也曾思考過「這些文化的根是什麼?與自己有什麼關係?」等問題。
同時,他開始考慮切身的問題,「進了醫學院,完成了7年的醫學課程後,將來會走哪一條路?」
回港行醫,得償素願
「到美國後,我反而多寫了中文。」區聞海在美國時,曾投稿《明報月刊》、《七十年代》等雜誌,因此認識了胡菊人先生,「他扶掖後進,不遺餘力,對於我們這些對文學有興趣的年青人,會用亦師亦友的方式予以提點。我跟他時有書信往還,好似筆友一樣。」
在大學時,一方面在西方的社會念書;而另一方面,他亦開展了一個與中國文化關繫的空間。人在美國,反而更認同中國文化。結果,取得醫學博士的學位後,他便決定回香港發展。
「如果留在美國,可以想像到自己的路……生活比較安穩,先找到專科的培訓職位、取得工作簽證、然後取得綠卡、入籍美國,接着成家立室、養育下一代。」
他曾於1977年的暑假,回港探親時,認識了女友(即現時的太太),彼此魚雁互通,長達5年之久。「留在美國發展,跟我們對文化的認同,似乎不大吻合,所以決定回港發展。雖然有其他個人的理由,但肯定這是其中一個因素。」區聞海接着說。
一般人的選擇,大多留在美國找工作,待取得專業資格後,才考慮是否回港,但他也想到,如果到了第4、5年,安頓下來,很少會走回頭路,再返回香港發展。他心裏想,「如果要回港,一定要及早抉擇,所以作了一個比較衝動的決定。」香港不承認美國的醫科資格,選擇回港,要重新考試、再實習,而且當時還未有專業資格,回到香港後,可能會面臨半失業的狀態。
「在醫學院時,我曾投稿到香港大學醫學院一份中文刊物《啟思》,由醫學院的學生辦的,有點像《中大學生報》,大概是喜歡文藝的醫科生搞出來的。」因為投稿,他認識了生化系的Teacher Advisor黃志超博士,一位擁有文人色彩的老師。
「我們互相通信,當他知道我回港發展後,便替我着緊,還主動說看看其學系有沒有Teaching Assistant的職位,讓我回來後即有工作可做,不用投閒置散。」對這位筆友的關顧,他心存感激。
可是,他回港前幾個月,當時正值越南難民潮,香港啟德難民營的紅十字會醫療中心,想聘請一位懂得說廣東話的醫生,但因為薪酬只有一半,所以請不到合適的本地人。
他寫信申請這個職位,結果被錄取,「我回港後第一份工作,就在這個醫療中心當醫生。這份工作,對我來說,可說是天賜良機,因為我在美國時,也動過念頭,想到泰國邊境的越南難民營,做國際救援醫生。」醫學院的副院長,力勸他要考慮清楚,因為他只是個醫學生,缺乏臨床經驗。故此,啟德難民營的工作,總算讓他一償夙願。

「女友念護士課程,但她對於中國文化,亦深感興趣,曾到中大校外課程聽霍韜晦先生講佛學、中國哲學等。」他仍記得,在1979年的暑假,曾隨女友往霍家聽佛經,認識了霍先生。其後,也曾到「佛教法住學會」,聽唐端正和霍韜晦兩位先生講授的課程。
區聞海在1982年回到香港,隨後,在「佛教法住學會」讀了一個碩士課程,研究東晉慧遠,淨土宗的創始人。這篇碩士論文,後來也被韋政通教授編入《中國哲學家叢書》(台灣東大出版社)。
他讀得很投入,也很認真,不單只是為了興趣,而是深入地研究。「如果我不念醫科,最想讀的就是思想史。霍先生曾說,可以介紹我到新亞研究所,跟隨徐復觀教授讀思想史。可惜我回來之前,徐教授已離世,好像跟新亞研究所擦身而過。」後來他也曾到訪新亞研究所,見過牟宗三先生和趙潛先生。
「那幾年的過渡期,非常順利,滿足了我想讀中國文化思想的心願,可謂素願得償!」他努力不懈,闖出自己的人生路,那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摸索,而非一些外在的人生規劃。

科學知識,人文關懷
1983年,區聞海在香港通過醫科考試,然後實習一年半,至1985年初,正式進入政府醫院工作。「我先在九龍醫院的『精神科』做醫生,當時沒有人願意入精神科。我是新人,所以被編入內。」其實,他最心儀的是「老人科」。不過,他強調,「我也喜歡做精神科醫生,因為治病,除了開藥,與病人溝通,也很重要。我雖然剛剛畢業,但去美國走了一轉,積累了點人生經歷,也嘗過甘苦,對於生命,亦有一些個人的想法。」
他也不諱言:「對於精神科專門的東西,我懂得不多,但憑着這些經驗和想法,可以輔導、開解病人,也比較容易跟他們的家人溝通,幫到他們。」
醫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的說法,好像已成陳腔濫調。多年來,區聞海仍在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醫學與人文學科,是『分』,抑或是『合』?」醫生需要具備邏輯思維、科學知識,最好還加上人文情操,對病人仁心仁術⋯⋯還是,醫學本身已內蘊人文關懷成份,二者並不是分開的。
他指出,「醫生在治病之餘,還要關心病人的生活,醫病與患病本身不是純科學的經驗。」以這幾年的疫情為例,大家可以看到,確診、隔離⋯⋯箇中困難、辛苦的經歷,並非純粹是與醫學相關的,這也影響了他的看法。
「這不是因為我念佛學,能勘破生死,而是我始終覺得,醫病不單是科學問題,而是關乎一個人的問題。」區聞海心儀老人科,也反映了這種傾向,他認為老人家患上心臟病,或高血壓,不能單靠藥物治療,患病往往是一個經驗或經歷,並不單純是「器官」問題,而是涉及「人」的問題。
「說得具體一點,香港的疫情持續蔓延,老人家卻拒絕『打針』,社會將它簡化成一個科學問題,不斷重申『現時已有很多科學證據,證明疫苗是安全的,可以保障人的性命』。為何老人家不相信這些證據,仍然不肯『打針』?為什麼他們如此頑固?甚至有人覺得他們很自私,不為社會着想。」他拋出連串問題。
區聞海一再強調,「我們要有寬廣的視野,用人文的方式去看問題,不能將它簡化為純科學的答案。如果能了解老人家多一點,你就會知道『打針』的背後,有很多『人』的觀念在內。」
他又指出,一般來說,香港的院舍環境不太好,雖然可能有很好的員工去照顧老人家,但生活質素如何?大家有目共睹。
抗疫已超過兩年,仿似作戰一樣。「我們一直只關心數字,有多少人未『打針』?百分比是多少?但長者的生活素質,有人關心嗎?8、90歲的老人家,自然壽命還有多長?他們已躺在院舍好幾年,而且被困了兩年,在這段期間,還不准家人子女孫兒探訪⋯⋯」他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頓了一頓,繼續說下去。
「教育長者,讓他們知道『打針』的重要性,但長者感受不到真正的關心。『打針』可以減少90%的死亡率,可讓他們多活幾年,這對他們來說,有什麼意義?他們還有什麼人生希望?純粹講科學數據,是沒有意義的。」他語重深長地說。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說到這裏,區聞海提起一則報道,由於仍有院舍長者或其家人,反對老人家接種疫苗,於是就有醫生學者建議,「將他們帶去另外一處地方圍住,甚至以後不讓他們享用老人服務。」區聞海慨嘆,為何言論如此涼薄,人生到了晚年,是否就應該得到這樣的待遇?
他的提問,讓我想起日本電影《楢山節考》,故事講述日本古代信州,在一個貧苦的山村中,由於糧食長期短缺,老人一到70歲,就要被子女背到山中等死,以供奉山神。這齣電影,當年亦引發不少討論。
他一直在思考,醫療的本質究竟是什麼,「醫病救人是為了什麼?人會病、也會老,我們不能抽象地思考『生老病死』的問題,對於疾病,也能不單純工具性地去進行治療。人生的最後階段,亦不能簡化為生物學的問題。」
他提到新亞書院,以「誠明」為校訓,所謂「誠則眀矣,明則誠矣」,二者不能分開。「人文關懷並非可有可無,除了科學醫學外,對心靈的關顧,其實很重要。我們要了解病人對疾病的恐懼,以及對健康人生的嚮往。」他極其盼望,人們能夠完整地看待一個生命。

對很多人來說,這兩年的經歷是非常困難的,大家都配合政府的措施,刻苦抗疫,有如作戰一般。「在這個過程中,對於抗疫,可有一個比較人性化,而又有意義的論述?究竟有沒有一個整體的說法?我們正在打一場什麼的仗,achieve了什麼?」連串的問題,惹人深思。
「總之,我們每天都要服從規矩而過活。這些規矩,據說是參照疫情數據而設訂的,也有科學的支持,普通人無法跟專家辯論。大家只能隨着官方的說法,從以調適自己的生活,循着醫學邏輯而行。如果像『沙士』般6個月便完結,問題可能不大,但已經歷了2、3年,而且還沒完沒了……」區聞海認為,必須要將抗疫,聯同生活的意義一併思考,如果不是這樣去想,就永遠處於「驚弓之鳥」的狀態,因為疫情可能會再爆發。
「不單止是老人家,身邊的年輕人,對於人生價值的體現,他們該如何思考、如何探索?除了社交不斷隔離之外,大家還可以做什麼?」也許,處於非常時期,不可能奢談這些問題,但區聞海覺得,無論如何,面對這些問題,也需要有個想法。
「3月初,染疫的確診數字,升到7萬宗後回落,相信已經差不多『見頂』,是否可以開始思考一下,社會如何重返正常的生活,但每天仍然聽到『不可掉以輕心』的訊息,因為疫情隨時反彈……我們彷彿永遠被綑綁着。」他搖了搖頭,苦笑地說下去。
他繼而指出,不少市民已經注射疫苗,亦有人估計,香港已有超過150萬人染疫,康復後就有抗體。「我有一個親戚,一家三口『中招』,全都沒有嚴重的病徵,也康復得很快。他們已有抗體,似乎可以『逃出生天』,但限聚令依然存在,不能跨家庭探訪,下午六時後,也不能在外面吃東西。種種的限制,不容許他們重過開放的生活,而社會經濟亦不住地衰退⋯⋯」他淡淡道來,不慍不火。
「社會是否可以逐步開放?『疫苗氣泡』的概念,其實是可行的。為何每天仍緊緊盯着數字,不斷的擔心?這涉及我們如何看待人與疫症,人與疾病的關係。」他反覆地說,這絕非純科學的問題。如果學者專家,未能意會其重要性,就會永遠被困於純醫學技術的思維之中。

人力資源,素質安全
談及個人的發展,區聞海說:「我還未在九龍醫院晉升顧問醫生之前,念了一個醫學行政碩士學位,這是一個遙距課程,由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開辦。」
當時,香港很需要醫學管理方面的人才,開辦這個課程的目的,是為了醫管局的成立。「當時的同學,有很多『猛人』,例如高永文、何兆煒醫生等。我只是一個『卒仔』,純粹為了興趣去讀。」他認為醫學管理與整個醫療系統關係密切,故此對於一些比較宏觀的,關於醫療管理方面的專業知識,深感興趣。這個機緣,又為他開啟了一扇門,他在醫院管理局中,逐步轉往擔任管理層的工作。
在2010年,他被調往醫管局做人力資源總監。由於當時的管理層與前線工作者之間存在矛盾,如屯門醫院有醫生醞釀工業行動,護士也有很多怨言,流失率亦相當高。
「當時,在總部做人力資源的主管是澳洲人,他沒有續約,返回澳洲定居。」他當年已是九龍醫院的院長,工作得很開心,也想做到退休為止。
當時醫管局的主席胡定旭,是他的讀者,一直閱讀他的專欄。事隔多年,他仍然記得,「當時我和太太去美國旅行,先陪她去UCLA開會,然後在西岸探訪一些老朋友、舊同學。」剛剛渡假回港,便接到胡定旭的電話,「他說想見見我,於是我上了總部,與他談了半個小時。他說希望我可以幫手,兼做HR主管,大約是三至六個月,讓醫管局有足夠時間,可以聘請到一位全職的專業人才。」結果,他走馬上任,兼任院長與人力資源主管的職位,「我一『埋位』便開始救火,梳理前線員工的情緒,處理管理層與前線之間的問題。」
「我覺得義不容辭,當醫院院長之時,我對於人力資源,也略懂一二,但不算專業,所以邊學邊做,亦學會了不少。當上HR主管後,對醫管局的問題,例如醫療制度、醫院員工等問題,也有較為通盤的了解,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驗。」如此這般,他便一直在總部工作下去。
至2014年,區聞海出任醫管局質素及安全總監。「這一次,也算是臨危授命,因為那位同事,想重返原來的崗位,不想再做領導行政的工作。」
驀然回首,「上天眷顧,我的人生中,遇上好幾次的轉折,雖然有些辛苦,但也有所得着。在人生不同階段,我還有機會可以學習,並作出嘗試,實在非常幸運。」人生於世,能夠學到老、做到老,也是一種福份。
醫學倫理,閱讀札記
2016年12月,區聞海在醫管局退休後,復於2017年3月加入香港中文大學,擔任生命倫理學中心總監,積極推動大眾關注生命倫理的議題。
5年後的今天,他再度退休,但他仍會在中大醫學院當顧問,也會繼續教授「醫學倫理學」。
「我在2012年停寫專欄,然後開始寫網誌。想不到,相隔近10年,再寫副刊專欄,不是偶然也有些偶然。」人生的際遇,實在很奇妙。
「每個人的背後都有自己的故事,我個人的故事,稱不上特別。可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故事,折射出不同的經歷,就反映了這個時代的面貌。」他如是說。

訪問那天,區聞海已經退休一周,亦開展了未來的計劃。「多年來,我看了不少醫學倫理及生命倫理的書籍,也搜集了大量相關的資料。現時可以好好地消化一次,融會貫通,再以閱讀札記的方式,寫一套筆記……」構思中,他預備將以前讀過的材料審閱一次,然後寫一本閱讀筆記,整理一套Notes on Medical Ethics and Bioethics for Teachers and Health Professionals。
「我未有出版計劃,這不是『雞精』書,亦非文學書籍,相信沒有出版社感興趣。」他會考慮將其中一部分,作為開放資源,一部分送給中大醫學院,讓日後的老師作為教學參考。
正如區聞海所說,像他一樣,在臨床醫療倫理和人文哲學等範疇,皆有所涉獵的人,確實比較少。
「醫療倫理有普世的一面,但下筆時,我可以將這份筆記置於香港的場景中,亦可同時反映這個時代。此時此地,一個像我這樣的人,有這樣經歷,能接觸這麼多的範疇,可算十分幸運,就應該當仁不讓。這個時候不做,更待何時?」

今時今日,醫學倫理是個成熟的學科,也有上佳的參考書可讀。「可是,在香港的脈絡中,帶點文化視野去看醫學倫理,還是比較特別的。我很想將它寫出來,雖然未必即時有用,但日後總可以用得着。」他現時已開展工作,而且尚算順利。
亦醫亦儒,「小心」樂事
眾所周知,區聞海任職醫生,卻愛文字創作,在美國念書時,已開始投稿,也拿過青年文學獎,以〈編織〉獲新詩高級組優異獎。愛詩的他,亦曾於醫管局舉行過「午間詩語」講座。

多年前,我已是他的讀者,然而,跟他面對面,在網上平台傾談,倒是第一次。我們早年的學習經歷,亦有點類似,中學時代,我念的是理科,跟他一樣,數學的成績比較好。那些年,我們的閱讀經驗也相近,余光中的散文、新詩,白先勇的小說……都是當時的課外讀物。
升上大學,我入讀新亞書院的經濟系,一年後,順應個人的興趣,不理會師長的反對,轉到中文系,且副修哲學,除了「魏晉玄學」、「宋明理學」……也修讀過霍韜晦先生的「佛家哲學」。
區聞海回港後,亦曾在「法住」念碩士,論文寫的就是東晉慧遠,而且差點就進了新亞研究院。
幾年前,他當上西西的「伴行醫生」,陪同她前往美國接受文學獎。事後,他曾撰文,以「小心樂事」來總結這次旅程,還說「最輕快的一刻其實是回到香港」,過程愉快,也有點壓力,實在不言而喻。第一次退休後,2017年,他出版《有詩的時候》一書,從馮至到卞之琳,從九葉詩人到七月詩人,從余光中到西西,為讀者細述中國新詩和詩人的小故事。

3月中旬的一個星期日,從早上10時半到12時半,我們聊了兩個小時,從他求學時代的心路歷程,談到醫院、醫管局的工作,說得更多的──是當前的切身問題,他對香港疫情的看法,突顯了他對生命倫理的關注……
區聞海談吐溫文,神情懇摯,既有文人的幽微細緻,亦有醫生學者的審慎認真。訪談結束後,我關上電腦,腦海就浮現「儒醫」一詞。
宋代的文人,大多通曉醫學,如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沈括、蘇軾、陸游、朱熹、辛棄疾等,幾乎到了「無儒不通醫」的地步,但他們都不是儒醫,只是「儒而知醫」而已。
醫生原是一種很專門的職業,儒者,讀書人也。「儒醫」,指的是具有一定文化素養的醫者。
由此觀之,區聞海,不正正是一位「儒醫」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