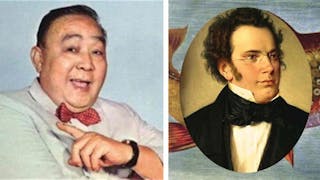榮園府,有一朵驕傲而鮮豔的玫瑰花。她,在人們沒留心的當兒悄悄開放。她,「又紅又香,無人不愛」。但是,請不要冒失地去碰觸,她鋒利的刺,會提出嚴厲的警告。
她,就是賈探春。
在第三回,這位「削肩細腰,長佻身材,鴨蛋臉面,俊眼修眉」的少女,文靜地出場。文靜,並沒有禁錮性格的表現,她「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我們第一眼見到的探春,表現出真正的青春的美,貞潔的、清新的、不可侵犯的青春的美。
美,往往就是性格的表現。探春詠白海棠「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為肌骨易銷魂」。詩的意象,神態的比喻,意識的象徵;化海棠的神態顏色為性格,寓審美思想於自然物象,是探春這首詩性格表現的秘密,它滲透着她自己的思想感情。
如果來到探春的閨房,我們會看到房中的擺設,它表現了探春性格的另一側面。花梨大理石大案,名人法帖、寶硯、筆筒、對聯、大花瓶、大鼎、大盤……,這位公府小姐「素喜闊朗」。這裏所表現的儘管只是一種情致,一種愛好,而這種情致和愛好已展示出它本身的豐富性。
但是,要把握探春的性格表現,要了解她的思想層次、藝術的眼光不能只停留在單純的靜態上,正如葬花的黛玉,眠石的湘雲,撲蝶的寶釵,撕扇的晴雯,夢詩的香菱,畫薔的齡官,品茶的妙玉那樣,我們的主人公必須行動起來,在典型環境中,通過典型情節表現性格的特殊性和思想個性。探春的理家,就使她發展着內心世界的豐富多采性,得到豐富多采的表現。
賈府是「黃柏木作盤槌子」
賈府,繁華富麗,奢費驕橫,那「白漫漫人來人往,花簇簇官去官來」;那「把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那赫赫權勢,豪華排場;人說「宰相家人七品官」,而這裏僕人的兒子也當上縣令。
但是,「外頭看着雖是烈烈轟轟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艱難去處」;「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管家的少奶奶鳳姐驚嘆:「咱們一日難似一日,總繞不過彎兒來」。當然,這一切並不妨礙他們恣意享樂。他們似乎明白好日子不多了,應趕緊縱情,趕緊放蕩。且不說元春省親花費上多少萬兩的銀子,連這位貴妃也感慨「奢華過費」;這個官僚家庭連吃一頓平常的螃蟹宴,也夠莊稼人過上一年的日子。 ……
繁華中的衰落,衰落中的繁華,萬花筒轉動的空間,上升與下降的雙重軌道。探春,她雖不是男人,不能夠「出得去」另「立一番事業」,卻想在賈府試一試「補天」的身手,扭轉乾坤,改變局勢。但是,她的努力,能否使賈府運行的規律改弦易轍?
探春理家的契機,是因為鳳姐病了,從二、三月,到八、九月。這幾年,賈府是「出去的多,進來的少」,鳳姐「生了多少省儉的法子」,可是「一家子大約也沒個不背地裏恨」她的,連「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鳳姐準備藉此「抽頭退步」,希望探春「出頭一料理」,眾人便會對鳳姐的「恨暫可解了」。禍水,正向探春引去。 ……
複雜的人事,錯綜的鬥爭,「清官難斷家務事」,還有多少利與害,親與疏,嫡與庶的膠轕。在這樣的漩渦中,探春是否能用尖利的刺去剔除積弊,用那輕柔的花瓣去掩飾矛盾暴露的破洞?
俗話說,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眾管家女僕起初卻看探春「素日也最平和恬淡,不把這個未出閨閣的青年小姐」放在心上。偷懶、懈怠,埋伏着的笑聲,準備了尖酸刻薄,陰謀詭計,刀槍劍戟,但探春不是草包,也不是繡花枕頭,她嚴密地警惕着、防守着,就如紅花綠葉掩映下鋒利的刺隨時準備回擊「觸犯」。別看她「言語安靜,性情和順」,那精細的地方不在鳳姐之下。
探春、李紈、寶釵,臨時套起的三駕馬車,在艱難的路上出發。初戰勝利了,解決了一個又一個的問題,那些管家的和那些準備看笑話的奴才們領略了探春們的厲害,裏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說:「剛剛的倒了一個『巡海夜叉』,又添了三個『鎮山太歲』」。小心!於是他們「更覺比鳳姐兒當差時倒謹慎了些」。 (第55回711頁)
賈府這個奧吉亞斯的牛圈堆積了許多現實和歷史的牛糞,探春們當然不能如古希臘英雄赫克利斯,用河水一晝夜間把它徹底沖洗乾淨。他們的財政小改革不過是局部的零星小雨,飄飄揚揚地灑在發硬的牛糞上。
探春蠲免了學銀、脂粉錢的重疊開支,又從賴大花園的經營方式中得到啟發,決定「在園子裏的所有的老媽媽中,揀出幾個本分老誠能知園圃的事,派准他們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們交租納稅,只問他們一年可以孝敬些什麼。」 (第56回785頁)這樣,每年可以增加400兩銀子的收入。但是,從賈府大賬房的經濟眼光看來,幾百兩銀子算得什麼!儘管賈珍自認賈府是「黃柏木作盤槌子,——外頭體面裏面苦」,但僅僅寧府便有八、九個莊子,歉年,從烏進孝那個莊子尚能收益數千兩銀子,粗略推算,榮寧兩府每年地租收入至少各有幾萬兩銀子。幾百兩與幾萬兩,九牛一毛,能有多大的意義?
封建統治階級中清醒的現實主義者
然而,探春理家這一改革行動的意義,卻是超過了行動的效果本身。姑且不推而廣之,談到改良封建制生產關係對鞏固賈府家業是否有利,以及「承包」的方法在古代經濟發展史上起什麼作用,單從文學的人學角度來看,它已充分表現探春眼光的敏銳,才幹的精明。
看到破荷葉,寶玉覺得是煞了風景,破壞圓滿的美感,要人拔掉;黛玉想到的是李商隱「留得殘荷聽雨聲」詩句的淒清的美感,要求留着;探春考慮的卻是「一個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可以取利。寶玉曾經批評探春說「誰都像三妹妹好多心,事事我常勸你,總別聽那些俗話,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榮才是。」(第71回1014頁)但探春不同於寶玉、黛玉,她是封建統治階級中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又是以「補天」為任的理想家。賈府是「忽喇喇似大廈傾」,探春卻要把它匡正;前景是「昏慘慘似燈將盡」,探春卻想節流開源,撥燈添油。寶黛經常停留在「情」的天地,徘徊在「愛」的世界,流連在詩的王國;探春卻直接面向社會現實,走向實際生活。她注意實利,不為朱子的「虛比浮詞」所蠱;甚至為我所用地「斷章取義」,突破某些封建傳統意識的束縛而「喻於利」。與寶釵相比,一個是保守地維護封建制度的一切尊嚴,不肯越雷池半步;一個是雖恪守封建制度規範,卻生氣勃勃,為封建階級「公」的利益而改革創新。「好,好,好,好個三姑娘!我說他不錯。」鳳姐這個「脂粉隊裏的英雄」曾對探春連聲稱讚。這雖然摻雜了個人得失和加以利用的私心,但也是出於客觀的評價。感覺到賈府的頹勢,探春與鳳姐都有一雙明亮的眼睛,精明而嚴厲地對待人。她們在維護賈府的共同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她們有實質的分歧,這不僅表現在性格、作風和具體為人方法的差異,更表現在對封建階級的「公」心與「私」心。探春興「公」家之利除「公」家之弊,鳳姐興自己的利除別人的弊。這也是探春執政時,鳳姐害怕改革之鞭首先抽打到自己的原因。
改革,有沒有阻力呢?雖然「承包」的方案一公布,「眾人聽了,都歡聲鼎沸」;雖然鳳姐出於要保住自己的大利而隨時準備小退讓;雖然鳳姐平兒幫助鎮壓,下人們也「安個畏懼之心」;雖然只有潛在的反對派而沒有人敢公開抗拒蠲免多餘開支;但是,沒想到阻力來自她自己的「命薄」,「沒託生在太太肚裏」。探春理家碰到的第一件最棘手的事就是發付趙姨娘兄弟趙國基的安葬費,風波,就從這裏發生……
公私分明 不偏不倚
在資本主義社會,一個人的金錢財富決定他的社會地位;在封建社會,等級地位決定了他的財富金錢。活着的人——賈府自上到下——每月各領與地位相應的月例錢,死去的奴隸,也需要憑主子的賞銀多少來證明自己的奴隸的級別。襲人之母死去了,賞銀40兩,因為她是「外頭」來的大丫頭的母親;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基死了,探春按舊例賞了20兩,這倒不是故意歧視自己的親舅舅,而因為趙國基是「家裏的」奴隸的後代,當然比不上還是平民的襲人的母親。但趙姨娘憑着她是探春的生母,又有「姨娘」身份,燃起怒火又帶着希望來找探春。我們不知道趙姨娘為了兄弟之死是否流了真情的淚,只知道她需要40兩銀子來證明自己的表面上的半主子的「姨娘」地位,需要熄滅掉「屈尊」於襲人之下的怒火。她希望探春看在親生母女情分,滿足她的體面。溫和的探春用微笑來接待趙姨娘,但一聽知來意,馬上用無私的臉孔無情地駁斥拒絕。探春搬來陳年流水賬,搬出祖宗的老規矩。她無須為趙國基悲傷,因為他僅僅是一個聽賈環使喚的奴隸;她也決不同情趙姨娘,因為半奴隸的面臉也不值錢,人們可以從古代封建經典中找出一大堆依據,來為無私的探春辯護。毫不奇怪,當一個人奉行某一傳統的行為準則時,她對事物的態度自然會根據這些準則分成等級,並且把這種做法堅持到底。
趙姨娘感到失望,感到痛苦,因而怒火熊熊上升,向六親不認的探春,發動公開的、真實的攻擊,那刻薄的語言像排炮鋪天蓋地而來。但無私的探春也有私心,她恐怕趙姨娘爭閒氣會連累自己,害怕王夫人不再讓她管家。她的傷心帶來了淚水,她的痛苦卻更堅定與姨娘劃清界限的決心。她早就曾向寶玉揚言,她「只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概不管」。這時,她更不承認趙國基是自己的舅舅。她臉不發紅心不跳地宣稱自己的母親是王夫人,舅舅是「九省都檢點」王子騰,一切都是天經地義。老實的李紈說兩句人情味的話打圓場,也遭探春嚴厲申斥,宣稱「姑娘們」是決不「拉扯奴才」的。
前人曾說:「觀其(探春)對趙姨娘論趙國基事,陳義何嘗不正?而辭氣之間,凌厲鋒利,絕無天性,真令人髮指。為維持自己之地位計,而不顧其母,至於如此,真無心人者」。其實,母不母,女不女,親不親,這種尷尬而離奇的局面,正是封建等級制度下人性異化的反映。在這一事件中,探春的態度是堅決的,感情是真實的,一點也沒有虛偽做作的因素,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有什麼「涼薄」(俞平伯語),她的所做所為,就像在履行一種天然的義務。這,才使人覺得雙重的可悲。
在虛偽而又殘酷的宗法制度面前,趙姨娘理屈詞窮,她只想在賈府的舊帳老例中鑽空子,根本不敢推翻老規矩。血緣的紐帶,相連的骨肉,被封建等級的沉重履帶碾碎。母與女,嫡與庶,權與勢,得與失,笑聲與淚水……趙姨娘失敗了,探春的勝利是輝煌的。殺雞儆猴,其它下人理事的也都「慢慢的一個一個的安分回事,不敢如先前輕慢疏忽了」。 (第55回779頁)
但是,痛苦還折騰着勝利者,封建的理性並沒有氓滅探春的作為「人」的全部感情。她希望趙姨娘能明確自己的地位,「安靜養神」,不要「失了體統」。應該說,她的願望是誠懇的,失望後的痛苦也是真實的。實際上,她畢竟沒法與生母完全割斷臍帶。儘管她採取「鴕鳥政策」,說「什麼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但最終還是得承認血緣關係和「庶出」這個歷史事實。她抽抽咽咽,一面哭一面對趙姨娘說:「何苦來,誰不知道我是姨娘養的,必要過兩三個月尋出由頭來,徹底來翻騰一陣,生怕人不知道,故意的表白表白。也不知誰給誰沒臉?幸虧我還明白,但凡糊塗不知理的,早急了。」(第55回774頁)其實,知理而不糊塗的探春,也是早就急了。她這段話的潛台詞是:希望趙姨娘不要像剛產下蛋的母雞,得意地向全世界宣布自己的功績,(在封建家族中,陪房的女奴能生孩子也是一種功績!)不要表白探春的「烙印」,以免給她「沒臉」。然而,嫡與庶在封建社會裏也是一種等級,不能逾越的等級。鳳姐對平兒說:「你那裏知道,雖然庶出一樣,女兒卻比不得男人,將來攀親時,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庶出,多有為庶出不要的。」(第55回779頁)其實,嫡與庶,對「女兒」不一樣,對男人何曾就一樣?鳳姐在談論寶玉和賈環將來的婚事費用時,寶玉準備了一萬兩銀子,而賈環才准備3000兩,價格差了兩倍多。可見,探春對嫡庶之分採取「不承認主義」,當然最後仍是徒勞的。
寶黛為青春痛苦,為愛情痛苦,探春為自己的「臍帶」痛苦。 「臍帶」是永恆的,痛苦也是永恆的。心理學家已證明,痛苦是人類心理本性的規律性的一種活動,在任何時代都不會停止。但是,在各個不同時代,各個不同的具體人,由於社會關係不同,生活環境相異,進入人頭腦裏的「痛苦」的材料就完全不一樣。所以,毫不奇怪,它加工的結果也就完全不同。鳳姐在連聲誇獎探春以後,也公道地嘆息說:「只可惜她命薄,沒福生在太太肚裏。」(第55回779頁)高級肚皮與低級肚皮決定了後代的貴賤。子宮,胎兒的搖籃,或稱胎兒的旅館,就像住過高級旅社的人一定有高等的身價,這,決定了一個人的家庭地位,以及將來被選擇的時價。

如果探春是個男人
女人,你的名字叫不幸!庶出的探春更有理由埋怨命運。她嘆息:「偏我是女兒家」,「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第55回773頁)她為了某種事業,某種理想,或者簡單說是為了某種想法,熱切地準備獻出自己。然而,因為她是一個女人,所以連貢獻自己的機會都沒有。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封建社會裏女人的命運。
如果探春是個男人,她能做些什麼呢?是的,她曾為家庭那種腐爛荒淫的生活擔心。她替王夫人向賈母辯解,就是為了妻妾成群的賈赦還要納鴛鴦為妾這醜聞。她曾為搖搖欲墜的家族擔憂,警告說:「你們別忙,自然連你們抄的日子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曾議論甄家,自己家裏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們也漸漸的來了。」(第74回1055頁)她又為統治者內部的勾心鬥角而氣憤:「咱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像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第75回1066頁)並預言了不可設想的嚴重後果:「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裏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第74回1055頁)總之,賈探春對賈府現狀不滿,對未來更充滿憂慮。賈府奴僕周瑞的女婿、古董商人冷子興對賈雨村演說了榮國府之後,悲觀地說:「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盡多,運籌謀劃者無一;……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第2回27頁)探春的見解跟冷子興相似而更深刻些,她對賈府現有的男人是不以為然的。如果她是男人,肯定不像賈赦那樣荒淫恣肆,不像賈政那樣僵化庸碌,不像賈璉那樣好色無恥;當然,她也不會像寶玉那樣既是「富貴閒人」,又是思想叛逆者。因此,探春只能從過去的「天恩祖德」中吸取力量,戰戰兢兢地請出祖宗的亡靈來當樣板。她對祖宗的光榮充滿敬意。如在批駁鳳姐認為趙國基之死賞錢 「添些也使得」時,她就指出趙國基並不是「那出兵放馬背着主子逃出命來」,上過戰場,立過功勞的人。這就是說,她認為那些追隨祖宗光榮歷史的人才有較高的地位。
作為封建家族的「補天」派,探春也不缺乏處事應變的本領。在處理「懦小姐」迎春和「累金鳳」事件時,探春使眼色侍書去請平兒來。聰明的寶琴和黛玉十分欣賞探春的調兵遣將的能力。當平兒進來時,寶琴拍手笑道:「三姐姐敢是有驅神召將的符術?」黛玉笑着說:「這倒不是道家玄術,倒是用兵最精的,所謂『守如處女,脫如狡兔』,出其不備之妙策也。」(第73回1041頁)這雖是戲談,但也說明探春是個頗有智謀策略的人物。如果她是男人,為鞏固封建制度,復興家族的事業,她是有相當的才幹和能量的。
從整體的出發點來看,作為「補天」派,探春與寶釵是相同的。但是,立足點和具體做法,兩人有相當的差異。寶釵本想入選進宮,探春卻從姐姐元春得到教訓,那裏是「不得見人的去處」,她「垂淚無言」的沉默意味着 領會的深刻。寶釵留意的是仕途經濟,功名科舉。在這方面,我們還看不到探春的議論。或許,她想「克繩祖武」,從這條途徑去幹出「一番事業」,這和寶釵實際是殊途同歸的。因為,在封建時代,作為男人,不論習文習武,最後都不過是「學成文武業,貨與帝王家」,從而得到封官賜爵,耀祖揚宗。封建家族總是依附於封建王朝,其它的出路是沒有的。
探春從她家族的種種矛盾和危機中感到時代的停滯、沉重和腐朽。她想振奮起來,「才自精明志自高」!但是,「生於末世運偏消」,喜歡開玩笑的歷史沒有為她安排舞台,疲憊了的封建「末世」更不會為女人提供用武之地。不管曹雪芹對探春多麼偏愛,給予多大的同情,寄予多大的希望,探春永遠成不了女媧。神話的時代已經過去,沒有一個英雄能夠「補天」。
賈探春二之一
本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