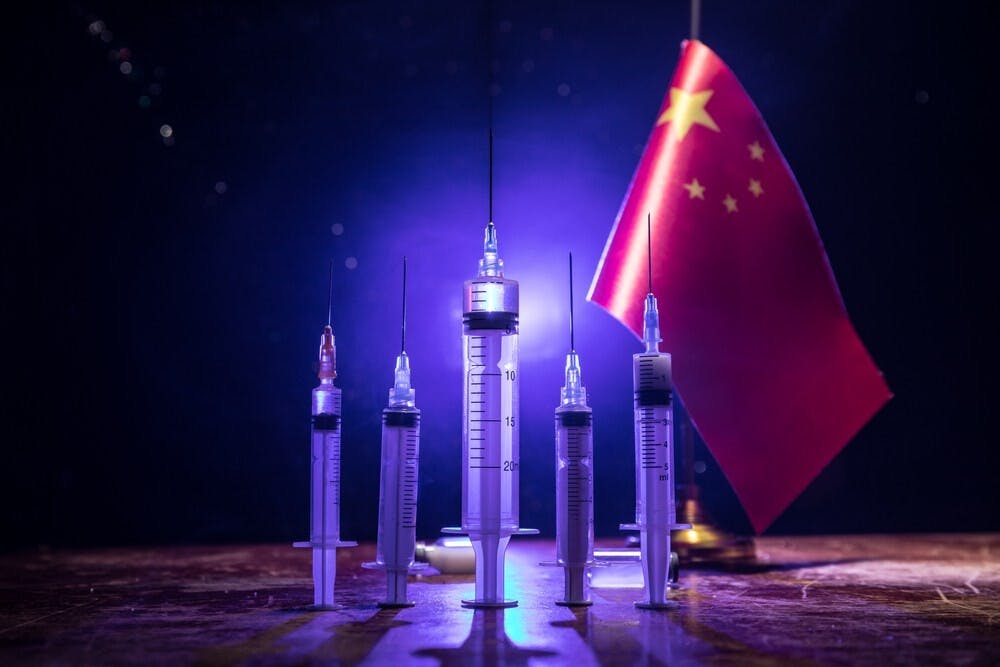2003年「沙士」病疫爆發過後,作為受影響至大的香港和中國內地,均進行了深入的檢討及反思。
通常危機過後會調整處事方式、政策思考、制度法規等,構成新的「標準操作流程」(SOP,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去指導人們和組織的認知與行為。危機預防建基於經驗,但現代社會乃風險社會,一些危機總是防不勝防,既有人為因素,也有天然和制度因素。最大挑戰在於一些危機不可預知,或不會簡單地重複過去。危機來臨時,才真正考驗一個政府在危機處理上的能量、智慧與適應力,因為要在有限時間和公眾耐性下,面對不完整資訊和未知因素,作出決定。
沙士處理之失誤及教訓
香港先後有國際醫學專家報告、醫院管理局專家檢討和立法會調查委員會聆訊。前兩者認為風險認知不到位(包括過分依賴傳統評估方法而忽略一些「軟」情報)、溝通失效、指揮不明、醫療物資分配不均,以及跨部門統籌協作不足,乃政府危機處理的主要失誤。在社區控疫、停學、隔離等措施方面猶豫不定,也造成抗疫執行上的混亂。立法會調查則批評政府及醫管局工作落後於形勢,導致社區爆發。
政府汲取教訓,全面改善應變機制(預防、預警、通報、監測檢疫、預案規劃、跨機構統籌)、強化流行病學應對能量、修改法規等。及後於2009年針對豬流感打了漂亮一仗,快速全方位地遏止社區傳播,突顯政府果斷統籌得當,贏得市民不少掌聲。
內地方面,前期隱瞞、緩報、封鎖消息,延誤遏制沙士蔓延的良機,引起民眾恐慌,國家形象受挫(註1)。危機爆發後領導非典疫情防治工作的時任副總理吳儀,於當年5月第56屆世衛大會上坦承:疫情發生初期,中國對其嚴重性認識不足、公共衛生系統存在缺陷、組織指揮不統一、信息渠道不暢通等,導致防治工作在一段時間內被動。有學者認為承襲自舊體制的「條塊」矛盾衝突,嚴重影響對疫情信息的及時、準確和有效管理,乃治理體制的問題;更有指國家長期重經濟發展而輕健康安全(註2)。
中央政府痛定思痛,迅速建立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機制,通過相關法律與條例,規定及時如實通報和公布疫情,並設立常規信息披露制度等。改革醫療及提升治理效能,也一直在國家議程上。
那麼,今次新冠肺炎的處理,兩地有否得着於和汲取17年前的沉重教訓呢?
香港:SOP要求的,都做到了
新冠肺炎爆發至今,香港在風險意識、流行病學應對,以及醫護專業應變能力上,皆表現良好。醫學界自去年12月下旬武漢傳出發現不明原因肺炎,已發出警告,政府於本年1月8日把它納入須通報之傳染病名單。當1月23日有兩宗確診病例,政府於兩天後啟動最高之「緊急」回應級別。醫學專家、公衛系統和醫管局均嚴陣以待,調動資源,每天發放資訊,又成立跨部門統籌委員會。
SOP要求的,都做到了,流程上有否滯後,事後應檢討。政府大抵上按專家意見行事,不過專家意見未必一致,政府也不能只依賴正規信息,忽略軟情報和十分敏感的本地民情,而這正是當年沙士的教訓。隨着內地披露嚴重疫情,香港民情波動,政府出現進退失據,在口罩供應、防護配備、「封關」與否、處理前線醫護情緒,以至市民搶購必需品等方面落後於形勢。執行過程中的爭議,包括隔離設施選址以至停課安排。
其實,這類問題也見於其他國家地區,只因香港現處政治不穩、民間充斥陰謀論,致所有公共行政系統常見的思慮不周和執行乏力情况,都被無限政治解讀,這就是危機的政治,但卻是當前政府施政的軟肋。政府民望低落、話語權不彰、動輒得咎,也影響公眾對政府應對措施的認同。
抗疫論述疲弱
政府的抗疫論述顯得疲弱,未能一早向市民清楚闡述今次疫情處境和嚴重程度、政府全盤抗疫的策略優次和行動方案、面對的局限與不足,以及可能出現的後果等,以協助市民置於一個較現實而非抽象的認知範疇去理解和面對疫情。
專家建議市民儲備大量口罩、天天換,時刻使用消毒液等,那當然至穩妥,但當這些都缺貨,那市民該怎麼辦?若無答案,自然焦躁恐慌。在預知口罩供應不足下,政府應及早告之市民在不理想條件下如何減低風險,以穩定情緒。任何疫情中,必有眾多的專家和民間智慧之言,社交媒體更會出現大量真真假假的信息。若政府缺乏明確論述,其抗疫工作,必會處處受挑戰、招懷疑。
「封關」問題,其實可正面辯論,以釋眾惑。控制來自源頭風險,防止社區爆發,乃流行病學應對常理,一切以控疫優先。不過就算主張「全面封關」者,也指限制內地人入境而非港人回家,針對人流而非物流,故關鍵在於執行幅度與風險效益。現時各國對外地人進境採取的管控程度不一,皆因涉及疫情評估、社會經濟考慮和成本效益計算,至今以內地和意大利的「封城」至為嚴厲。
香港公衛系統、醫護防治和醫學專業,在今次抗疫的表現,備受國際專家肯定,相信當年沙士的不少經驗已進入了制度的基因中。但危機因新冠已全球擴散會帶來變數及新恐慌,而醫護和隔離的應付能量有其極限。

內地:嚴重低估風險,後強力控疫
內地方面,儘管去年末武漢已現不明病毒,可是一如沙士爆發初期一樣,在緩報、隱瞞、封鎖消息下,錯過了及早控制、遏止擴散的時機,讓新冠病毒乘虛藉春運巨大人流迅速傳染各地,何况其傳染早於症狀呈現,易令風險警覺鬆懈。無論國家經濟科技發展如何驚人,一場早段低估失控的病疫,頓使國人在國際上備受排斥、國譽受損。
但一旦官方確認風險,危機出現後的果斷控疫舉措,包括封城、醫護軍民總動員、流行病學應對等,展示了特急情况時,在舉國體制下應變能量之強勁,強制性力度非他國可比,對遏阻疫情惡化散播,起了作用,逐步在全國範圍內把疫情穩定下來,但湖北(尤其武漢)受重創的現實已無法挽救,為體制上防範危機失敗付出了沉重代價,國家也付出重大經濟代價。
根本體制缺陷依舊存在
諷刺地,去年兩會期間,國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還在表示:不會再出現當年「SARS類似事件」。今次危機並非簡單地因疾控體系不足,而是治理體制和資訊控制的束縛,遏抑了風險意識。北京大學教授強世功認為,「我們國家的治理體制和治理機制」、「官員和精英階層的思想和心態以及普通國民的觀念」,距後工業化發展的要求還有差距。(註3)他歸咎於「小農社會」的小富即安、缺乏風險意識,以及決策仍靠層層集中、層層下達的垂直體制。
沙士後10多年來,內地公衛系統及防治整體能量和效率均有所提升,醫療科技及SOP也今非昔比,法規及機制俱備,可是沙士時揭露的根本體制缺陷和官僚文化弊病,依舊存在,這體制基因究竟可如何改造?新冠爆發矛盾地既反映制度性缺陷,也突顯(事後)一些特有制度能量,儘管前者造成的嚴重後果,不能因後者而輕輕帶過。
官僚文化的本位主義和僵化,不同國家常見,韓國和日本早期也低估新冠傳染風險。大疫壓境下,香港人搶購潮曾被譏為「瘋狂」,但現在各國皆見搶購口罩藥物及超市貨品,人心之虛怯反映對未知的恐懼。病毒無國界,不分種族政治,現時切忌幸災樂禍,或五十步笑百步,反之應合力抗疫,及應付隨之而來的全球經濟萎縮。
註1:門洪華(2003),〈中國SARS危機管理:理論框架與實踐評估〉,於胡鞍鋼(主編)《透視SARS:健康與發展》,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頁3-26
註2:見同書其他篇章
註3:強世功(2020),〈我們為何不敢承認大疫背後的小農心態?〉,2月16日。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