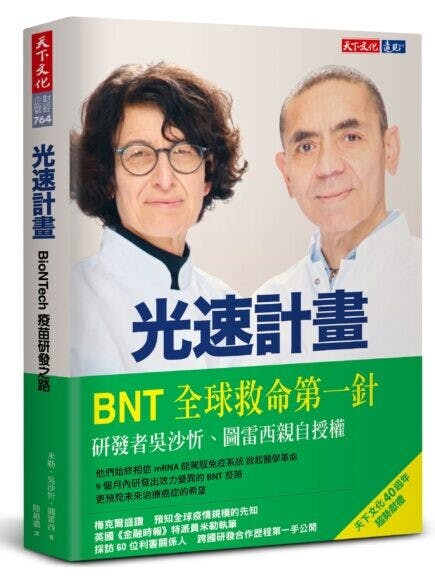編按:當新冠病毒來臨,全球忙於搶購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資。另一邊廂,一群科學家秉持救世意志,以不到一年的速度開發疫苗。其中一種便是以mRNA的新型技術研發的復必泰(BioNTech)疫苗,曾經引起不少市民懷疑,但仍刻劃了這時代最重要的醫療里程碑。繼牛津大學研發人員親身解說研發過程,BioNTech創辦人與其團隊亦道來他們的故事。本社獲天下文化授權轉載部分章節,以饗讀者。
延伸閱讀:〈與新冠病毒競賽的兩位牛津疫苗專家〉
相遇
偶然之下,吳沙忻不久之後也來到了薩爾邦距離法國邊境只有32公里的小鎮宏堡(Homburg),並且進入大學的附設醫院工作。
1991年,在講座、醫院病房和研究室之間瘋狂往返的兩人相遇了,圖雷西形容那就像是「電影裏的場景」,雖然完全不是最浪漫的那種場面。那時圖雷西輪值到血液癌症病房,吳沙忻則是那裏的住院醫生,同時也是她的主管兼職場導師。
這裏大部分的病人來日無多,他們必須常常告訴病人所有可用的治療方法都已用盡。每一天,他們看着這種無情的疾病帶走病人的性命,病人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甚至沒有一雙溫暖的手握住他們。就是在這樣恐懼的氛圍當中,某天下午巡房時間,他們兩人對上了眼。
這對年輕的愛侶很快就發現,除了相似的背景以外,兩人還有更多共通點。對於治療久病病人,手邊能用的工具有限這件事讓兩人都很挫折。醫生只能在開刀、化學治療和放射線治療之間做選擇,在他們的專業領域,這3種方法被粗魯地形容為「割、毒、燒」。
與此同時,吳沙忻和圖雷西在實驗室裏也瞥見了可以徹底革新癌症醫學的先端技術。在這個攸關生死的領域裏,科學理論和臨床實務之間的差異折磨着他們。治療症狀並不能滿足他們,他們渴望投入研究預防並治癒這種疾病的方法。這種從實驗室到病床邊(bench-to-bedside)的方法,目的是盡快讓病人使用到新藥,幾年後,這種方法被稱為「轉譯醫學」(translational medicine)。
有了這種方法,一種全新的學科即將誕生。但在當時,也就是1990年代初期,他們還沒辦法用這麼宏大的名詞來定義這種方法。他們只知道自己想要從事科學研究,但目的不是為了科學。
在吳沙忻的內心,他還是當初那個男孩,對成年人欣然接受癌末診斷一事感到震驚。圖雷西則還是那個想要效法父親成為全科醫生的女孩。兩人彼此承諾,並共同努力打擊那個吞噬着他們周圍病人的殘酷疾病。

通緝病毒
在腫瘤學家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口中有「萬病之王」這赫赫稱號的癌症,給醫學界帶來一項獨特的挑戰。
不像在別處生存而後入侵人體的病毒或細菌,致癌細胞是健康細胞隨着時間發生隨機突變後,以極快的速度分裂而來,到了某個時間點,開始以不受控制的態勢生長。致癌細胞的目的就是對宿主造成最大傷害。因此,它們就像隊伍中的叛徒,是冒充朋友的敵人,是免疫系統無法認知的威脅。
200多年來,科學家已經知道,經過訓練的人體可以偵測到傳染病之類的外來敵人,並對未來再度遭遇相似攻擊者做好準備。正是這項觀察結果造就了疫苗的發展,拯救了幾億人的性命。1990年代初期,由全世界免疫學家組成的小群體開始了解到,經過訓練的免疫系統也可以識別出「來自內部」的威脅,並與之對抗,這也為新形態的癌症醫學鋪設了道路。但在當時,免疫療法是一個未成熟的新興領域,主要局限於大學校園內,完全沒有受到製藥界的關注。
吳沙忻和圖雷西是這個小眾俱樂部的成員。
他們相信,那些在他們眼前逝去的病人,血管內其實早就有對抗腫瘤的武器。
他們只是需要找出方法利用並且釋放這些武器的威力,藉此對抗複雜的癌症。
免疫系統就像一支軍隊,由組織精良、高度專責的單位所組成。每個單位都以不同的方式接收指令,身着不同制服,施展獨特的戰技。然而,清楚識別敵人身分後,各單位會同心協力,進行大規模、多管齊下、協調一致的反擊作業。
運作順利時,免疫系統的美妙之處就在於它的攻擊既精確又有效。像抗體和T細胞這樣的武器,有如免疫大軍的狙擊手,一旦認得作為攻擊目標的特殊分子,就會展開強力攻擊。吳沙忻和圖雷西把注意力轉向癌症時,科學家才剛開始發現,腫瘤表面上散布着健康細胞沒有的獨特分子。如果可以透過訓練,教導免疫系統認得這些分子,那麼狙擊手就能把癌細胞納為攻擊目標,朝它們開火。
1994年,圖雷西放棄繼續接受醫學訓練,轉而致力於研究領域之後,她和吳沙忻兩人,花了幾年時間,全神貫注地尋找這些獨特的分子,也就是所謂的抗原(antigen)。
他們的目標是在實驗室生產這些分子,再把抗原注入病人體內,達到「通緝犯海報」的作用,清楚地指示免疫系統去逮捕並攻擊相似的敵人,希望人體可以認真看待這個重罪犯,產生全面性的免疫反應,認出這些抗原跟腫瘤很像,進而把腫瘤也當成敵人。也因此,她苦笑地形容他倆就像一對「免疫系統的告密者」。
原則上,有好幾種方法可以把抗原引入人體內,這對夫妻全都試過了。「我們是典型的書呆子,」圖雷西這麼承認,她偶爾會自豪地穿上畫着薛丁格貓悖論圖案的T恤。圖雷西表示:「我們對許多不同技術有着廣泛的興趣,而且它們都是不被接受的技術。」
但他們發現,合成胜肽、重組蛋白、重組DNA或病毒載體(後來被牛津大學和阿斯利康製藥公司,應用於製造新冠肺炎疫苗)等方法都有限制性。不是讓細胞培養物在培養皿上生長(這是一個麻煩且漫長的過程),就是無法激發強效且持久的免疫反應。
接着,在1990年代中期,吳沙忻和圖雷西遇見一個最適合用來把抗原引入人體的平台,幾十年後他們就是利用這張王牌,開發出冠狀病毒的疫苗。這是平台的基礎,就是RNA。
有些人認為,在生命演化的過程中,RNA是最原始的生物分子,它具備許多卓越的能力。19世紀末首度被人發現的RNA,跟它那更為人熟知的親戚──DNA──一樣,可以儲存基因資訊。但RNA也可以充當科學家口中「催化劑」的角色,也就是說,RNA本身就能進行複製,不需要其他分子的幫忙。在RNA剛被人發現時,有理論認為,RNA分子攜帶着細胞藍圖,並激發了以RNA為材料進行建構所需的化學反應,可以說RNA既是雞,也是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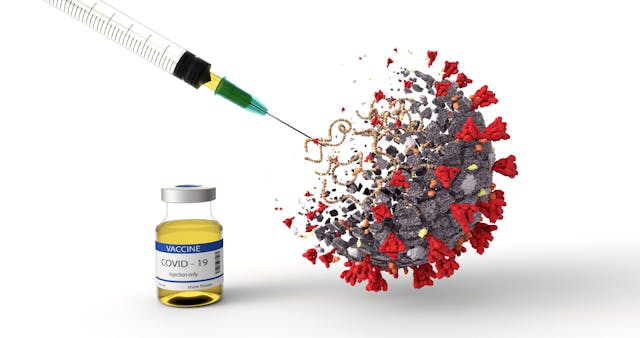
麻煩的RNA
然而,讓吳沙忻和圖雷西感興趣的是一種相當平淡無奇的RNA功能。那是「搖擺60年代」(swinging sixties)氛圍剛開始風行至英國劍橋時,一個喧鬧的派對上,一群學者擠在茶几上首次勾勒出來的RNA功能。
他們發現這種存在於人類和動物身上每個細胞中的分子,其實就是生物界的密碼信使,把來自DNA的一系列指令,送到細胞中有如工廠的地方,讓細胞工廠根據密碼生產出可以建造、控制身體器官及組織所需的重要蛋白質。一旦任務完成,這種緞帶似的單股RNA分子在幾分鐘內就被摧毀。
1960年秋,這個分子有了名字:信使核糖核酸(messenger RNA),很快地就被簡稱為mRNA。對於有興趣進一步了解自然界的人來說,mRNA一直是令人着迷的研究對象,但它幾乎不受臨床研究人員的重視。從沒有人因為發現mRNA而獲頒諾貝爾獎,大型藥廠也很少多看mRNA一眼。若在科學研討會上提到以mRNA為基礎的藥物,結果要不被忽略,就是受人嘲弄。
mRNA會被如此對待,也不是沒原因。
原刊於《光速計劃:BioNTech疫苗研發之路》,本社獲天下文化授權轉載,題為編輯擬。
新書簡介:
書名:《光速計劃:BioNTech疫苗研發之路》(The Vaccine: Inside the Race to Conquer the COVID-19 Pandemic)
作者:米勒(Joe Miller)、吳沙忻(Ugur Sahin)、圖雷西(Özlem Türeci)
譯者:陸維濃(國立中興大學昆蟲系博士)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22年3月
作者簡介
吳沙忻(Uğur Şahin),1965年於土耳其出生,4歲移居德國,科隆大學癌症免疫療法博士,是腫瘤學與免疫學專家。2008年與妻子圖雷西共同創辦生技公司BioNTech,並擔任CEO職務。2020年BioNTech與美國輝瑞開發出對抗新冠肺炎疫苗──BNT。榮獲2021聯邦德國星級大十字勳章。
圖雷西(Özlem Türeci),1967年生,生於德國,父母為土耳其人。薩爾邦大學分子生物博士、醫師。目前為BioNTech的首席醫學官。吳沙忻與圖雷西夫婦共同獲得2021年「德國未來獎」表揚他們在自然科學、市場應用等方面的貢獻。
米勒(Joe Miller),《金融時報》駐法蘭克福記者。在報道英國的退歐後果時,踢爆與政府高額簽約的「海上貨物運輸公司」(Seabourne Freight)名下一艘船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