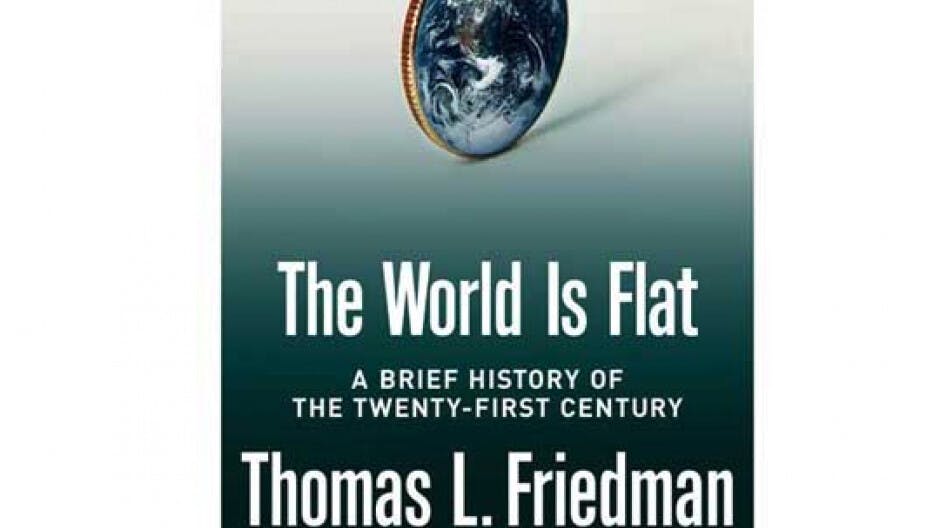1991年,蘇聯的解體震撼了整個世界。翌年,美籍日裔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了《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這本著作,也成為了備受觸目的話題。在書中,福山高調地宣稱,經歷了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在20世紀的激烈較量,資本主義經已全面獲勝。由於資本主義所包含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代表了人類文明追求的最高境界,因此資本主義的勝利,標誌着人類的歷史已經抵達終站,而未來的歷史,將只會是這一主題之上的一些變奏吧了。
然而,差不多在同一時期,另一位美國學者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是哈佛大學一位政治學教授。1993年,他在學術期刊《外交事務》(Foreign Affiars)之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lizations?)的文章,迅即引起學術界的廣泛爭議。1996年,他把這篇文章擴展為《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又簡稱《文明衝突論》)這本書,把有關的爭議帶到更廣闊的層面。
意識型態的角逐
如果說福山是樂觀主義者,那麼享氏無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按照他的觀點,共產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的對壘屬於一種意識型態的鬥爭(ideological struggle),而這在人類歷史中屬於例外而並非常規。隨着這種鬥爭的終結,我們迎來的將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返回傳統的文明衝突的軌跡。在他看來,現今世界主要由三大文明圈構成:以西方為主的基督教文明圈(Christian civilization)、以阿拉伯世界為主的伊斯蘭文明圈(Islamic civilization)、以及以中國及周邊國家為主的中華(儒家)文明圈(Sinic civilization)。由於這些文明圈抱持的核心價值各有不同,而在地緣政治上亦有利益上的衝突,所以未來的世界仍將是一個爭鬥不絕的世界。
最初,上述兩派的觀點各有擁護者,支持福山的人甚至提出了世界將由美國這個獨一超強(sole superpower)的統攝下,達至一個類似羅馬帝國和平(Pax Romania)的美利堅帝國和平(Pax Americana)。但2001年9月的9.11恐怖襲擊,將這個美夢敲得粉碎。人們開始意識到,21世紀的動盪,有可能較20世紀的不遑多讓。文明衝突而非歷史終結成為了主流的論述。

按照本書迄今的分析,無論是福山或是享廷頓的分析都是膚淺和失諸偏頗的。民主自由與專制獨裁的鬥爭固然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一道主軸,但這項鬥爭至今未有完結。此外,文明的衝突和國族的紛爭(包括領土糾紛)也是十分現實的一回事,而且在短期內也不會消失。但從宏觀和歷史的結構性角度看,真正威脅世界和平的罪魁禍首不是這些,而是在於「無休止資本擴張」這股「衝動」下的全球性市場爭奪和資源掠奪。
資本主義全球化不但帶來戰爭的風險,而且正在引發全球性的生態環境災難。除非我們像鴕鳥般埋首沙堆,否則我們會看出,每日每夜的新聞報道(軍事演習的數量與規模、極端天氣的頻密度與破壞性……),都是這兩大趨勢的寫照。
但樂觀派總有它的支持者。2005年,美國《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湯馬斯・弗列德曼(Thomas Friedman)發表了一本名為《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著作,迅即成為瘋靡全球的暢銷書。弗氏在書中極力歌頌全球化的好處,並指出在一個由互聯網「平化」了的世界,各國人民都可以透過自由貿易而搭上通向繁榮富裕的列車。
世界爆發戰爭的機會低
此外,他又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就是世界各國愈是受到貿易的緊密連繫,則由於彼此的利益已綑縛在一起,所以爆發戰爭的機會便會愈來愈低。他甚至提出了一個黃金拱門理論(Golden Arch Theory),就是兩個國家之內到處都有以黃色 M 字為標誌的麥當努快餐廳的話,則這兩個國家之間便不可能發生戰爭。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首先,這本書發表後不久,第三輪的世貿談判(稱「多哈回合」,Doha Round)便停滯不前。原因是眾多發展中國家都認為,不少建議中的貿易條例都嚴重地向富裕國家的利益傾斜(如富國可以向本國農業進行補貼而它們則不行)。它們的口號是:「寧願沒有條約,也不要糟糕的條約!」(No deal is better than a bad deal!)
尤有甚者,這本書發表後只三年,便爆發了全球金融海嘯,至令全球的經濟受到重創。要知按照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倡議,除了自由貿易之外,最重要的一點便是資金的全球自由流動,即各國除了消除關稅之外,還要解除一切對外匯(外資)的監管。金融海嘯令世人驚覺,這種資本的解放不是通向金光大道的鎖匙,反倒是讓國際金融炒家興波作浪來去自如的屠城木馬。全球化的美麗承諾即使沒有完全幻滅,亦已蒙上灰灰的陰影。
但按照本書迄今的討論和分析,這個美麗承諾當然從來都是一個騙局。不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全球各處的殖民地紛紛獨立。(新主子不想擁有殖民地,當然也不容許舊主子繼續擁有。但這並不表示爭取獨立的過程不艱巨和血腥,印度和越南便是兩個很好的例子。)從宏觀的歷史角度看,這個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運動當然值得我們稱頌。但現實卻是,名義上雖然獨立了,但這些新興的國家卻仍然處處受着西方的操控。這些操控雖然不再來自赤裸裸的軍事侵佔,但經濟上的控制仍是令這些國家深陷囚籠。簡單來說,舊的殖民統治消失了,但迅即取而代之,是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的制宰。
由軍事侵略轉為經濟侵略
按照歷史學家伊曼紐・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提出現代世界體系分析理論(Modern World-Systems Analysis)(四卷本的鉅著橫跨1974至2011年),前資本主義的帝國如羅馬帝國或蒙古帝國的掠奪,靠的是直接的軍事侵佔和統治,但自從資本主義興起之後,在這種方式之上,還出現了以市場經濟作為手段的掠奪,這便是新殖民主義的本質。但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角度看,彼此的基本關係沒有改變。
按照華氏的觀點,過去數百年來,西方富裕國家(在此也包括於19世紀透過明治維新全力西化的日本)構成了他所稱的中心(core)區域,而其他國家則成為了環繞着這個中心的邊陲(periphery)。中心壟斷了知識、科技、資本和制定了遊戲規則,而邊陲則只能夠靠出賣廉價勞動力以及農產品、木材、礦產等原材料來換取中心國家所提供的高價製成品。之間即使有貿易關係,都是一種絕不平等的貿易。
當然,新殖民主義(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模式)和舊殖民主義是一脈相承的。事實是,當西方列強侵佔其他國家並進行殖民統治時,它們最想獲得的(除了最先發現的貴金屬之外),是大量廉價的糧食和工業原材料、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以及龐大的消費者市場以吸納他們的製成品。而他們最不想見到的,是能夠挑戰他們市場地位的競爭者。結果是,他們所到之處,必然會將當地多元化和基本上自足的本土經濟徹底摧毀,然後強迫當地的人民進行單一的經濟生產。大英帝國將印度原本十分發達的紡織工業摧毀,而只容許他們種植綿花以提供原材料,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如是者,世界各地人民的本土自足經濟逐一被摧毀。為了配合殖民主子的經濟利益,當地的人被迫進行大規模的單一種植(monoculture):例如某處地方全是種植甘蔗、另一處則只是種植香蕉、再另一處種植綿花、玉米、咖啡豆、可可豆、橡膠等等。當然,還有的是大規模開採各種珍貴的礦產如金、銀、銅、鐵、鋁、錫、錳及至煤、石油、鑽石等。此外,大量廉價勞工亦可用以進行低端的工業組裝,當然這些半製成品會運返宗主國進行最後組裝,然後以高價行銷全世界。這便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之下的國際勞動分工秩序。

貧窮國家是被製造出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解放鬥爭的確換來了國族的政治獨立,但上述的國際勞動分工秩序基本上沒有改變,貧國仍然不斷地補貼着富國。留意不少原本在糧食上自給自足的國家,在殖民統治後只有靠輸出大量的原材料以賺取外匯,然後才能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糧食滿足國民的需求。然而,這些出口原材料的國際價格往往十分波動(例如全球咖啡豆大豐收會令它的價格大幅下降),而外匯收入的銳減會令這些國家無法購買足夠的糧食,從而導致饑荒的出現。
而每當這些國家財政出現困難的時候,西方的國際金融集團便會伺機透過 IMF 或世界銀行等組織向它們提供貸款,代價是進一步開放市場甚至要求它們賤賣國家資產。要是這些國家還不起債(即連每月的利息也無法償還),則它們只有進一步舉債來以債還債。如是者,不少發展中國家(特別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便成為了西方的債務奴隸。
從全球的角度看,一個基本的認識是:貧窮是被製造的。對,環境貧脊會令生活較艱苦,而天災和戰亂會導致生靈塗炭哀鴻遍野。但艱苦卻不等於現代意義上的貧窮,而且環境太差人們自會移居他處。我們不會在一個活火山的山麓或撒哈拉沙漠中央找到處於苦貧的居民。事實上,在白人未到達之前,即使澳洲的土著也不貧窮,而身處富饒的非洲人民便更不用說。古埃及文明之發達眾人皆知,較少人知道的是,個多世紀以來不斷發生饑荒的埃賽俄比亞,在白人抵達之前也是一個十分富庶的王國。也就是說,所謂貧窮國家及廣泛和持續的系統性貧窮,基本上是西方殖民迫害和掠奪所導致的新生事物。
從這個角度看,弗列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之中所設想的全球共富,只不過是一種天真的幻想,因為中心和邊陲的關係是西方的利益所在。
本文節錄自作者的新著《資本主義的衝動——世界深層矛盾根源》一書,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