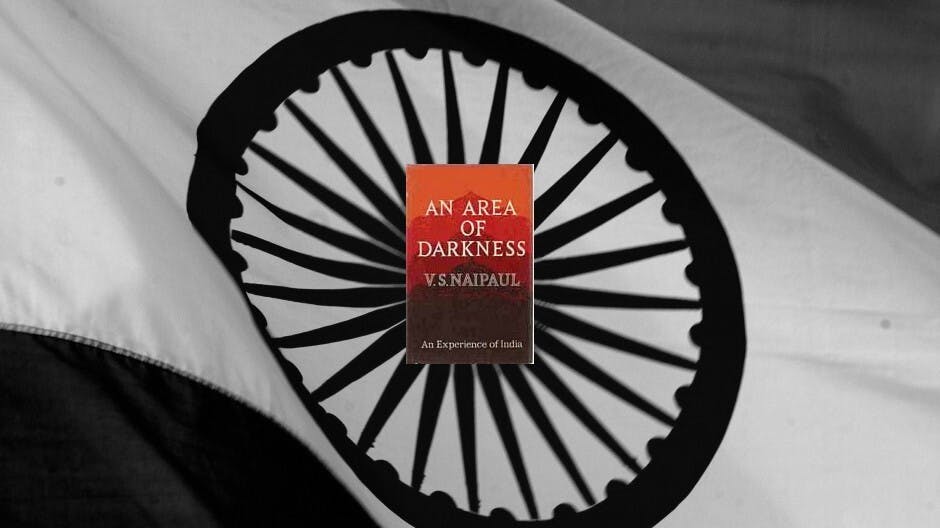撰文:查建英
這是奈保爾(V. S. Naipaul,1932—)著名的「印度三部曲」的第一部。在加勒比海島特立尼達出生長大的奈保爾是印度婆羅門移民家庭的後代,18歲獲得政府獎學金去英國牛津大學讀書,畢業後定居倫敦,終生專事寫作。1962年,他30歲,偕英國未婚妻首次踏上祖先故土印度,先後在孟買、德里、加爾各答、克什米爾等地遊歷一年。回到英國之後,他寫下了這本《幽暗國度》。
必須承認,此書對印度的描寫極其負面,結論極其悲觀。除了沿途遇到的幾位有趣而可愛的人物(比如作者下榻的一家船屋旅店的店主和聰明能幹的店員),以及克什米爾的壯麗山景,奈保爾在印度看到的一切,都令他震驚、憤怒、厭惡。可怕的貧窮、骯髒、停滯,僵化低效的官僚機構,古老種姓制度造成的深入骨髓的不平等,多次外族入侵和征服帶來的扭曲心理和失敗主義的逃避心態,荒唐的文化幻覺,消極的人生哲學,後殖民時代印度精英階層對英國風俗的滑稽模仿……與故鄉長達一年的初次接觸,使極度敏感、性情激烈的奈保爾幾乎精神崩潰。旅行即將結束時,他心情忐忑地前往自己祖先生活過的村莊探訪,但起初的一點浪漫情懷迅速蒸發,厭惡的情緒隨之達到高潮;無法忍受窮困族人的糾纏索求,他倉惶離去。最終離開印度時,他像在逃離一片被詛咒的瘟疫之地。
批判故土 刀刀見血
奈保爾的目光銳利無情。在他筆下,印度城鄉醜陋凋敝,印度文化不可救藥,而身在其中的大多數印度人對此卻可悲的麻木無感。毫不意外,《幽暗國度》剛一出版,即在印度被禁。過去十年當中,我因工作之故去過印度很多次,身邊也有不少結識多年的印度朋友。總的來說,我深感印度人和我們中國人一樣愛面子,對自己文化傳統的驕傲自大,比我們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奈保爾揭露、抨擊起印度的「國民性」、「劣根性」以及印度阿 Q 的「精神勝利法」來,那真是有十分力氣絕不用九分半。其犀利刻毒、刀刀見血、一個都不饒恕,實在與我們的魯迅先生可以一拼。
但魯迅把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罵得狗血噴頭,卻被尊為中華民族的良心和脊梁。因為自五四以降,挖祖墳一直是中國知識界和文化界的時尚事、熱鬧事,魯迅生前的所謂孤獨,其實多少有些矯情。他身後在偉大領袖力挺下繼續紅得發紫,也不能算是意外。再說魯迅到底是土生土長,那些諷刺挖苦的文章全都是用漢字碼出來給中國人看的。關起門來數落自家的醜事、臭事,大家到底比較容易接受。
奈保爾完全不同。這位婆羅門後代長了一副印度面孔,卻身世複雜,文化認同曖昧。他基本上不會講印地語,終生用英文寫作。他生活在倫敦,卻深感自己是個局外人。作為地理和文化雙重意義上的自我流亡者,他不止在印度,在任何地方都難以找到終極歸屬感。疏離感與他永生相伴。
但在印度人眼裏,奈保爾或許類似於魯迅筆下的「假洋鬼子」。難道他不是狐假虎威、用西方價值觀來裁判和誣衊印度人,以此迎合白種帝國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印度文化博大精深,他卻將它說得一無是處,難道這不恰好證明了他的膚淺狂妄、數典忘祖?他以為他是誰?事實上,雖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奈保爾至今在印度仍然名聲不佳。我認識的一些印度學者朋友,提起奈保爾就火冒三丈,總要將他從作品到人品貶得一無是處才算罷休。
作家的反省
要說奈保爾那支筆,有時確實太尖刻;他的觀點,有些也太偏激、太絕對。半個世紀後,今天印度的社會狀況與《幽暗國度》中的某些描寫已經相當不同。時過境遷,奈保爾本人對此也不無反省。90年代他重返印度旅行採訪,寫下「印度三部曲」的最後一本《印度:百萬叛亂的今天》。書中對印度社會的活力和轉機寄予一定希望。結尾處,他坦承自己初訪故鄉時是「心懷恐懼的旅行者」,對當時剛剛獨立十幾年、仍在尋找自我重建的複興之路、處於轉折期的印度社會的某些面相不夠理解。
年齡是另一因素。早期的奈保爾是個十足的憤青。無論寫印度還是寫其他穆斯林國家,他下筆一貫激烈、尖刻、毫不留情。比較之下,他的晚期作品則相對溫和、寬容。
融匯多種寫法
不過,無論有多少瑕疵、有多大爭議,《幽暗國度》無疑是經典之作。血氣方剛的奈保爾對印度歷史、文化和人性那些富有穿透力的描寫和洞見,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讀來,仍然震撼人心、促人深思。書中許多場景和人物,仍然存活於今天的印度——我就曾在孟買和德里的街頭巷尾多次撞見。感性而富有節奏感的優美文筆,閱讀實是享受。此書的精彩和卓越,還在其敘述方式上的創新,以及敘述者那獨一無二的視角和聲音。在這本遊記裏,奈保爾融匯小說、自傳、歷史、評論等各種手法,將個人經歷、家族歷史、民族風俗分別嵌入敘述當中,將自己與印度、英國、特立尼達這三個國家、三種文化的不同關係,輪番置於顯微鏡下,逐一審視、描繪。在精準細膩的敘述中,充滿張力、寓意豐富的圖景一幅幅凸顯出來,猶如燈光照射下漂浮在沉沉夜海上的一個個船屋。奈保爾不愧是駕馭這種雜糅文體的大師。
不難想像,這位神經質的老兄在生活中,大概是個難以相處的刺頭。奈保爾天性敏感、自尊、多疑。他太易怒,口無遮攔。但他的寫作卻既是激情的,也是冷靜的、誠實的。或許,恰恰因為他與他的描寫對象,始終保持着一種充滿矛盾、苦惱與警惕的距離,這位遠道歸來的陌生人、局外人、旁觀者,對於他祖先故土的認識,要遠遠勝過許多生於斯長於斯的印度人。
原刊於高和分享微信平台,標題為本社編輯所擬。
(封面圖片:設計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