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慧怡的《不帶感傷的回憶》,找來張曼儀(她是我老師馮以浤的妻子)寫序:「繁花似錦,曲徑通幽」。張教授說得好,這本書「不是哀傷的追悼,而是快樂光影的回味」。
書中有好幾位算是認識的,有同輩,有老師,有只有一面之緣,卻是一見難忘,印象深刻。孔慧怡書寫他們的時候,我們早已沒有見面。原來同一個人,在不同人生階段,出現我們眼前,會讓人有不同觀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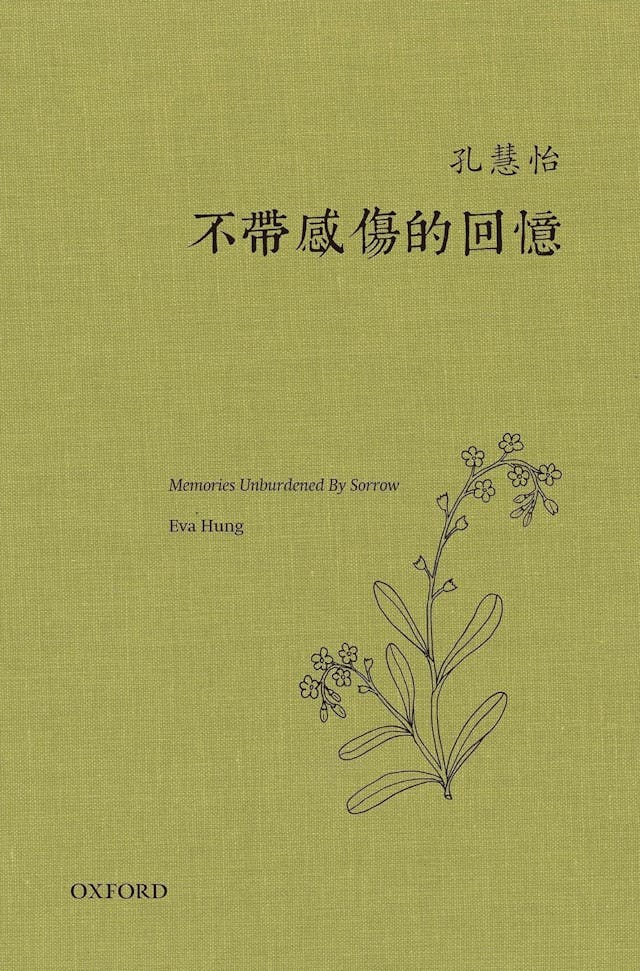
昔日好時光
張曼儀說孔慧怡「不寫大名鼎鼎的朦朧詩人顧城,而懷念他的妻子謝燁,叫人看到她那『花瓣般嬌嫩」的『粉紅粉紅的笑臉』」。
謝燁是「生命的小說家」,是「以口述的方式把自己的人生編成故事」。當年顧城與謝燁路過香港,住在孔慧怡為他們在中文大學安排的宿舍,而我又找到機會,與顧城在港台談他的詩作。
翻查當天的訪問紀錄,顧城說「我們是在空白中長大的孩子,有一種長久的幼稚和天真」。回想起來,當天給我們印象最好的是謝燁,那時謝燁大着肚子(她說孩子還有幾個月就會出來了),在用膳的時候,忙着幫丈夫添菜(我們在訪問後到沙田吃晚飯),又談她的遭遇。雖然不知道明天怎樣了,謝燁卻「天真」相信,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戴着牛仔布帽的顧城,坐在飯桌前,心不在焉。沒法知道他在想什麼(他不怎麼愛說話,與在港台談詩、誦讀詩時,完全兩個人),他寫過一首詩《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他承認自己就是「詩中的孩子」。
只是那時我們並不知道他是個任意妄為之人。

太空人
在《不帶感傷的回憶》,孔慧怡有一篇介紹〈也斯:心裏美〉的文章。也斯介紹作者去一間北京小館:「有個菜一定要嘗嘗,叫『心裏美』。我先不說是什麼,你嘗了就知道。」
那時已經很少見也斯了,他有他的忙碌,我有我的生活,活動圈子不同,見面機會自然少了。
2023年12月9日收到也斯太太Betty的WhatsApp,說有出版社將會出版也斯選集,分詩、散文、小說。傳來一首也斯詩作《渡葉》,希望我寫篇讀後感。
Betty說:「也斯的《渡葉》1988年寫於溫哥華。溫哥華機場有Bill Reid的大雕塑,不同種類、不同個性的動物,帶着不同的希望,同坐一條小舟渡海,從一個地方移居到另一個地方。」
我們都是「港漂」一族,從一個城市搬遷到另一個城市。以為找到安居之所,可留下來了。在一個地方生活了那麼多年,都習慣了,該不會再漂流的了。
也斯的孩子已移居溫哥華,在那裏繼續學業、事業。也斯則要留在香港,在大學任教。他不是「穿梭的太空人」、「逍遙遨遊」香港與加拿大,他只是「一個孤獨的父親來回穿梭」兩地。像不少香港人一樣,為了生活,成為「太空人」。
一個人離開了「熟悉的語言與泥土」,可會有「連根拔起」的痛苦。
像《渡葉》中提到的動物「海貍」,為了過不一樣的生活,不得不移居海外。人也一樣(人也是動物呀),總有不得不生活在他鄉的理由。
也斯不是「海貍」,他會不會是「水陸兩棲的青蛙」?為了下一代,不得不「來往穿梭兩個不同國度的邊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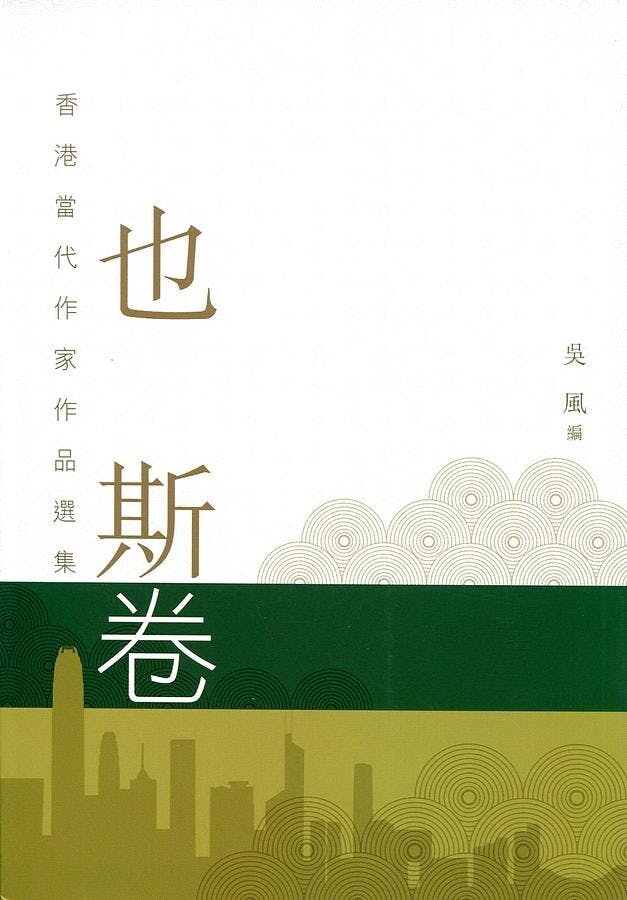
披風一轉
孔慧怡《不帶感傷的回憶》談〈黃兆傑:那披風一轉〉,道出作者的事業和人生,「黃兆傑就是那輕拍翅膀的蝴蝶,事隔20餘年,蝴蝶效應才充分顯示出來。」
作者念中學時,學校上演中文舞台劇《萬世師表》,中文話劇得要有一個英文名,臨時起的An Ideal Teacher,「連學生都感到Far From Ideal,難登大雅之堂。」
在香港大學任教的校友黎翠珍,把這個翻譯難題交到翻譯系的Dr. Wong手上,「一個星期後,有了旗鼓相當的英文名:An Undefiled Heritage。」
因為黃兆傑,孔慧怡走上翻譯研究之路,若干年後到英國唸博士,如寫序的張曼儀所言:「結果不但完成學業,並且成就了一段美滿姻緣(成為卜立德教授的夫人)。」
在港大的第一學年,孔慧怡上黃兆傑課:「時值深冬,他披着斗篷走到講桌前,雙手掂起斗篷兩肩的部分往上一舉,同時來個360度轉身,斗篷像塊墨雲在空中旋轉一周,悠然下降,剛好落在講桌的椅子背上,一絲不苟地掛在那兒。」
黃兆傑到港大任教前,先回母校教了幾年書。也是冬天,他愛穿上藍色長棉袍(那年代學生則可穿半身藍棉袍),在禮堂前與其他老師談笑風生。在課堂,他「有姿勢,有實際」。他教學生動有趣,穿上長袍的他雖然年輕,學生稱他「黃夫子」,他點頭稱善。
在大學與他共事20多年的張曼儀說:「慣見他嬉笑怒罵、謔而不虐的作風(遇到深惡痛絕的人,也會謔而虐的)。」
黃兆傑辭世而去。他的家人帶了一份他的心意返回母校:一筆獎學金,用來獎勵喜歡藝術、創作的同學。

原刊於《星島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綜合轉載,題為編輯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