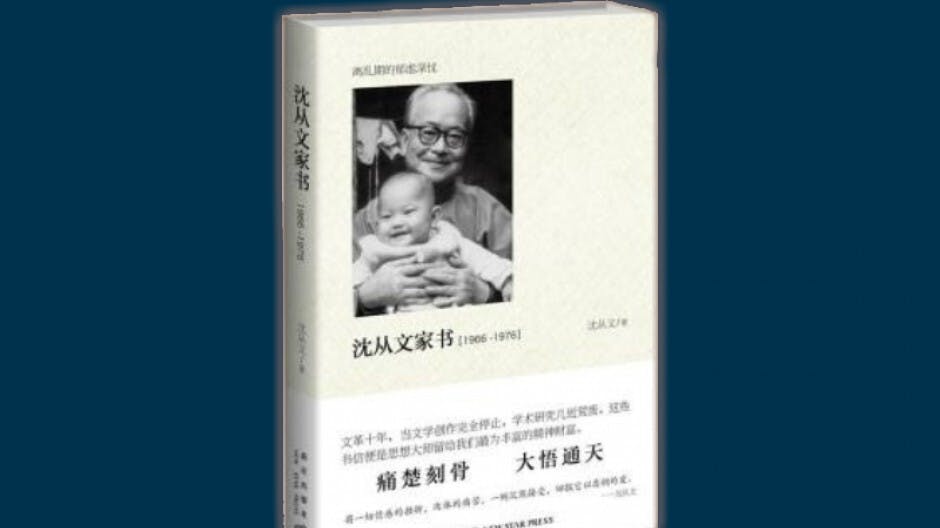撰文:啟之(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
推薦語
此書收入了沈從文文革十年間寫給家人的83封信。這些信有三大好處,一,有助於了解當時的社會,尤其是運動的情況。二,有助於了解當時民眾的生活,尤其是知識人的生活。三,有助於了解沈從文的思想活動,尤其是他對自己和國事的看法。
家書告訴我們,1967年初,刮起了「經濟主義」之風,上百萬外省人湧入北京,不少人懷揣着幾百元人民幣,到商場搶購日用品。 「百貨大樓出售手錶等特種物資的,已由紅衛兵把守,不再出售。東安市場的東西也多入庫。且有用大卡車把這種搗亂分子連同所購東東西西遊街示眾。」「北京大街上和一切機關,還是大字報佔領一切牆壁,天安門除了人大會堂和博物館不許貼,此外看台和兩側廣牆及地面,是標語大字報的海洋。」
家書還告訴我們,政治高燒並不妨礙人們保健延年,1966年底到1967年上半年,「雞血注射」流行,一時間,公雞銷路看漲。而與打雞血相伴的是那些或真或假的政治新聞:蕭望東、李維漢、王任重、劉瀾濤等坐卡車掛牌子遊了街。薄一波、羅瑞卿、鄧小平、陶鑄已經撒手塵寰。呂正操因鐵路員工罷工而下馬。四川的什麼請願團與北京的什麼兵團在景山戰鬥了好幾天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沈從文的內心矛盾:一方面,他慨嘆自己平生所學於新社會沒有用處,「我等已完全成為過時沉渣、浮漚,十分輕微渺小之至,小不謹慎,即成碎粉。」另一方面,又認為他所做的研究沒有人可以替代,並且時刻準備着重新投入到那未竟的古代服飾研究之中。
儘管沈從文努力掩飾對文革的看法,我們仍然能夠從字裏行間之中發現他對國事的「杞憂」:這樣搞下去,國將不國。
延伸閱讀 沈從文:政治灰霾中的文化情懷 撰文:唐小兵 《沈從文家書1966—1976》是一份不可多得的關於文革中的政治、文化與知識人心態的史料,他在動盪年代寫給妻子張兆和、兒子沈虎雛、兒媳張之佩等人的書信,呈現出晚年沈從文在面對政治摧折人情、真理毀滅常識的時代灰霾時,如何切實地守護讓生命的延續不僅僅是苟活的三重世界。 第一重世界是親情的世界,通讀這部文革時期的書信集,字裏行間着墨最多的是對於日常生活的記錄,以及對親屬的衣食住行的細緻入微的關照。沈從文是如此興致勃勃地向着遠方的讀信人,鉅細靡遺地記錄他所目睹的一切,包括孩子的成長、生活用品的價格變化、鄰里的變遷等,當然在這些書信中最多的是對於其時文革政治的細微觀察。這些觀察又穿插着他的理解與評論,自然,沈從文對政治的態度一直是胡適所謂的「不感興趣的興趣」,是一種疏離的洞察。 作為一個信任文學作品的力量的作家,他對政治有著一種本能的距離感。他也在寫給兒子的書信中,委婉地勸說後者走「專業主義」的路線,不要過多地介入政治。儘管我們可以站在道德的高地批評沈從文在向其子女傳授一種「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可是對於一個政治陰霾籠罩一切的時代,引導親人對政治保持距離感,也就是在舉世若狂的政治風雲中保持一種「有所不為」的立場,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消極的抵抗」吧。 正如阿倫特在反思獨裁政治下的個人責任時很有洞見地提出的那樣,在面對極權政治時,看似消極的服從其實就意味着積極的支持,那麼公民不服從,也就是一種有效地與體制性的惡之形成機制實現切割的方式。通讀沈從文這段時期的家書,極少讀到意識形態式的敘述,即使偶爾有一兩句應景性的政治語言,也是瑕不掩瑜。 這彰顯了一種罕見的語言品質,當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相當一部分在日常語言中,也無法擺脫政治語言和政治思維的幽靈時,沈從文卻以個體化的方式仍舊堅持了一種貼近事實和本心的言說方式,這無疑也是另一種堅持生活在真實中的表達,語言的真實,是跟歷史的真實同等重要的追求,現代獨裁政治迥異於傳統專制政治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前者發明了一套用詞彙、語句和真理構造的一元化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最大限度地壓抑了自發性和自主性的表達可能。這也從反面說明了此時此刻的沈從文具有多麼強韌的內心,來消解政治灰霾的壓力。 第二重世界是文學的世界。誠然,1950年代以後,震懾於新時代政治空氣的極端壓力,以及陰晴不定的文藝氣氛,一度陷溺在精神絕境中的沈從文基本上放棄了虛構性的文藝創作,而轉向了對歷史文物主要是中國古代服飾的研究。他試圖像同時代諸多知識分子那樣,對自己來一次刮骨療毒式的自我清算(其實質大多是自我污名和自我毀滅),在文學的領地裏有組織地重新起航,卻最終發現內心深處的「老虎」從未被完全地降服。他在這些吐露給親友的書信中毫不保留地傾吐著他對文學的理解,以及矢志不渝的熱愛。 在沈從文的價值世界裏,敘事的價值永遠是高於說理和議論的,他尊重的是敘述中展現的歷史、人性與情感,而新時代推崇的或者培養的諸多作家,在他看來,在寫作上都是缺乏基本功的。這種直言不諱的臧否,在這本書信集中比比皆是,這自然也相當於沈從文在含蓄地為自己被壓抑甚至消音的過去進行隱秘的辯護。 1968年3月9日,他在寫給兒子沈虎雛的信中說:「目下在大學裏國文系教習作的老師,會寫敘述文的就極少,會論事不會敘事,下去再久將不免還是若『目無所見,耳無所聞』。」與此相應的就是他對自己作為文學者的歷史與能力的自信:「五四以來有上千成萬人搞創作,大多數人全淘汰掉了,跑萬米式搞個廿卅年不斷努力的,不到十個人。少數人僥倖,機會好,成了『作家』,依然不久還是曇花一現的過去了。這個多數有許多理由不幹這個『費力不討好』工作,或教書,或做官,或經商,都比寫作容易得多。」對於當時的「計劃性」的作家培養模式,沈從文也很有保留:「四川學沙汀,山西學趙樹理,湖南學周立波,取法乎上,斯得其下,這那會出人才?因此全國一年搞一個短篇選集,看來還有許多不免湊數。一般缺點是既不會寫人,又不善寫事,更不知如何寫有特殊性風景背景……照《人民文學》過去的鼓勵方法,是永遠產生不了真正新作品的。學校則改來改去,也決不會從中文系產生起碼作家。」這些在書信中談及文藝的只言片語,充分說明了沈從文並未放棄他內心對什麼是好的文學作品的理解,他堅持了某種獨立性。 第三重世界是自我的世界。革命政治的終極訴求之一就是鍛造一種人類史上的新人種:社會主義新人或者說共產主義新人,而生活在毛時代的知識人卻大都是從民國一路走來的,按照出身論和階級分析的方法,像沈從文這樣的舊知識分子是不可能完全脫胎換骨站在人民一邊的,於是對待知識分子的洗澡、洗腦、清洗等各種運動紛至沓來,唯恐斯文不掃地。可是通讀沈從文的家書,會發現在如此極端的侮辱人的尊嚴和人格的時代,他仍舊在內心深處堅持了一種人格的完整性,而這份完整人格核心的精神品質就是個體生命的獨立。 顯然,沈從文對自己從民國一路走來不與任何黨派發生直接關係,也不依附於任何政治力量或政治人物,而始終堅持通過自己的寫作、編輯等工作來面對生活,有着一份執拗而充沛的自信,寫作成了彰顯自我的方式,而當公共寫作被禁絕的時候,書信這種私人性的寫作便成為沈從文表達對世人、世相的理解的唯一方式。 1969年9月,沈從文在寫給其兄長沈雲麓的書信中說:「我因為這卅年來,前廿年不依傍過蔣,近廿年又不沾文學,不和周揚有什麼關係,隻老老實實在博物館搞文物工作,不怕沉悶寂寞,也不懷什麼名位野心,凡事從頭做起。有一次讓我去作老舍作的那個北京市文聯主 席,也不去,寧願守著午門樓上陳列室作說明員,或鑽庫房搞文物登記,一個大學生也受不了的工作,我卻一作廿年。」在私人生活領域高度政治化的時代,沈從文仍然堅持認為保持與政治的適當距離,是一種值得讚許的正面價值,這無疑也表明了他對其生活其中的時代的某種態度。 沈從文自然不能算是人情練達之人,也非世事洞明者,與其說他對政治的態度是仔細權衡後的理性選擇,不如說他是將青年時代艱苦奮鬥的自主人格放大到了支撐整個精神世界於不墜的境地。他不是在有極限感的生命險境中去挑戰時代的禁忌,也不是面對荒誕的政治現實表達出一種虛無主義的遊戲感,他靠的是一種湘西鄉下人野蠻而通透的價值執著,以及對世界的一種審美主義態度。 自然,他不會將政治世界的猥瑣與荒蕪也審美化,在涉及那個高分貝時代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張力時,他毫不隱晦地批評這個時代的「分裂感」:「走後門似乎還在發展,不少事以人為重,不是以事為重,佔有位置即成功,幹不下,做不出成績,卻無所謂。奪了權,此外即不再過問。不免令人為國家深抱杞憂。」面對這樣一個時代,關鍵的問題是個人將何去何從?是同流合污還是避而遠之?或者充滿絕望感地反抗如與大風車作戰的唐吉可德那樣?沈從文在致其家人的書信中給出的是不同於以上三項的選擇。 在給其兒子沈虎雛的信中,他說:「作個『書呆子』比作個『混日子』的人顯然是不同的。前者或許會因對國家有個理想,受事實挫折而十分痛苦,但比一個『混日子的人』生命有分量,則極顯明。既不宜在『承認現實』中消極,還宜為『愛國家』而作一切努力。」這種理想主義的情懷有兩種面相,既有堅持個人生命價值的本真性的執拗,也有家國情懷的九死不悔。 正是這種個人主義與國家意識的兩種精神底色的交融,讓晚年的沈從文在自身已經完全邊緣化的時代,仍舊堅持一些最基本的人類價值,他平實的話語充滿了一種赤子情懷的感人力量:「熱情無私和正義感,在社會任何階段中還是需要的。還是會起好作用的。還會起連鎖反應的。就可能範圍內,至少把自己活得就堅強素樸而有力,而對別的人,也依然有積極意義和良好影響。」這無疑是貧病交加中的沈從文對生命的基本理解,這種人生態度,既有儒家君子人格中「任重道遠」的「傳教士」情懷,也有近代以來以胡適、魯迅等五四一代作家倡導的自主人格的底色。如今回首這個蒙昧而荒蕪的時代,會發現沈從文這些像獨白又像談心的家書內蘊著一種發人深省的精神力量。 (摘《南方周末》2013年7月30日)
原文刊於高和分享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