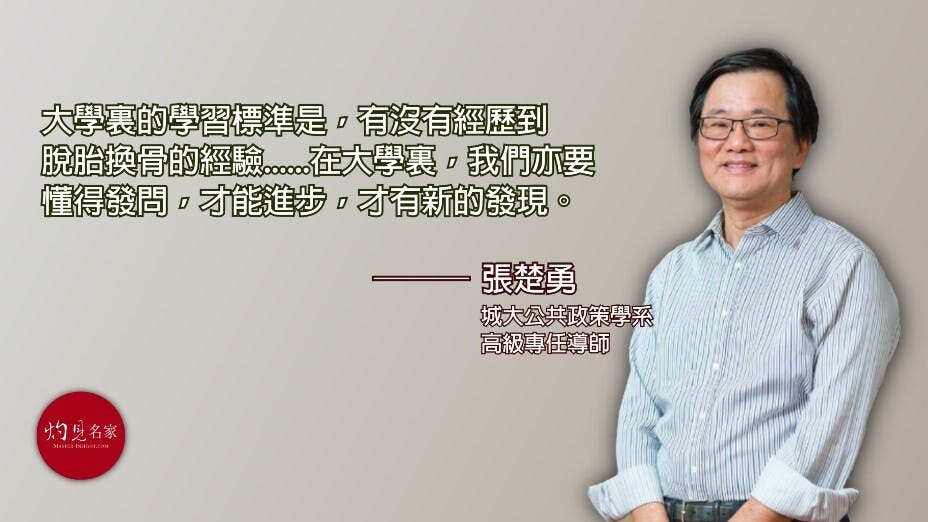「顧名思義,大學就得主張教授大而通達的知識。」(註1)
我在大學讀書教書30多年,對大學的教育有一定的看法。但這種看法,坦白說,不是什麼新鮮的看法,只是學界其中一項重要的傳統。此傳統現在提及的人還有一些,不過並不多,而真的去繼續實踐這傳統的人卻很少。我自己覺得這傳統非常重要,亦很有啟發性,所以決定談談這個題目。
這些看法是得益於一些前人和很多經典的著作。如果我只能為此介紹一本書,我推薦紐曼(John Henry Newman)的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在19世紀50年代,紐曼那時在天主教教會,希望在愛爾蘭成立一所天主教大學。因為成立這所大學,他一連講了9個重要的講座,後來成為了通識教育(Liberal Education)和大學教育的一本經典著作,這也就是The idea of a University。我真的很希望,我們的校長、老師在每年開學的時候,能像紐曼那樣,講一些類似內容和水平的講座,讓其精華可以留下來。
我這文章可以視為是對紐曼的大學理念的一個註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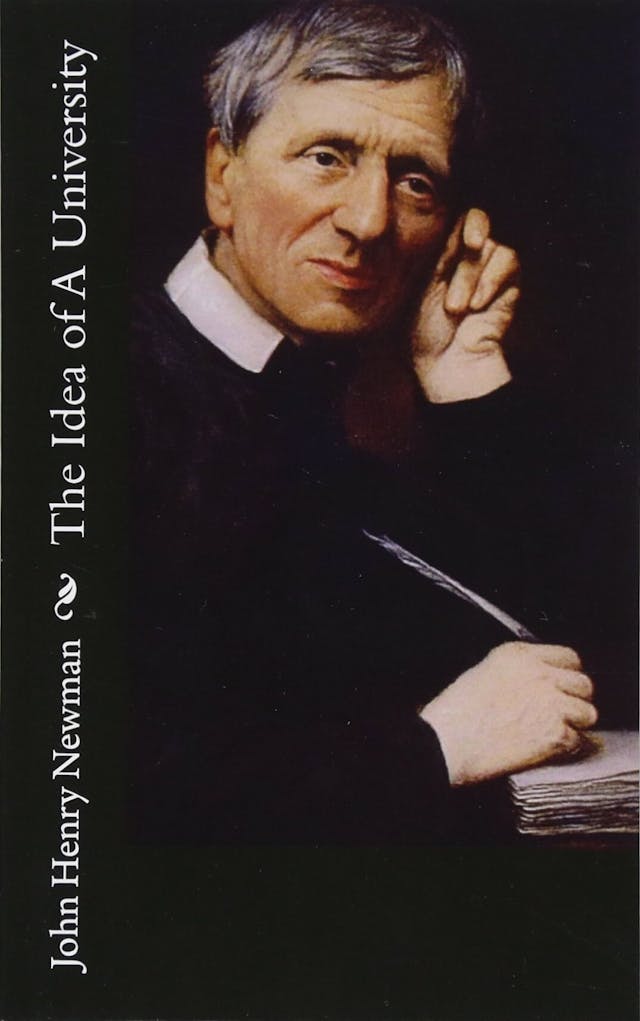
大學教育最獨特的地方,是進行人的文明教育
大學作為現代社會的最高學府,它的教育或求學問道的使命,理該有其獨特而不可被取代之處,與人類文明、人生處境、宇宙天地間種種相關的根本問題以及不斷碰到的新困惑,緊扣相連。
當下我們對一所大學的成敗判準,往往集中於其國際排名、畢業生在名牌企業的就業率、大學教授取得的科研經費、以及學校擁有的尖端設備等等。這些量化標準當然有一定的參考作用,卻容易使人誤以為大學主要是為企業機構培育能幹的員工,或教授的專題科研比啟迪本科生的整全教育來得重要。
如果大學教育的首要目的是為企業機構培育人才,大學便變成了職業訓練學校。以我自己以前在傳媒和政府的工作經驗來說,我在英國廣播公司和香港政府任職時取得的專業訓練,比起大學裏的傳理或公共行政學院的教育顯然是更有效實用。如果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養企業員工,那麼大學便難免被類似香港的職訓局或企業機構的訓練部門所取代。同理,如果大學主要是為專題科研服務,社會不如把資源用來成立各類高質素的專門科研中心,讓專家學者集中精力做他們的尖端研究好了。
我這樣說並不是認為大學可以漠視社會的實際需要,也不是主張大學毋須重視專題知識的拓展和科研的推進。我的意思是,大學教育最獨特的地方,是進行人的文明教育,讓師生在學習其本科專業知識之外,同時得對通達的學問認知和探索。這是因為人類文明是一個不停地變更的整體;這個整體儘管不一定十分連貫,但它既蘊含着卻又超越了種種常識、實用認知、以及個別專門知識的範疇。匯集不同學科的師生同時處於大學這個環境,去教授和學習各學科基礎水平以上的知識,讓各學科的學人在互相觀摩的氛圍下多作交流,是系统地提供人的文明教育最不可被取代的一種做法。
人類文明是我們文化成果的總和
大學為什麼要提供一個環境進行人的文明教育呢?這裏說的文明教育,顯然並非是指講禮貌守規矩這些在家裏和中小學時應該已學了的良好行為和品德,而是指人類過往累積下來的、方方面面的文化成果,包括在科學技術上的、哲理宗教上的、藝術文學上的、歷史社會方面的,以及人類各種行為和實踐建立起來的重要關係和行之有效的做法等等。這些成果有些是很古遠的,其起源可能已經「不足征」了(例如古代的神話或禮儀) 。但與此同時,另一些成果卻可能與我們今天的生活息息相關,還在不斷變化創新,遠遠未有定論(例如基因療法)(註2) 。這些成果不少可能是很有實用價值,很能幫助我們解决生活上遇到的種種問題(像工程學的技術) ;但更多的可能是與工具價值沒有直接關連,完全是人類心靈的好奇、求知(像探索宇宙的起源)、想像和表達(像不少音樂、抽象藝術) 。
進行人的文明教育,說到底就是要認識自己,認識人之所以為人。英國伊頓(Eton)公學的校長科里(William Cory)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句話:「你到一家了不起的學校,最重要的就是學會認識自己。」(註3)
人類文明是我們文化成果的總和。嘗試去認識這個總和,也就是嘗試在人到目前為止所能明白和所累積下來的種種意義中去進行認知和繼續探索。文明在當下為止取得的成就,體現了人目前的認識水平和能力的高峰;文明裏遇到的災難困境,反照出在經歷苦難時人性的黑暗、光輝、甚或是試圖超越的想像。至今文明無法突破的(不管是暫時性的或可能是永久性的) ,也就代表了人的局限,起碼是今天的局限。「止於至善」可以理解為儒家對人性是可以完美的一種信念。但一天人類未能「止」,一天人便仍有局限,仍然不完美。在不同的年代,人們對這個整體關注的部分可能不盡相同,甚至有不少部分會幾乎被遺忘;我們對這整體不同部分的理解和評價,也往往是前後不一致。但無論怎樣,我們不可能離開這個文明的整體來認識世界、認識自己,因為這就是人的視野,除此之外我們並沒有一個阿基米德支點來觀照世界。
這裏說的人的文明教育,也許可以簡稱為人文教育。它之所以是大,正因為它是對人之所以為人,嘗試有一個整全的認知,從而也讓學子認識自己,認識自己和其他人的關係,與文明的關係,天地萬物的關係。我認為稱職的大學教育必須包含人文教育,而大學在整個教育制度當中,也最適合推行人文教育。
如果大家讀過或正在讀大學,如何審視你接受的大學教育究竟稱職沒有?在此,我嘗試提供兩個準則。
第一,當你畢業時,你是否對自己作為一個人有認識。這也是上文引述科里所說的自我認識。
第二,就是在大學的學習經驗中,你有沒有學到了脫胎換骨的視野。
為何稱脫胎換骨?因為大學本身要教的、要大家看的是我們人類文化、人類文明中最精彩的東西,無論是關於科學的、文學的、哲學的、歷史的、技術的、科技的,你都是向最好的去學習。
文化精華事實上跟現實潮流有一段的距離的
你向最好的學習,傲然天海,博大精深。你可以跟孔子對話,亦可以跟蘇格拉底對話,跟歷史上人類文化流傳下來的、從古至今最好的東西砌磋。因此,你應該要學的就不只是在街邊的、只是常識性的,經常接觸到的東西。我不是說這些東西不重要,但它們應不是你唯一或最主要的學習對象。例如報紙文章、媒體資料等,它們多是一些未經考驗、未經篩選、未經審定的東西,是在現實世界、社會中經常發生但往往不久即被淘汰的東西。但是人類的文明、人類的文化是累積下來的,汰弱留強,將不好的淘汰,遺下的是千百年、甚至幾萬年裏最聰明的人、最好的頭腦都認為這些是好東西,不只不能不學,而且還未被超越。在大學裏,正是應該要學習這些東西。
如果我們認真學好這些東西,不難發現,文化精華事實上跟現實潮流有一段的距離的,因為現實世界良莠不齊,往往宥於一隅,打破不了一時一地的局限。我自己在香港大學唸本科的時候,覺得跟外面的社會便很不同。為什麼呢?因為大學是討論和關心大問題的。那時有兩本書,最近因為要準備這個題目,便翻查當時的資料。相信大家都知道,那時新亞書院有一本書叫作《望道便驚天地寬》,連名字也與眾不同,很有些氣勢。另外一本書也是很重要的,叫《敢有歌吟動地哀》。以前中學時都不說這些的,沒如此豪氣、有氣魄。最重要的,是大學生關心的跟現實和當下的社會截然不同。他們主要不是關心將來是否考政府的政務官AO,或是當律師醫生,而是究竟我們要怎樣去認識這個世界、認識中國/香港、認識殖民地的政府、殖民地的社會是什麼等等。外面的世界、當時的香港跟大學的世界是兩個世界,大學裏所關心的是一些比較長久的意義、比較深刻的意義,這起碼是在比較活躍和勇於思考的大學生之中是這樣。當時進到大學覺得真的和現實社會視野不同,有些震撼。
經典著作的精華在於其深刻的道理
我們那時候能考進香港大學也自覺挺能幹的,書也像讀得不錯。但我一開始進大學讀哲學時真是要命。第一,要精讀大師的著作。我記得當時讀康德(Immanuel Kant)關於道德哲學,深刻的感到為什麼他的思考能如此有邏輯、有系統,真是佩服。你讀康德時會覺得他很有說服力,很對的;但是讀休謨(David Hume)時,他說的不少都是相反的,卻也同樣有說服力。那麼誰對誰錯呢?我有否自己的想法呢?我們那時讀哲學系一定要讀原著的東西,不能只讀二手的東西,一定要讀經典著作。第二,上導修堂的時間真要命,一位老師對着兩位學生,這星期你做報告,下星期輪到我,如此類推、周而復始。還有老師都是:你說任何看法,包括康德的看法也是沒用的,因為他必定挑戰你,最重要的是要你有自己的看法、解釋為何你會有如此的想法、你的想法是否defensible(能辯解的)等等。這樣跟在外面,尤其是媒體式或立場主導的文章,在深度上和意義上很是不同。
經典著作的精華不一定在其結論,而是在於其深刻的道理,其視野並不宥於一時一地的關注。能夠在學問上自成一個學科,往往是因為它看待事物的有效方法與我們以常識看待事物的方法不盡相同。如果以常識看待事物的方法已經足夠,我們便不需要學科,也用不着建立一所大學來學習。但若果我們看着太陽圍着地球轉動便已足夠,便不會發展到今天的天文物理科學。它用另一種視野與角度,才發現原來我們從前直觀以為是對的事情,往往只是表象;而經得起考驗的學科,在我們老祖宗一直流傳下來的,那些無論是東方的或西方的,最初可以留下來的書籍大多是離不開人類活動中涉及比較根本的關懷。中國最早期的書是《尚書》、《易經》、《詩經》等:即是現今的哲學、文學或是歷史、政治。西方的書籍最初也都是這一類。

我是讀政治學的。古希臘柏拉圖的不少對話錄,便是西方早期對人類政治活動和行為的深切思考。他去理解政治,並非只去探求政府在做什麼,政治領袖們怎樣爭領風騷,政治集團如何壯大自家的力量等等,而是嘗試釐清,人的行為,哪些屬於政治,和其他範疇的人的行為在性質上有何根本的分別?在這公共範疇內面對不同的利益和考量,哪什麼才是公正?他有感於古希臘城邦紛爭不斷,歷史上由人建立起來的制度看來是早晚逃不了腐敗一途,於是他試圖有系統和尋根究底的去探問,如果我們有機會一切重頭開始,我們能設計出不會腐敗的、公正優良的制度嗎?建立這樣的制度的憑藉為何?是人力可能範圍的事嗎?這些敲問、探求、反省,都在他的《共和》(The Republic)一書中精彩的討論到。不管其答案能否說服我們,但其主旨和關懷,不單深刻有力,更超越古希臘的城邦時空,到今天21世紀依舊困擾人心。
這些經典為何能留下來、成為文化的起點?這是因為它們協助文明逐漸確立了人的觀點,而這些觀點經歷了幾千年還是站得住腳,超越了當時代的關注,從現在來看,還是能看到很多我們用常識、用平常的視野看不到的東西。
脫胎換骨的經驗
人類文明的累積就是通過我們的科學、歷史、哲學、政治、心理學、文學、藝術等等去看這個世界,而這些正是常識不能給我們的,因此才需要這些學科。讀社會學的朋友可能會經常聽到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社會建構的現實)或者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社會學想像)。這些imagination跟我們常識的看法不同,進大學就是要學習這些東西。當然亦可學習較實用的東西,這也是需要的;但如果讀大學不讀相關的經典,你不會脫胎換骨,你會看不到這個世界的多樣性與統一性。你會察覺從人類文化歷史留下來的那些經典看法、著作,雖然它們之間會互相矛盾,但正正因為這些看法經得起考驗,能刺激你去思考認識,刺激你看到平日你的視野看不到的東西,所以我覺得你別問其他,如果你自己作為一位大學生,你便需要看看你那幾年的大學教育裏,究竟你學了多少,而不是純粹想着畢業後能否找到工作。當然找到工作亦是重要的。但作為教育,無論你住在舍堂,或是上課,你學習的、與人交往的震撼有沒有脫胎換骨的經驗?現在有外國的同學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學在我們的大學學習,同學又能到外邊當實習和去交流,你會否從這些學習經驗看到一些你在香港完全看不到的東西,並發覺原來香港在這方面的經驗可以是頗片面的?經驗片面,也不是代表我們比別人差,而是代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認識迫你反省。
這些機會如果做得好的話,便正正是一些震撼。就是說我們習慣的視點受到衝擊,而通過那些已建立的、經歷了時間考驗的學科,學習當中的精華,無論是技術的或知識的,然後加以反省:我是誰?我們在做什麼?我們之所以是我們,是為什麼呢?我們與別人的關係是什麼關係?我們與這個世界的關係、與萬事萬物的關係?了解這些關係是否可以改變它們,甚至深化這些關係?
因此,大學裏的學習標準是,有沒有經歷到這些脫胎換骨的經驗(transformational experience),而這些transformational experience,是通過大學的環境和學科得來的。當我去理解紐曼所說的universal knowledge(大而通達的知識)時,我認為是和我以上的論說有些類似。學問之所以為大,大學之所以為大,正正就是說要學習我們人類已累積下來並一直在發展的最好的東西。在大學裏,我們亦要懂得發問,才能進步,才有新的發現。如果我們不能夠吸收好的東西,發問的問題亦自然不會好;如果我們能夠吸收好的東西,即使未必有答案,亦能問得好。那怎樣才能學到好的東西呢?大學須緊扣整體人類文明的發展、宇宙間的萬事萬物。但那麼多怎麼學得了?莊子所說的無涯治:「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這也是真的,也可算是文明人的苦惱。
註1:“A University…by its very name professes to teach universal knowledge”。見John Henry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頁25。我這裏對大而通達的知識的理解,和紐曼(Newman)的理解不完全一致。關於紐曼的看法,可參考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的”Discourse II: Theology a Branch of Knowledge”和”Discourse III: Bearing of Theology on Other Knowledge”,見頁25-57。
註2:請參考2014年2月8至14日的The Economist,頁67-68的”Gene Therapy: Ingenious”。
註3:科里這句話原文的上文下理是這樣的:”[At school] you are not engaged so much in acquiring knowledge as in making mental efforts under criticism…A certain amount of knowledge you can indeed with average faculties acquire so as to retain; nor need you regret the hours you spend on much that is forgotten, for the shadow of lost knowledge at least protects you from many illusions. But you go to a great school not so much for knowledge as for arts and habits; for the habit of attention, for the art of expression, for the art of assuming at a moment’s notice, a new intellectual position, for the art of entering quickly into another person’s thoughts, for the habit of submitting to censure and refutation, for the art of indicating assent or dissent in graduated terms, for the habit of regarding minute points of accuracy, for the art of working out what is possible in a given time, for taste, for discrimination, for mental courage and mental soberness. And above all you go to a great school for self-knowledge.”,轉引自”The Voice of Poetry in the Conversation of Mankind,” Michael Oakeshott,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62,頁200。
「學何以大?我對大學教育的一些看法」三之一
本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