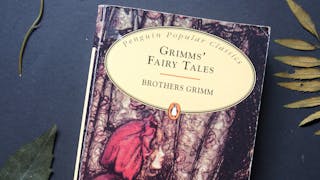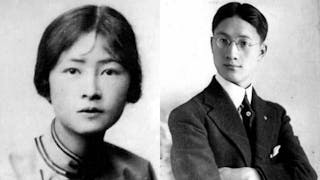法國總統馬克龍近期在法國外交使節年度會議上發表內部演講,認為西方霸權或許已近終結。近代以來,法國的啟蒙運動、英國的工業革命和在兩次世界戰爭中崛起的美國,讓西方世界偉大了300年。不過,今天,西方因為種種內外因素,其所確立的世界政治秩序正在動搖。同時,非西方政治大國尤其是中國、俄羅斯和印度崛起了,這些國家的政治想像力超越了今天的西方;它們在擁有了強大的經濟實力之後,不再迷信西方,尋找自己的「哲學和文化」。
馬克龍的這番話的確是對世界秩序的現實思考。不過,他過度誇大了其他政治大國的「政治想像力」。這些其他大國的崛起是不言而喻的,但很難說這些政治大國具有法國啟蒙運動所具有的「政治想像力」。現實的情況是,當西方面臨巨大的困境時,這些其他政治大國的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仍然對自己的「哲學和文化」毫不自信,仍然以西方文化為旗幟,幻想着自己能夠搖身一變,成為西方。結果,這些政治大國面臨着「知行不一」的困境,即這些國家的崛起是基於其自己的「哲學和文化」,但其民眾的「政治想像力」仍然是西方的。「知行不一」無疑是這些政治大國所面臨的最大政治挑戰之一。
以香港為例
這裏不討論其他國家,只想從近來的香港問題入手來討論中國,試圖回答為什麼中國很難產生馬克龍所說的「政治想像力」,其知識界也很難產生法國式的思想啟蒙運動。
如果從「知行合一」的角度來看香港問題,便不難理解。一旦「知」出了問題,「行」必然出問題。如果去問香港的抗議者,甚至是暴力行為者,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會回答:他們都是在爭取實現自己的理念或者理想。儘管大多數人譴責暴力行為,但暴力者本身並不必然這麼想。在心理層面,激進行為大都是「理念+理念的道德化=正義」這一邏輯的結果。
問題在於這樣的「知」是如何形成的?「知」的來源多種多樣,但從小到大的教育經歷無疑是最主要的。為什麼香港的抗議者大多都是1997年回歸之後成長起來的一代?這是一個須要深刻思考的大問題。香港本來是殖民地,思想被殖民並不令人驚訝。令人驚訝的是1997年回歸之後的教育更具有「殖民」色彩,從以往的被動殖民教育轉變成為主動殖民教育。從前的教育是港英政府所施加的,而回歸之後的教育則是香港自發的,並且具有明顯的目的性,那就是抵制中國的影響和培養及強化西方(非香港)認同。
同樣,問題得不到解決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抗議者所擁有的「知」和執政者所擁有的「知」相去甚遠。如果兩者是一致的,執政者就很容易接受抗議者的要求。是否就是抗議者要求「民主」而執政者反對「民主」那樣簡單呢?顯然並不是這樣。抗議者所要求的,是一步到位的民主(或者西方式民主),而執政者認為這樣的激進民主或者民主方式並不合適。較之抗議者,執政者所面臨的內外部制約更多,所須要考量的實際問題更多。
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期許
今天香港所面臨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在國家民主政治發展進程中所面臨的一個困境,即國家需要什麼樣的民主?這個困境在民國時代經歷過,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經歷過,今天的香港在經歷,而明天的中國大陸也同樣會經歷。
年輕人變得如此激進,教育者負有很大的責任。教育者的「知」出了問題,學生的「知」必然出現問題。
史學家許倬雲教授最近通過對北宋張載的四句話的「曲解」,來討論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角色,很有一番新意。這四句話便是廣為流傳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認為,這四句話可以說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期許,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四個方向或維度。
- 「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釋自然現象和宇宙意義,屬於理念的維度,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學家。
- 「為生民立命」者,屬於實踐的維度,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是把理念付諸實踐的執行者,也許是官員,也許是社會領袖。
- 「為往聖繼絕學」,也屬於實踐的維度,想辦法擴大並傳承所學,盼望後來的人能學得比自己更好。
- 「為萬世開太平」,屬於理念的維度,這個類型的知識分子能提出一個理想境界──理想的社會、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態度,盼大家往那個方向走,並且用這些理想來針砭、批判、矯正眼前所見的不合理地方。
一般來說,知識分子對現實都具有批評性,充滿理想,相信現實應當改變(無論是通過改革還是革命)來符合其理想。對這一點,人們並無很大異議。問題在於:知識分子應當擁有怎樣的理想?理想從何而來?是烏托邦還是着眼於現實國情?
全盤西化易導致水土不服
許教授認為,「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和傳統知識分子(「士」)已經大相逕庭。五四以後,主張全盤西化的知識分子佔據主流,並且愈來愈左,基本上都是要把西方的一套系統全盤端進來。西化派人物實際上是“Intelligentsia”,而不是“Intellectuals”。根據許教授的解釋,所謂“Intellectuals”是指那些在本社會、本系統之內,或做解釋工作,或懸掛理想,或做良師、良吏的知識分子;而“Intelligentsia”只是知識分子中的某一些人,他們意圖將另一個文化整盤端進來,從那個花盆移植到這個花盆,從那一土壤移植到這一土壤。
在西方歷史上,“Intelligentsia”原本指當年東歐學習法國的先鋒人馬,例如,波蘭曾有一批人要全盤學習法國;俄國彼得大帝以後,有一大批“Intelligentsia”出現,主張全盤西化。這些“Intelligentsia”,初心高尚,希望國家改革一步到位。不過,他們通常面臨的情況是外來事務與本地土壤不適合,端進來的東西要不是削足適履,要不就是去改變土壤,而不會去改植物。結果怎樣呢?改植物,是橘移淮為枳;改土壤,就是徹底把土壤改過來。
不論如何,中國近代以來已經有諸多類似的做法,但都失敗了。當然,失敗的不僅僅是中國,很多經歷類似政治試驗的國家也都失敗了。
在亞洲,要算成功的只有日本。日本明治以後,也有大批的“Intelligentsia”主張全盤西化,所謂的「脫亞入歐」,不過日本做的只是表象文章,他們骨子裏都是日本人,只是外面着上了洋裝。的確,如果撇開那些工具型的不談,深入到日本各項核心的制度,就不難發現沒有任何日本制度是「進口」的,都是根據日本本身的實踐形成的。因為戰敗,日本有一些制度為外力所強加,但日本人也一直在抵制。直到今天,日本人仍然在努力地想「推翻」美國為其所起草的憲法。
回到中國的例子。近代以來,因為全盤西化不僅很難在中國獲得成功,而且經常造成不小的災難。但西化派基本上沒有反思能力,因為他們往往把他們所接受的西方世俗價值,當作一種具有宗教性質的東西來信仰;並且,他們也簡單地把責任推給執政者或者老百姓。這就造成了執政者和知識分子群體之間的深刻矛盾。
知識與官僚的「斷裂」
在中國傳統上,因為「士」這個階層既是知識分子,也是政府官僚,因此在知識分子和政府之間並沒有什麼大的矛盾。皇帝不僅把「治權」(即相權)給了知識分子,而且更把知識領域留給了知識分子。「知識參政」便是知識分子的一個「共識」。
這一點到了晚清並沒有改變。從張之洞(1837年-1909年)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康有為(1858年-1927年)的「托古改制」,都是中國知識分子試圖找到一條以中國為主體、兼學西方的道路。
晚清廢除科舉考試對知識階層構成了致命的打擊,因為這樣做就把知識分子和政府分離開來,沒有了把兩者連接起來的「橋樑」。
晚清以來,大凡改革或者革命或者社會運動,知識分子都會衝在最前面。這並不難理解,儘管科舉廢除了,但知識分子的「知識參政」心理已經是一種歷史文化沉澱物,不會輕易消失,一旦出現機會,還是會拼命參與到政治中去。
不過,正是因為知識和官僚兩者之間的「斷裂」,晚清以來的「知識參政」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知識參政」完全失去了傳統上的現實感,而表現為烏托邦空想和由此而來的激進化。因為知識分子不再是官僚,他們既不用考量一項價值的現實可行和可操作性,也沒有機會來參與到政治現實中去來了解現實。
這種局面又進一步造成了「官學」和知識分子之間的深刻矛盾。傳統上這兩者是一體的,因為知識分子就是官僚,所有的「學」都是「官學」。
但近代以來,「官學」和知識分子就分離開來。政治人物開始把「官學」的權力抓到了自己手中。從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開始,到蔣介石、毛澤東到後來的所有主要政治人物,他們都有系統性的政治論述。無論是革命時代還是建設時代,政治人物總是處於一線,是第一批實踐者。他們較之其他群體更早、更深刻了解實踐,哪些價值可行,哪些價值不可行,把實踐融合到自己的理論思考之中。
學者的兩種選擇
同樣重要的是,這些系統性論述並非某一個政治人物的個人思考,而是反映了以該政治人物為代表的整整一代政治人物的思考。正如鄧小平強調的,「毛澤東思想」代表的是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的思想,而非僅僅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也就是說,那一代人對自己身處的「官學」是有「共識」的。
知識分子在知識創造過程中的劣勢地位是顯然的,這也促成了「官學」與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認同「官學」者就看不起知識分子,認為他們脫離現實,只會空談;而知識分子也看不起「官學」,認為他們過於現實,毫無理想,甚至只是為了個人利益。今天,這種矛盾現象愈來愈嚴重。基本上,無論是今天的當政者還是學者都是知識分子,只是當政者是具有實踐機會的知識分子,而學者則是沒有實踐機會的知識分子。
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實踐機會的學者的選擇是什麼呢?人們可以先撇開那些只是「輔助」「官學」者不談。學者中間最普遍的選擇有兩種,一類為「專家學者」,一類為批評型知識分子。但很可惜,這兩類的實際效果都是「全盤西化派」。
「專家類型」的學者表面上專注於「解釋」事物,根據西方的「八股」發表文章。這方面,今天中國學者所發表的文章數量愈來愈多,中國也已經成為一個論文大國。問題在於,文章眾多,但沒有出現任何原創性的思想。
核心在於,這類學者所研究的命題大都是西方的,只是用中國的材料來論證西方的命題。很多人從來就沒有想找到過中國本身的命題,用中國材料來研究中國命題。
此外,大學有關部門嚴酷的考核制度的核心就是論文出版和排名,這也逼使學者成為了西方式工具的「奴役者」。實際上,這種似乎非常「學術」的途徑是傳播西方思想最有效的手段。理由很簡單。第一,命題決定結論,用西方命題來研究中國只能證明西方的「正確性」;第二,由於西方命題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命題要不得不到確立,要不就根本無人去找。在目前的考核制度下,這類學者已經佔據各大學、研究機構的主導地位。
第二類即是批評類型的知識分子,廣義上說包括今天的「公共知識分子」。這類知識分子愈來愈多,西方化趨勢愈來愈嚴重。近代早期的知識分子儘管提倡西化,但他們還受中國傳統的深刻影響。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傳統完全消失,一些人一方面痛恨自己的傳統,另一方面也根本不想了解西方的真實情況是怎樣的。對這個群體來說,「西方」的學術意義並不重要,因為他們只需要西方的「工具」意義,即用西方來批評和評價中國的現實「政治」。
這也是最不確定的地方。儘管近年來人們在呼籲「文化自信」,但在實踐層面則是「西方化」的加速。如果不能確立中國自身的「政治想像力」,就不會有可以解釋自己實踐的社會科學,最終難以避免「知行不一」的局面。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