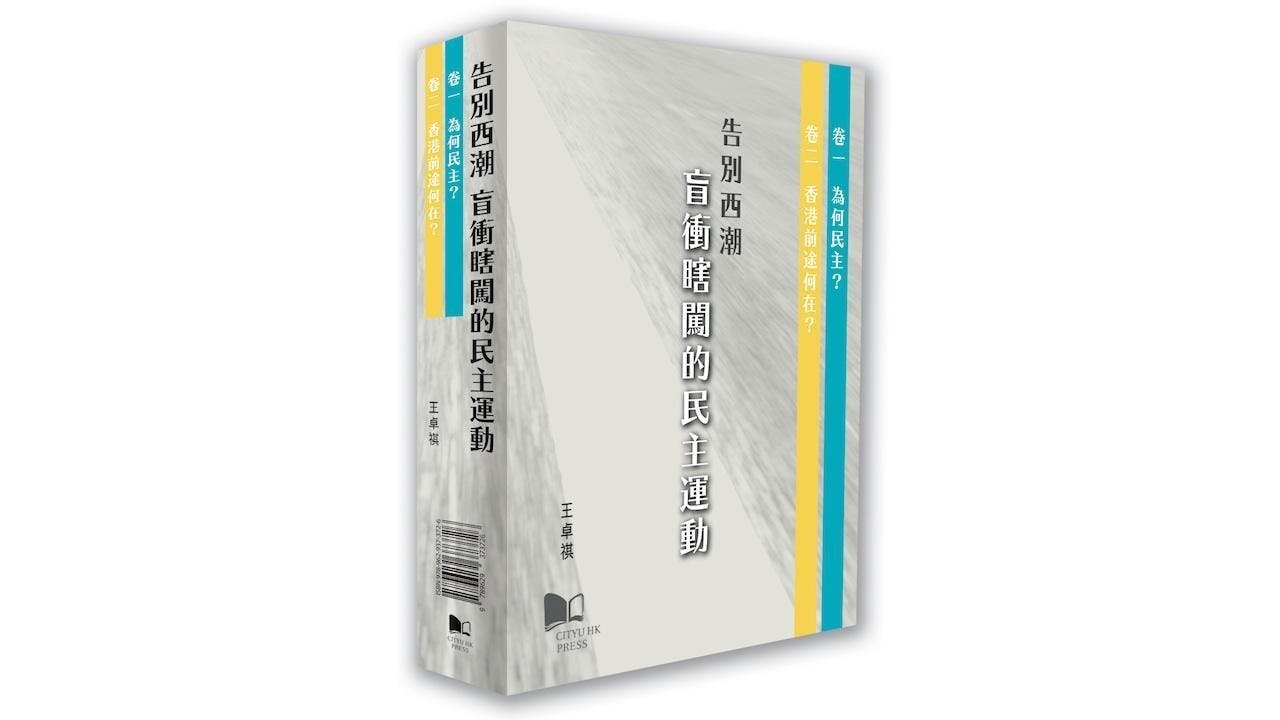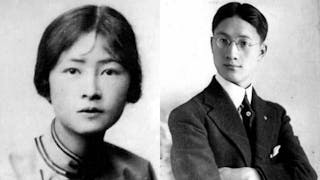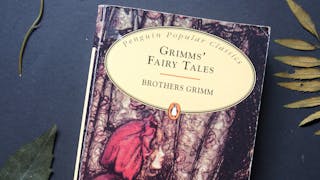過去一段不短的日子,筆者有機會細覽有關民主的英語文獻,主要是西方學者所寫,以及觀察21世紀以來,例如阿拉伯之春的第四波民主化,以至鄰近國家新加坡及菲律賓等的民主化經驗,再作出思考。本文目的是在概念上弄清民主是怎樣的政治制度,它與政治認受性及良治(good governance)有沒有必然關係,然後再看西方民主制度面對的困境。
筆者任職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簡稱中策組)全職顧問,但並未曾參與政改具體工作,讀者不可當本文是官方立場,但筆者希望透過討論,探索民主的功能及面對問題。
西方民主實際是選票民主
根據加拿大政治學者Daniel Bell的講法,民主的最低定義是國家的重要決策者由自由、公平具競爭性的選舉方式產生。美國政治學權威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認為這種選舉要具備某種程度的言論、結社及新聞自由的條件,才能讓反對派候選人免於被報復的情況下對當權者作出批評,公平選舉才有可能出現。因此,西方不少學者把俄羅斯、新加坡、馬來西亞列為非自由的民主政體。更重要的民主政治元素是政府輪替,以顯彰公民有權用選票決定政治領袖的命運。
就算是新加坡被西方傳媒及學者稱為非自由的民主制度,但她仍然有定期選舉,執政黨要透過選舉得到執政權。舉例說,2001年至2011年三次大選,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得票分別由2001年5%,下跌至2006年66%及2011年60%。若人民行動黨繼續這種跌勢,可能再過兩屆大選便有機會被反對黨奪取政權。這種以在選舉投票箱的「多數決」制度可稱之為選票民主,因為最關鍵是選民用選票決定誰人/政黨執政。筆者不敢奪人之美,這個對西方民主制度的再界定原創於中策組前首席顧問邵善波的想法,筆者只是借用。
在文獻回顧期間,筆者有點驚訝,早於上世紀70年代,西方學者如諾貝爾獎得主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已有專論,指出這種多數人意願(majority will)的選票民主制度的問題,尤其是少數人如何騎劫整體社會利益。不過,海耶克亦指出,西方的代議政制民主,值得不少人甘冒生命危險爭取,就是因為它是人民對抗專權者的最後武器。他比喻選票民主代表的多數人意願好像是種防疫針,人民並不留意到它的功效。

但若我們要減低選票民主的問題,一定要有系統性的制度配套措施,遏止以保障個人及少數人權利為名,實際是製造民主失範。例如少數極端政客用議會的否決點(veto points)阻礙政府有效施政。美國奧巴馬聯邦政府於2013年10月1–16日的政府關門(據悉是歷史上第18次,並惹來美國是否已經是一個失敗國家﹝failed state﹞的議論)便是激進的茶黨騎劫共和黨權鬥的例證。當然,我們亦留意到美國民主黨當時在他們控制的參議院更改了1975年以來的「拉布」(filibuster)規則。
選票民主與認受性及良治沒有必然關係有些人認為有選票民主,政府便有認受性。從概念及歷史發展經驗來論證,結果發現這是沒有根據的。西方政治學的早期研究(如Seymour M. Lipset、Juan Linz)便是探索民主政府為何崩潰(breakdown)的問題。例如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大批民選政府倒台,回復專權以至獨裁政權。這個情況在拉美尤其嚴重。甚至2011年初始於北非突尼西亞的所謂第四波民主化的阿拉伯之春,埃及的第一次以選票產生的伊斯蘭兄弟會的民選政府,不及一年已被群眾上街抗議,並以軍事政變垮台。
所謂選票民主便有認受性,是代議政制的邏輯缺陷──選舉程序並沒有帶來管治成效的必然性及認受性。而歷史上,中國及外國的皇權從來都有認受性。
除非被統治者認為現存的政權無可救藥,寧冒包括殺頭、坐牢的風險,亦不接受統治政權的命令,當政者才有認受性危機。當然,這種講法是建基於一個信念或判斷,即認為政府已經沒有認受性。而認受性的界定是:即使政府有什麼缺陷或過失,它還是好過其他可能產生的選擇,因此它的指令得到遵守。若從這一個立見分曉的試金石看所謂認受性危機便會清楚不過,例如它的法律是否得到遵守及有沒有人進行推翻政府的行為,而這些活動的廣泛性都是證據。而最後是政府有沒有決心及能力用武力阻止反政府的行為。
這是政治學ABC。很多情況是政府施政有困難,如某一重要法案被議會否決,便被渲染為認受性危機;這是政治論述,並不一定符合現實。
至於選票民主與良治更沒有必然性。亨廷頓早於1968年的專書,開章便指出民主政府與獨裁政府最明顯的分別不在政府方式,而是政府的管治素質,例如它們的領袖與公民能否有對公共利益的相同願景,以及相同的政治傳統及原則。即是說,政治制度最重要是建立共識。而每個政體有不同傳統及共識,並沒有所謂普及真理。一些研究東亞的政治學者,包括美國史丹福大學的Larry Diamond便發現一個思念威權主義(nostalgia of authoritarianism)的現象。香港人熟悉的菲律賓便是一例。自從馬尼拉的中產階級於1986年推翻馬可斯獨裁政權後,實現選票民主,即公民可以透過投票箱(voting booth)選舉總統,政府的管治毫無寸進。曾幾何時,菲律賓與新加坡,以至香港有相差不多的生活水準,但今天的菲律賓卻要輸出具有大專教育學歷的傭工。有報道指出曾經對推翻馬可斯政權十分自豪的馬尼拉中產階級,今天的反思是菲律賓民主是太多了!

民主與良治沒有必然關係的例子不勝枚舉,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選票民主的邏輯是難於克服推行要選民克制及犧牲短期利益的政策。當然,印度是選票民主大國,就算沒有全球化,亦沒有什麼良治的寶貴經驗!
從理論來分析,選票政治不一定導致良治的根由是清楚不過。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講法是民主比皇權或貴族政治,從功能主義角度來看都要低下,原因是它傾向減弱有管治能力專家的份量,而選出那些能夠引導未必能分辨複雜議題的民眾但訴諸公義的專家(今天我們稱之為政客)。從個人權利角度看,選票民主當然能夠使政府決策傾向民意一方,但若它作出不受民眾歡迎的決策,而其效果未必能夠在下次投票選舉代議士之前生效,政治領袖下台的機會十分大。因此,所謂民主政治或選票民主改善政府認受性及達至良治並沒有什麼必然性。
西方選票民主面對的困境
香港部分人熱中於所謂普選的選票民主,但稍為覽閱西方政治學文獻,便會知道代議政制的選票民主實際毛病叢生。早於1975年,歐洲、美國及日本政治學者,包括亨廷頓在內,組成一個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寫了份名為《民主的危機》的報告。其中特別指出民主失範的問題。該報告認為原因是傳統制度,包括教會、學校、政黨及政府等權威的衰落,而另一方面是公民缺乏責任感現象冒起。這兩者加上一個愈來愈存有偏見的傳媒,更剝奪負責任政府的時間,以及社會的容忍及信任所賦予的空間,容許它做創新及負責任的工作。這些西方主流學者的警告,可以歸結為一個可實證的財政現象,就是顯示超載政府(overloaded government)的國家債務危機。
美國今天的財政懸崖便是一例,由上世紀80年代30–40%的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在2012 年末第一次增加至104%的GDP。但美國還可以提高借貸上限,因為還有強美元的國際金融體系支撐。但過去所謂「歐豬」五國歐債危機的衰敗格局便可實證選票民主的困局。
美國學者Charles A. Kupchan早前在美國《外交事務》期刊(Foreign Affairs)特別指出民主的抑鬱症(malaise of democracy),其斷症是全球化弱化西方政府應對選民訴求的能力。而背後是國際權力構造的改變。他指出,全球經濟重心已由西方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而在這個過程中深受其苦的中產階級及一般選民正需要政府的協助,但後者卻無能為力。Kupchan的分析有點偏差,西方的超載政府、不負責任選民及存有偏見傳媒的問題,在地大物博、人口稀少的加拿大及澳洲較為輕微,而西歐的德國及北歐的社會主義福利國家亦並未出現;當然這是相對而言。筆者初步的看法是,德國及北歐國家有較多負責任的公民,它們的文化傳統重視工作倫理(國際競爭力都在前列)及社會責任(稅收最重,願意把較多的社會資源再分配以達到社會團結)。相反,以美國為例的自由經濟、較低政府介入社會分配的國家,社會分化及管治失效是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貧富差距擴大及生活水平停滯不前的背景下發生。
結論
本文論證以選票主導社會發展的民主制度,並不是靈丹妙藥,可以解决社會問題及政治紛爭。如果我們細心分析,尤其參考國際經驗及發展趨勢,選票民主可能是短暫的興奮劑,服過之後,問題還是繼續,還可能有更多後遺症!
本文只是希望打開一個討論民主制度設計及功能的窗口,吸收歷史教訓及借鑑國際經驗,在香港邁向民主的過程中,享有後發優勢以避免選票民主的問題。
本文原載於2013年12月17日《明報》
新書簡介
書名:告別西潮──盲衝瞎闖的民主運動
作者:王卓祺
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