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熄》之夢醒時分
閻連科的長篇小說《日熄》於2015年由台灣麥田出版社出版, 2016年獲得第六屆「紅樓夢獎」首獎。小說以伏牛山脈的皋田小鎮為背景,敘述者是一位叫李念念的14歲智障男孩,時間為某年農曆6月6日的短短一夜。故事講述了在那一夜全鎮的人紛紛夢遊,在夢境裏燒殺搶掠,慾望橫流,無惡不作,全鎮陷入無序狀態。只有開冥貨店的念念一家時夢時醒,念念他爹李天保一直在試圖喚醒其他夢遊的人。到了該天亮的時候,太陽沒有出來,夢遊的人也就一直醒不過來。最後李天保用一種奇特的方式,以自己的血肉之軀製造了一個太陽,終於結束了這場噩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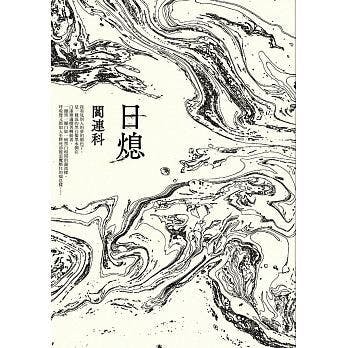
作者的不少作品,例如《日光流年》、《受活》、《丁莊夢》、《四書》、《炸裂志》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作文本實驗,告別了五四以來的「茅盾式」現實主義,在形式、內容上都掺進了非現實甚或荒誕的元素。(註1)《日熄》的故事更是完全建構於一場集體夢遊之中,顛覆了傳統意義上的現實。首先,小說的第一人稱敘述者念念智力不健全,人稱「傻娃」,從他嘴裏講出來的故事可靠程度令人懷疑。另外,書的結構也疑幻疑真,為故事抹上了一筆不確切的色彩 。除了前言和尾聲無時間說明以外,全書11卷均以時間標示,時間段先用五更劃分,然後在每一更裏再細分出從幾點幾分到幾點幾分發生的事情,具體時間以24小時制標出。傳統上的五更應從晚上19時到第二天清晨五時,每兩小時為一更。換言之,第一更應該是19時至21時,但小說中的第一更卻從17時開始。
此外,小說五更結束的時間向後推延了15分鐘,至5時15分才結束。之後作者又加了一卷「更後」,從五時十分開始,與他的五更結束時間有五分鐘的重疊 。最有趣的是時間到了六時,正常情況下應該是接近天亮的時候,作者又加了一卷「無更」,時間在這裏停頓了。卷十「無更」與卷11「升騰」的前三節整整40頁,時間都停留在六時,白天拒絕到臨,黎明前的黑暗無限延續:「——好像白天死了不會再亮了。⋯⋯這一日日頭死了時間死了白天跟着也死去了。」(註2) 雖然時間分段精確到以分鐘計算,但是上述的混亂卻宛如在精確中屢屢出現誤差,頓時使讀者對這個精確度也產生了懷疑。 作者一方面同時使用古代的更與現代的24小時計時方式,更把在夢遊裏打砸搶行為比擬成古代的農民起義,卻又故意犯下時代錯誤,把明末的李自成和清朝的太平天國混為一談,並讓這些暴民頭纏黃布,誘導讀者聯想到時代更為久遠的東漢末年的黃巾軍。如此一來,貌似精準的故事時間實際上給讀者造成了一種模糊錯亂的時空感。另一方面,如此改變五更的起訖時間,等於人為地延長了黑夜,增加了故事的不真實感與幽暗感。

小說殘酷陰暗風
20世紀80年代崛起的先鋒作家有一個特別的現象,就是作品中競相出現各種殘酷、陰暗、骯髒的極端描寫,例如莫言《紅高粱家族》裏羅漢大爺被日本人活剝人皮,余華《一九八六年》裏在文革中失蹤的中學歷史教師再次出現後對自己施行各種古代刑法,蘇童《舒農》裏在河面上漂浮的避孕套與燒焦的貓屍,劉恆《蒼河白日夢》裏曹家老爺為養生延壽吃女人的經血,最後發展到吃糞便等等,不一而足,以至於海外文學批評屆出現了「殘酷現實主義」、「骯髒現實主義」的説法。這種寫法無疑是對革命年代「高大全」式光輝文學的逆動,對於當時習慣了玫瑰園假象的讀者來說,此種前所未有的閱讀經驗極具衝擊力,挑戰着他們心理承受能力的底線。類似的寫作手法在閻連科今天的作品裏依然存在,甚至有過之並荒誕化了。例如,2013年出版的《炸裂志》裏,村長孔明亮用金錢獎勵村民向仇家朱慶方吐痰:「咳痰呸吐的聲音在黃昏如是雷陣雨,轉眼間,朱慶方的頭上、臉上、身上就滿是青白灰黃的痰液了。肩頭上掛的痰液如簾狀瀑布的水,直到所有村人的喉嚨都乾了,再也吐不出一滴痰液來,朱慶方還蹲在痰液中間一動不動着。像用痰液凝塑的一尊像。⋯⋯朱慶方被痰液嗆死了。」(註3)
如果説《炸裂志》裏的痰液雕像已經超出了讀者的想像力,在感官上引起極大的不安,《日熄》裏出現的屍油則更是達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李天保開火葬場的妻哥把焚燒屍體時產生的人油收集起來,以300元一桶的價格賣出去:「賣洛陽。賣鄭州。所有的城市工廠都要這種油,做肥皂、做橡膠、提煉潤滑油。這是天好地好的工業油。說不定當作人的食用也是上好哪。」(註4) 後來李天保用同樣價錢把屍油買了下來,但沒有說明作何用途。這使讀者聯想起若干年前在中國社會上就曾經有過類似的傳聞,説市面上某牌子的方便面,還有某種香水都使用了屍油,後來此一傳言已經證實為謠言。專家指出,焚化時油脂會迅速燃盡,不可能收集儲存。(註5) 閻連科本人也知道這個常識。(註6) 然而,他在故事裏不但寫了如何把屍油收集裝桶,如何把一桶一桶的屍油運往山洞裏藏起來,結尾處更是異想天開地把所有屍油推出來倒進東方山頂的天坑裏,試圖點燃屍油製造太陽:「大麥場似的天坑裏,油有大腿深。也許能埋過大腿到了腰那兒。平整黏稠的油面發出黑光發出一片刺鼻的味。彎腰看時能從那油面上看見一片一片魚鱗似的光。⋯⋯——可以點火啦日頭就要出來啦。」(註7)
大概在不少讀者的認知經驗裏, 會有「萬人坑」的記憶——多指日軍侵華大屠殺後就地處理屍體的場地,例如南京大屠殺萬人坑遺址。數以萬計的屍骨混埋在同一個大坑裏,無疑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實存在,而閻連科的「人油坑」則完全在讀者的認知經驗範圍以外,是作者豐富想像力的結果, 也是全書荒誕的頂峰所在,「毛骨悚然」幾個字已經不夠用了。大腿深甚至齊腰深的人油湖,豈是萬具屍骨可以煉成的?固有經驗會使讀者把「平整」、「一片一片魚鱗似的光」這樣的字眼與美麗的湖水聯繫起來,然而這卻是一片黏稠的、發出黑光和刺鼻味道的人油湖。文字帶來的觸覺、視覺以及嗅覺效果,遠非文字可以形容。最後,與本書作者同名而身分同為作家的小說人物閻連科提醒李天保,點燃油坑只能製造出一片光亮的效果,並不足以亂太陽之真。只有想辦法讓油燒成一個球形才像太陽。於是,李天保決定把自己浸透了人油的肉身當成燭芯,站在油坑高處引火燒身,遠處的人們看見的就是太陽一樣的火球了。最後,天亮了,太陽出來了,皋田鎮醒了,一場荒誕的夢遊就此結束,生活回復正常。
閻連科之神實主義
閻連科把此種具有卡夫卡特色的荒誕風格命名為「神實主義」。他認為,神實主義 是「在創作中摒棄固有真實生活的表面邏輯關係,去探求一種『不存在』的真實,看不見的真實,被真實掩蓋的真實。⋯⋯它與現實的聯繫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於人的靈魂、精神(現實的精神和實物內部關係與人的聯繫)和創作者在現實基礎上的特殊臆思。⋯⋯神實主義決不排斥現實主義,但它努力創造現實和超越現實。⋯⋯它尋求內真實,仰仗內因果,以此抵達人、社會和世界的內部去書寫真實、創造真實。」(註8) 可以想像,如今的中國社會,已然不是傳統的現實主義手法足以表現的了,因為「今天中國的現實樣貌,已經到了不簡單是一片柴草、莊稼和樓瓦的時候,它的複雜性、荒誕性前所未有。其豐富性,也前所未有。」(註9) 閻連科指出,神實主義「立足於本民族的文化土壤生根和成長。⋯⋯[於]現實而言,文學最終是它的附屬之物——什麼樣的現實,決定什麼樣的文學。」(註10)
他從早期的現實主義風格轉型到神實主義風格以來,作品的「複雜性、荒誕性、豐富性」恰恰與他眼中的中國現實相契合。文本互涉是閻連科作品裏常見的現象, 例如,「疾病」就是一個出現於諸多文本裏的命題。 如上所述,《日熄》裏的第一人稱敘述者念念是智障者。除了擔當「不可靠的敘述者」這一角色而增加故事的荒誕色彩以外,念念也是閻連科疾病敘述患者群裏的一員,而描寫夢遊症的《日熄》也和他的疾病三部曲(《日光流年》、《受活》、《丁莊夢》)一樣影射當今不健康甚至病態的社會。(註11) 他的「神實主義作品群」作為一個整體,有如挪威畫家愛德華.蒙克(Edvard Munch, 1863-1944)的著名畫作《吶喊》(The Scream),藝術家的主觀感覺投射出誇張扭曲的畫面,充滿了痛苦和焦慮。 或許可以說,閻連科作品裏的荒誕元素不是沒有現實基礎、空穴來風的, 而是在中國這麼一個特殊語境裏已經發生或者有可能發生的。也許是作者集社會荒誕之大成而在作品裏集中表現,也許是讀者從小說的精神荒誕推衍出生活中的事實荒誕。無論是由實而神或是由神而實,荒誕的「神」在在都指涉着可能的「實」,指涉着作家所理解的時代的「內真實」和「被真實掩蓋的真實」,或曰「深層真實」、「生命真實」和「靈魂真實」。(註12)
寓言式小說具現實烙印
《日熄》得獎後閻連科接受採訪時説:「我們這一代作家的寫作總是無法擺脫宏大敘事和歷史現實的背景。在《日熄》裏我在嘗試做一些改變,這部作品裏既沒有宏大的歷史,也沒有我們今天每個人都看到的,正在發生的現實。」(註13) 中國文學自古以來都有着反映現實、教化社會的傳統,五四時期以魯迅為代表的主流嚴肅文學更是如此,鮮見純粹為寫作而寫作的作品。建國以來17年乃至整個文革時期的文學完全淪為政治工具。文革結束後,不管是曇花一現的傷痕文學、改革文學,還是影響深遠的尋根文學,都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像閻連科這樣具有社會良心和歷史使命感,高度關注民間疾苦的作家,作品完全超越歷史和現實,殊非易事。熟知中國歷史和現狀的中外讀者和批評家,都很容易不自覺地把虛構的故事與現實聯繫起來。
儘管閻連科努力地把《日熄》寫得既沒有歷史也沒有現實,其出版者還是把這場夢遊具象到中國的社會現實:「閻連科以獨特的文學語言,講述一個人類因夢遊而失序的故事,藉此暗諷大躍進的中國,人們正集體沈浸在資本主義社會富裕美好的前景幻夢中,致使集體迷失在無盡慾望的夢遊中。這是針對當代中國發展現狀最無奈的憂思,也是最痛切的關懷。」(註14) 再如,《受活》、《炸裂志》以及《日熄》的翻譯者、杜克大學副教授羅鵬 (Carlos Rojas)也把閻連科的作品與魯迅相提並論,從《日熄》的夢遊聯想到魯迅的鐵屋裏昏睡的人們,再以魯迅「吃人」的母題類比閻連科《丁莊夢》、《日光流年》、《日熄》裏農民賣血、賣皮、賣屍油的行為。(註15) 看來,正如一提到魔幻現實主義,人們就會想到拉美文學一樣,閻連科神實主義實驗的寓言式小說,也難免帶着具有中國特色的歷史和現實烙印。

黑暗中尚存光明和救贖的可能
羅鵬指出:「複雜的情況是,這種同相嗜食/同相商品化現象——《日熄》中的『人油』或『屍油』。既是一種商品,又是拯救人類『日出』的必需。這就是閻連科與魯迅的不同,是閻連科的複雜,更是今天中國和人類的複雜。」(註16) 換言之,在小說裏,「人油」這種商品同時成為了毀滅與拯救人類靈魂的雙重隱喻。 閻連科的另一部小說《受活》裏,也有類似的矛盾隱喻:「受活莊最初被用作病態社會的隱喻,但後來村子成功『退社』,回到了以前的烏托邦狀態,卻又成了希望的象徵。受活莊人最初是柳鷹雀荒謬計劃的受害者,最後卻成了這個曾被村人當作神明的人的救星。」(註17) 或許羅鵬所言的複雜,或者閻連科所界定的神與實,都體現在這種矛盾統一體上,正如閻連科的不少作品,雖然通篇極盡晦暗負面之能事,但最後尚存光明和救贖的可能。《受活》裏的受活莊最終恢復其世外桃源的本色;《丁莊夢》裏的丁莊因大規模爆發愛滋病而死人無數村子盡毀,最後爺爺親手殺了自己作惡多端的兒子——血頭丁輝,看見了女媧重新造人,看見了新世界誕生的希望。
到了《日熄》,李天保不斷地要想喚醒夢遊的人,最後想出燃燒屍油的方法,並不惜犧牲自身,完成了救贖和自我救贖:早年政府推行火葬政策時,遭到村民強烈反對,不少人依然偷偷地土葬自家逝去的親人。李天保對開辦火葬場的妻哥告密,把已經入土為安的死者挖出來火化,從中賺取告密費。自焚之前他想到的是,他燒死自己來喚醒別人,他們家從此就再也不欠任何人的賬了。同時他念念不忘的是讓角色閻連科在書裏把他「寫成一個好人」。(註18) 點燃自己而為早年告密的劣行贖罪,李天保完成了自我救贖的同時也救贖了皋田鎮。把自己點燃的一刻,就是他完成救贖行動、決心要做好人的時候,就在那一刻,他先於其他人清醒了:「隨着那掙的逃的火團兒,傳來的是爹那撕疼死痛轉着身子的嘶喊着。——我醒啦。——我醒啦。」(註19) 角色李天保央求角色閻連科把他寫進書裏,寫成一個好人。然而,故事的結尾,角色閻連科消失了,書並沒有寫出來。「好人」在故事裏懸空了,變成了作家閻連科的一廂情願。
《丁莊夢》的爺爺一直在瘟疫中充當照顧病人的好人;《受活》的茅枝婆是死後連上百條殘疾狗都來送葬的好人,而政治瘋子縣長柳鷹雀也有可能變回好人;《炸裂志》不貪圖名利不享受特權的孔明輝是孔家唯一的好人;《日熄》的李天保要用實際行動贖罪成為好人⋯⋯也許,《日熄》裏角色閻連科寫不出作品的焦慮正是現實裏作家閻連科尋找「好人」的焦慮。在閻連科的神實世界裏,只有「好人」才是污濁現實唯一的精神救贖。李天保把他「寫成一個好人」的要求具有兩層意義:書寫與道德,而這個要求最終沒有得到落實。角色閻連科在從這個世界消失之前,把自己寫過的書堆在李天保的遺像前點火焚燒,彷彿在祭典這個「好人」,從此以後,人和書都全無蹤跡。也就是説,以往書寫過的好人全都被勾銷了。這是否在暗示,書寫的救贖、道德的救贖,都只能在荒誕中存在?
註1. 孫郁在其〈從《受活》到《日熄》—— 再談閻連科的神實主義〉一文中屢次以茅盾式的現實主義書寫方法對照閻連科的「神實主義」創作。此文見《當代作家評論》,2017年第2期,頁5-11。
註2. 閻連科:《日熄》(台北:麥田出版,2015年),頁254。
註3. 閻連科:《炸裂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年),頁25。
註4. 閻連科:《日熄》,頁72。
註5. 〈東莞殯儀館:屍油流入食用油市場?這不科學!〉,《前沿科技》,2015年4月7日。下載自大粵網,2018年5月29日。網址:http://gd.qq.com/a/20150407/017386.htm。
註6. 筆者2018年3月與閻連科在美國洛杉磯見面時,閻連科向筆者證實了屍油不可能儲存的情況。
註7. 閻連科:《日熄》,頁297-298。
註8. 閻連科:《發現小說》(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81-182。
註9. 同上,頁183。
註10. 同上,頁182。
註11. 參見拙作〈癌症、殘疾和愛滋敘事:論閻連科的疾病三部曲〉,汪寶榮譯,《當代作家評論》,2017年第二期,頁12-23。
註12. 閻連科:《發現小說》,頁184。
註13. 羅皓菱:〈閻連科《日熄》獲第六屆「紅樓夢獎」首獎〉,《華文好書》,2016年7月19日。下載自騰訊文化網,2018年5月29日。網址:http://cul.qq.com/a/20160719/037115.htm。
註14. 閻連科:《日熄》,封底。
註15. 羅鵬 : 〈《日熄》:魯迅與喬伊絲〉,《日熄》序論,頁3。
註16. 同上,頁6。
註17. 見拙文〈癌症、殘疾和愛滋敘事:論閻連科的疾病三部曲〉,頁19。
註18. 閻連科:《日熄》,頁304。
註19. 同上,頁304-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