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張炳良教授新著《疫變:透視新冠病毒下之危機管治》通過危機管治的⻆度,探討新冠疫情如何演變成為全球化危機,並就一些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抗疫策略和表現作出比較。然後,針對香港在過去3年抗疫表現之得失,展示疫情如何考驗政府的治理能量、社會信任度和領導力。最後歸納一些國際性的重要經驗與教訓,以有助再理解抗疫應變之道及箇中的關鍵因素。本社節錄序言如下,以饗讀者。
新冠狀肺炎病毒可說是21世紀以來至嚴重、堪稱災難性的大流行病疫。本書定稿於2022年8月底,當時全球確診病例按各國匯報統計近6.03億宗,死亡個案逾649萬宗。上述數字或屬低估。世界衞生組織(世衛組織)曾於2022年5月初宣布,按其最新估計,單是2020和2021兩年內新冠已導致近1500萬人額外死亡,比各國官方報告總數的540萬人多出接近兩倍,當時《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模型更估測高達1800萬人。世衛組織的專家表示,大部分死者死於冠毒,但也有其他病患者(如心臟病)因醫護系統受新冠疫情影響致未及時獲救治而去世。
危機已成新常態
新冠病毒帶來的不只是一場公共衛生(公衛)安全上的災難,更是一系列對經濟商貿、就業民生、教育文化、社會生活、公共行政、公共服務、國際往來,以至民情和政治上的連鎖衝擊,打擊面之大,前所未見;而且疫情經歷幾波起伏、病毒變種持續,傳染擴散仍然不止,未見終極。
從公共管治的角度言,「危機」已成為新常態。以世界扁平論知名的美國普利茲新聞獎三屆獲獎者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於2020年初新冠初發時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聲言,世界從此不再一樣,大疫標誌歷史的新轉捩點,構成「新冠前」(Before Coronavirus, BC)vs「新冠後」(After Coronavirus, AC)之別。還有一點諷刺性的是,全球化既大大方便了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也促成像新冠般病毒的全球性快速散播,讓危機也全球化。21世紀的大瘟疫跟以前的已不再一樣。
世界衞生組織於2022年5月初最新估計數顯示,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間,與新冠狀肺炎病毒大流行直接或間接相關的全部死亡(稱為「超額死亡」)約為1490萬例(範圍為1330萬例至1660萬例)。
當然,不同國家和地區處理疫情的策略和方法,既受其本國本土「國情」和制度傳統因素所影響,也吸收了他國經驗,如「封城」之舉由早期的不可能之想像,後來成為各國紛紛採用的防疫措施,乃一顯例。「封城」(lockdown)是一般統稱,不一定是全個城市,也包括對指定大小地區的全面或局部性的封鎖禁足,以及帶有封城特色的嚴厲限制措施包括戒嚴,各地正式名堂不一。疫情不單考驗各國各地的防疫抗疫手段成效,更是對其危機處理、管治思維、政府能量和政治領導能力的一次大考。
公衛及安全危機,往往暴露治理缺陷、制度盲點、低估風險、後知後覺,易招重大民怨,造成嚴重的政治後果。人們記憶猶新,2003年香港SARS(「沙士」)病疫加上當時經濟衰退及反23條立法之群情,造成併發式的政治風暴,其後行政長官董建華於2005年3月以「腳痛」為由辭職。
「沙士」(中國內地稱「非典型肺炎」,簡稱「非典」)也令時任國家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兩人問責下台。2005年美國卡特里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2009年台灣莫拉克風災(又稱「八八水災」),以及2019至2020年澳洲延續近半年的叢林大火(「黑色夏天」災難),皆成為當地的重要政治轉捩點。所以,抗疫之戰,對危機管治之道,具有莫大的啟示及結構性和深層性的意義,對社會生活和政治變化影響深遠,此乃本書探究的主軸。
2021年一本有關新冠大流行的專書便以「餘震」(Aftershocks)為名,去形容新冠對政治和國際秩序的衝擊。至於新冠病毒的來源,仍有待傳染病學及微生物學專家認真研究,它的爆發或許偶然,但人類社會爆發病疫,已屬必然,且隨着交通發達、邊界開放、人流物流頻繁,全球化也帶來任何傳染病毒迅速跨境擴散,無一國家或城市可以真正「免疫」。新冠病毒因屬無症狀、變種快,所以傳播更易更廣。對新冠疫變的認知和解構,宜立足於起碼三個基本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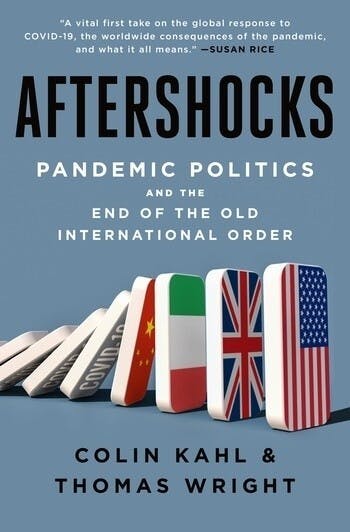
對新冠疫變的三個基本點認知
第一個基本點是,人類社會已進入「風險社會」狀態,並應以此為常態。上世紀自1979年3月美國發生三里島核洩漏事故(Three Mile Island accident)及1986年4月前蘇聯切爾諾貝爾(Chernobyl)(今位於烏克蘭)發生核電廠爆炸事故,世人開始擔心核科技帶來的重大風險;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及海嘯不僅是該國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天災,而且引發福島核電廠洩漏災害,是切爾諾貝爾核災以來全球最嚴重的核洩漏事故。
早於上世紀80年代後期,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已著書警告「風險社會」(risk society)年代的到臨,指出風險社會的特點,是除了面對天然災害(包括氣象災害和病疫)外,還須應對種種人為風險和災難(human made, manufactured)。源自天然的風險,也可因人類社會的一些作為或不作為,或介入不當,而加劇成為更嚴重的綜合性災難。
第二個基本點是,伴隨人類社會的全球化和高科技化,風險也藉全球化及高科技而擴散,人類的成功諷刺地助長了病毒的進化。21世紀至今已經歷多次全球性危機(除大病疫外,也包括氣候變化、金融風暴),以及高科技(High-tech)風險(如網絡詐騙、虛擬貨幣、網絡恐怖等)。這些新時代的風險,與人類在高科技下全球貫通及進入網絡世界的新生活形態息息相關,風險之源似已植入人類的社會和行為基因,變成「進步」與「風險」並存共生、驅之不去,唯有視風險為新常態,需不斷提高安全意識,做好制度性和行為性的風險管理。
第三個基本點是,對全球化及其政治經濟含義要加深了解。21世紀經常被稱為全球一體化的世紀。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論述,無論是學理性分析,還是民間通俗性表述,均蘊含兩個層次,一是全球性,二是一體化。在互聯網資訊普及和國際出行快速便捷的推動下,全球性意指傳統的國土地域邊界已被打破,世界各地朝向單一地球村的大同邁進,正如前述佛里曼2005年暢銷書所形容,「世界已經扁平」(The world is flat)。全球化的政治經濟學和文化含義,見於一體化,意指各國各地皆高度融入同一「全球」(或曰「普世」)的政治秩序和經濟金融秩序,以及支撐如此秩序的國際組織和文化價值體系,而這些在二戰後逐步建立和鞏固的秩序體系乃以西方文明為基礎,主要受西方世界所主導和定義。這就是所謂「趨同」論(convergence)。
但現實歷史的世界不見得切合如此簡單甚或理想化的趨同表述。二戰後40年的冷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與以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世界,持續進行意識形態鬥爭、政治對壘及外交軍事衝突。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及其東歐附庸國體系(即「華沙公約」集團,相對於美國及西歐的「北大西洋公約」即北約集團)瓦解,美西有宣稱「歷史終結」,認定全球從此邁向自由民主的普世制度,世界秩序也以當時盛行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去重塑,被稱為「華盛頓共識」。
所謂「規則為本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其規則和背後的價值觀乃美西自二戰後建構的主流意識形態之伸延,批判者視作文化征服。不過,也存在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之衝突」批判論述,認為宗教戰爭和意識形態對壘之後,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已冒起成為爭鬥主線,2001年「911」恐襲成為明證,乃西方與伊斯蘭衝突全球白熱化的標誌。

全球化論述的樂觀已一掃而空
從歷史發展角度去看,在20和21世紀轉角的全球化概念,與19世紀以來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概念,其實一脈相承,兩者皆建基於以視為較優越的西方現代文明,去一統被視為較落後的東方和他地文明。19世紀末日本的明治維新,其中一個改革口號便是「脫亞入歐」,而中國反封建革命也曾出現「全盤西化」的主張。科學與民主,大抵上代表了20世紀西方文明所代表的現代化之路的物質文明和制度文明。今天,全球一體化也同樣標榜以美西發展經驗構建的經濟秩序和政治制度。
若說上世紀90年代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的崩解,以及隨後1998至1999年亞洲金融風暴帶來的「東亞經濟奇蹟」的挫折,乃美西主導的全球一體化步上巔峰的里程碑,那麼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海嘯的爆發,乃打破美西新自由主義經濟神話的轉折點;之後西方經濟不振愈顯,中國以至亞洲(東亞、東盟和印度)經濟崛起,中國一躍而成可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與美國合稱G2),從此改寫國際地緣政治。
一方面,西方國家經濟放緩、生產日益依賴中國、亞洲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供應鏈,致內部社會和階級矛盾惡化、反全球化浪潮澎湃,極右排外的民粹主義意識枱頭。另一方面,中國拒絕接受美國主導的全球化,且認為已找到符合自己國情、讓國家富強起來的另類發展模式(有稱之為中國模式及「北京共識」,對發展中及低發展國家尤具吸引力),並透過「一帶一路」及亞洲基建投資銀行等平台向外展示其新興力量,震撼西方世界。受此衝擊下,美西國家在國際層面愈把矛頭指向中國,視其經濟和科技崛起為衝擊西方文明及西方主導之國際秩序的重大威脅。
至此,全球化前期論述的樂觀已一掃而空。政治衝突、經濟矛盾波動漸成常態,世界雖是扁平卻不再和平共處。2022年2月俄羅斯進軍烏克蘭,更使地緣政治進一步複雜化和對峙化,美國指揮的北約集團,實質上跟意圖復興其歐亞(Eurasian)核心地位的「大俄羅斯主義」,在烏克蘭進行一場代理人戰爭。在上述的全球大環境下,新冠病疫的危機不止於一場傳染病學上的挑戰,也與本土本國及國際的政治經濟和管治上的根本矛盾和所衍生的危機交集一起,更涉及國際勢力和話語權的角力,令抗疫之戰彷彿構成地緣政治的另一場競賽,甚至改寫全球秩序。唯有從這樣一個較宏觀、全球性廣度和深度去探究,才能較全面掌握新冠病疫帶來之「疫變」,亦即本書命名背後的思考。新冠疫變,對風險的全球化和危機管理作為公共管治的新常態挑戰,帶來跟以往不一樣的體會。
人類社會並非首次受傳染病大流行(pandemic)所侵襲(上世紀初西班牙大流感時全球死去的人以千萬計),回應大疫之道不外乎作好計劃、具準備部署及開放信息溝通。從管理學角度言,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已成為企業管理和公共管理/管治的重要功能。雖然政府機關經歷如金融危機、病疫和自然災害後(海嘯、地震、叢林大火、風暴水災等),建立及不斷更新相關的危機處理機制及應對架構和流程。
不過,每一場危機都不會是過去危機的簡單重複,危機也似傳染病毒,不斷變異,因此公共管治的思維應以風險管理為常務,如何做到處危不驚、轉危為機,在在反映政府的政治思考和治理能量。每一宗重大事故和災害,都成為對領導力、統籌力、動員力和執行力的一次考驗。危機後的改革,必會涉及整個公共體制改革的各方面。從新冠疫變的正反經驗,也可得出一些改革的啟示。

《疫變》三大部分
本書除此引言及書末總結章外,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討新冠如何由未名病毒演變成為全球化危機、後新冠時代世界及生活如何不再一樣,遍及經濟、教育、社會生活、公共行政、公共服務、國際往來、政治及民情。至今幾波的疫情及病毒的變種,已構成疫發初期未有預見的多番轉折衝突。防疫抗疫的手段(非治療性及治療性的紓緩),各國各地或許大同小異,但其危機定義、應對力度和覆蓋面卻見有別,皆因本國本地的體制條件及政情民情等因素,令成效不一,短期和長期表現有異。病毒不斷變種,疫情、民情和政情也不斷在變。
差不多在所有國家和地區,抗疫都成為最大的政治,見諸於保生命與保生計、控疫與復元,以及科學與經濟之間的張力與爭持。在國際層面,新冠政治反映於不同形式的新冠國族主義和國際地緣政治張力,導致世衛組織陷於被動、區域或國際合作薄弱(如見於疫苗競爭)。在本書執筆時,更存在「清零 vs 共存」之爭,但兩者被置於對立實乃偽命題,真問題並非二取其一,而是如何在新冠病毒不斷變異及風土化下,致力切斷傳播鏈及減低重症、併發症、致死率及長者面對的風險。
第二部分就一些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抗疫策略和表現作出比較。在進行國際比較時,須先掌握各地疫變情況及究竟要比較什麼,因為涉及不同應對模式、不同醫學準則、不同資源條件、不同行政與行事方式,以至不同制度傳統和文化。在疫變過程中,抗疫防疫與民情政情交集,也受國際經驗交流、政策學習與政策轉移所影響。而且,疫情長期持續下也見抗疫之轉折反覆,以及不同手段的因勢組合。各國各地控疫防疫手段和政策工具,不外乎檢測監察與追蹤、隔離與社交距離、封區封城、疫苗與治療等。不過,病毒在異變,對策和論述因而也在變:從早階段的經濟配合醫療,逐步走向醫療配合經濟復原。
在至今已兩年多近三年的抗疫行動上,大抵上「領先者」皆從強力圍堵開始,顯著者包括中國內地、香港、台灣等地,以及日本、韓國、新加坡、越南、澳洲、新西蘭等國。它們之間的具體圍堵及所謂「清零」策略,在不同階段也見調整和轉變。新冠爆發之初北美及歐洲一些國家對新冠病毒未夠重視,這些「滯後者」一些早期曾迷信依賴群體免疫,當中以英國、美國及個別北歐國家為甚,後來也經歷不同階段的抗疫策略和手段的調整,但因前期輕視病毒疫變,以至無法根本地扭轉疫情。在兩極的應對態度和策略之間,也存在歐陸混合模式(如意大利、法國、德國、荷蘭等),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如俄羅斯、印度、南非,以至南美國家的各自應變取向。
第三部分針對香港在過去三年抗疫表現之跌宕。簡言概括之,其第一階段(2020年)集中於圍堵策略,表現突出;第二階段(2021年)曾見策略徘徊不穩,主要因為須平衡遏止傳播(動態清零)與維持經濟民生活動(逐步開放禁制)兩者在不同時期的需要和條件,但大抵上疫情受控,香港在國際比較表現上仍位於前列,不過經濟活力受壓日增;第三階段(2022年)首見疫情失控而呈淪陷邊緣,導致中央政府積極介入支援抗疫,市民質疑政府抗疫能力和策略的聲音此起彼落。
綜觀這三年,香港的應變能力在新冠抗疫上經歷重大考驗。初期香港受益於2003 年「沙士」的經驗和制度啟示,使 2020 年新冠爆發後,政府即時啟動應變機制發揮作用,整體醫護體制的表現突出,機構協調與公眾溝通也比「沙士」時大為改善,公共部門與企業和公民社會之間亦充分合作。但為何香港會由控疫戰勝走向2022年初第五波的困局?當中涉及戰略與戰術上的落差。抗疫之危機論述為何貧乏脆弱、持久戰為何欠缺準備,皆須予以認真檢討,並與香港的深層次和結構性矛盾有所關連。香港之例,展示疫情嚴重考驗政府的治理能量、社會信任度和領導力。
最後,在總結章歸納一些國際性的重要經驗與教訓,以有助再理解抗疫應變之道及箇中的關鍵因素。踏入2022 年,邁向與病毒共存(甚至視之為恆常化的風土病風險)似成為國際趨勢,不過共存策略下也存在被動vs進取、寬鬆vs嚴謹之別,而在少數仍維持清零導向的國家和地區,也漸見較動態化和靈活的抗疫認知。對於堅持「動態清零」原則的中國內地來說,2022年首、次季度Omicron肆虐下香港和上海等城市的慘痛經驗,也應帶來不能迴避的策略反思。初期成功的經驗和方法,不一定足以應付病毒變種後的疫情變化,「動態」便需因時制宜、緊貼形勢,這亦是今次疫變帶來的重要啟示。
原刊於《疫變:透視新冠病毒下之危機管治》第一章,本社獲中華書局授權節錄。
新書簡介:
書名:《疫變:透視新冠病毒下之危機管治》
作者:張炳良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22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