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缺乏透明度
回首往事,不少人都低估了疫情的危害!但是,在疫情還沒有開始蔓延時,如果做到資訊公開透明,如果吹哨人不被勸誡、警告、和懲罰,或許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歷史會改寫。許多在武漢不該發生的事一定不會發生,武漢的犧牲就不會這麼大,中國百姓的犧牲也就不會這麼大。
從中國最早處理新冠肺炎的不當做法,到世界衛生組織遲遲未對全球發出最高級別的警告,到歐美各國的遲緩應對行動,都和缺乏透明度有關聯。這次疫情如此迅猛擴散的第一責任人當然是武漢當局、湖北當局,他們對公眾隱瞞資訊甚至掩蓋真相,引發了民眾的不信任,國際社會不少人甚至懷疑中國的死亡率造假。中國最為受傷的就是因封鎖和隱瞞資訊,導致疫情的控制受到延誤,遭到國際社會詬病、排斥和指責。武漢封城之後,中國的經濟和民生受到重創的舉措和犧牲也因此大打折扣,對中國的負面影響其實剛剛浮現。
美國政客在中國疫情最嚴重的時刻,頗有隔岸觀火的看客心態。特朗普為了選舉,為了股市不下跌,不影響經濟,就是不願承認疫情遲早會衝擊美國。他本以為關閉了來往中國的航線,切斷了來自中國的人流就萬事大吉了。他還不讓郵輪上受感染的遊客在美國下船,就是要製造美國本土病毒感染者很低的假象。但這樣的做法和一切以穩定為首要的考慮有何區別呢?在疫情終於席捲美國之後,他也是不斷大事化小,盡量降低疫情所帶來的衝擊和影響,甚至在感染人數還在不斷攀升時竟然表示美國的經濟活動在復活節就可以恢復正常!所幸美國有獨立的媒體,在白宮可以直接和總統公開叫板,不讓政府傳播的不實消息當道。在白宮記者會上,美國媒體公開質疑特朗普的抗疫政策不當,當場質問總統為何不停地使用「中國病毒」這樣的歧視性字眼。
早在1月20日,當我確認這將是一場公共衛生災難時,我就第一時間在我的朋友圈裏轉發了管軼教授對疫情的「悲觀」看法。但他的科學分析在內地被視為聳人聽聞,有人甚至借他的「逃跑說」對他進行人身攻擊,但正是這樣客觀的資訊才有助於我們了解事實真相,了解這一公共衛生危機已經去到了多麼危險的境地!其實在發生類似新冠肺炎這樣的危機時,面對太多的不確定性,要阻止謠言,資訊的透明就顯得尤為重要。
除了刻意隱瞞資訊,還有虛假資訊氾濫。全球數百名科學家2月上旬出席日內瓦「世衛論壇」,討論新型冠肺炎疫情,學者就感歎他們不得不面對兩條戰線作戰,除了應付病毒大流行,還要應付虛假資訊大氾濫 ,而應對虛假資訊氾濫比抗疫本身還艱難。網上流傳最廣最快的往往就是聳人聽聞的假消息和渲染成見的看法,這些不實的資訊,有惡意造謠,有斷章取義,導致非理性的反應和恐慌,甚至製造混亂和分化。世衛顧問隆基尼(Ira Longini)和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曾提及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有可能感染新冠病毒,但網上的資訊都忽略了「如果傳播未加抑制」的假設,特意將最壞的可能性無限放大,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在任何一場公共危機發生的時候,政府是不可能靠遮罩資訊來阻止危機的蔓延。恰恰相反,這只會造成危機的進一步惡化。即便在上個世紀的蘇聯時代,對切爾諾貝利核洩露的隱瞞最終給人類帶來了一場世紀大災難,更何況我們已經身處社交媒體如此發達的時代!
面對全球疫情大流行,資訊披露和資訊對稱有助於我們了解不同地域,在不同的文化和背景下的不同應對策略和措施。不管是對疫情的判斷,還是應對疫情的方法,各國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相互之間不僅不該嘲笑,反而應該借鑒。我們因條件限制無法獲得全面的資訊,但至少可以換位思考,從他者的角度看問題,避免幸災樂禍的看客心理。

我們缺乏同理心
疫情爆發之後,各國不僅有不同的認知過程,而且在獲得相同的認知之後所採取的應對也並不相同。武漢封城的消息傳出之後,西方的反應也是兩極,有稱這樣的舉措是流行病專家的天堂,而這只有在威權國家才能實現,民主國家只能羡慕。但也有一些西方國家看到中國面臨的困境,在疫情剛剛爆發時,也帶有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甚至幸災樂禍看笑話的心態來看待中國的抗疫,還把病毒與中國的國民性和低劣文化相聯繫。
各國抗疫的做法離不開其體制、文化、歷史等因素。在中國,一聲令下,舉國體制立馬見效,整個國家有如一部機器,全力抗災,所有其他事情都要靠邊站,甚至做出犧牲,包括在「准戰爭」狀態下個體的權利和自由,其他病人可否受到正常的醫療救助,都不是最重要的考慮。事實證明,這樣的犧牲確實巨大,但這一抗疫歷史上未曾經歷過的舉措,一座上千萬人口的大城市被封城兩個月的戰略最終是奏效的。
中國的犧牲阻止了疫情蔓延,可歌可泣。即使如此,可圈可點之處也多如牛毛,野蠻作業的現象也並非個別。中國人不喜歡美國指手畫腳,那別的國家難道就喜歡中國這麼做?一些自媒體對別國狀況一知半解,充滿無知、偏見和輕蔑,非要說人家不會抄作業。看看東鄰日本,和韓國的做法也不同,連大面積的檢測也沒做,情況也不算太壞!日本的人口密度還超過中國!但日本人平時的生活和衛生習慣,你又了解多少?其實就是華人社會的香港、澳門、台灣、新加坡等地的處理方式都不同,當中新加坡的所謂「佛系」防疫措施相當成功讓不少人大跌眼鏡。
新加坡從「重災區」到「模範生」,表面上看去似乎選擇了「佛系」的抗疫策略,曾引來不少懷疑、甚至嘲笑。新加坡防疫成功是有原因的,其策略可以概括為:最快反應、最早防範、最有系統、最嚴懲罰、最少折騰、最缺恐慌。新加坡一度是僅次於中國病例第二高的國家,同時人口稠密,還是國際交通樞紐。但新加坡政府反應迅速且效率高,最早限制來自中國的人流,並實施了對不同人群的休假令和居家隔離令。「非典」之後建立起來的疫情警報系統立即派上用場。新加坡國家傳染病中心集先進的檢測、治療與實驗研究為一體,馬上研發並合作生產了快速病毒檢試劑,有健全的檢測體系,保證了疑似患者盡快得到治療,避免了疫情的傳播,加強了民眾的信心。新加坡缺乏口罩生產能力,不鼓勵大家戴口罩,但政府還是快速購買了500萬個口罩派發到每家每戶,安撫民眾。新加坡有充足的醫療資源,類似於中國的發熱門診就有873個,相當於北京發熱門診的11倍。我很早在朋友圈裏就轉發相關的資訊看好新加坡的做法,甚至比香港還成功,沒有發生香港排長隊爭口罩、搶廁紙的「奇觀」。但話說回來,香港的恐慌是基於香港曾在2003年「非典」(SARS)時曾遭重創的慘痛歷史,以及香港和內地每天有大量的人員來往這一事實。
韓國這次的抗疫模式在西方更是受到肯定,法國總統和瑞典首相等多國政要甚至致電韓國討教。但韓國對疫情的控制到底有何魅力?為何西方願意到韓國取經和複製韓國模式呢?韓國也曾面對與中國相同的困境,但兩國在大範圍發生疫情之後,採取了類似的抗疫戰略,新增病例曲線迅速被壓平。但西方在看韓國的經驗時,特別看重韓國沒有因疫情出現壓制言論和資訊受阻的現象,沒有因禁令影響民眾的行動和自由,國家的經濟更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韓國的經驗可以歸結為:早幹預、早準備、早檢測、早跟蹤、早隔離、早觀察。韓國的企業早就判斷病毒遲早會擴散到韓國,第一時間就研發出檢測試劑盒,獲得政府的緊急審批投放市場,檢測過程只需十分鐘,幾小時內可以出結果,準確率超過98%。韓國單日可檢測近2萬人,檢測率全球之冠,已有120多個國家爭相從韓國進口測試盒。韓國政府還迅速修訂法律,網站和手機都可以追蹤病發者,一旦有新病例,就可以獲得資訊和警報。
好的經驗當然可以抄,可以借鑒,但不必過分地顯耀自己的成功,這只會讓人反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現在中國不准外國人入境,這是因為中國不能再冒第二次疫情失控的風險,於情於理都不是自私自利。同樣,疫情爆發初期,香港、新加坡、意大利、美國等地對中國人封關、撤僑也是同理,人家也同樣不願意看到疫情蔓延,為何那時就可以攻擊別人是惡意製造恐慌,是對中國背後插上一刀呢?美國在歐洲疫情嚴重之後也禁止歐洲人前往美國,最後連英國這個小兄弟也進了入境限制名單。日本現在對包括中國、韓國、美國、歐洲在內的國民入境都採取14日隔離的政策。疫情初期,中國民眾對日本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曾經被我們罵得一無是處的大和民族似乎對中國很友好、很善良,向中國捐贈各類物資,而對美國政府的表現極為不滿。其實拋開美國民間和企業的資助不提,為何一定就要期待和中國正在打貿易戰的特朗普政府對你友好呢?而對中國最早鎖國的是朝鮮、俄羅斯、越南等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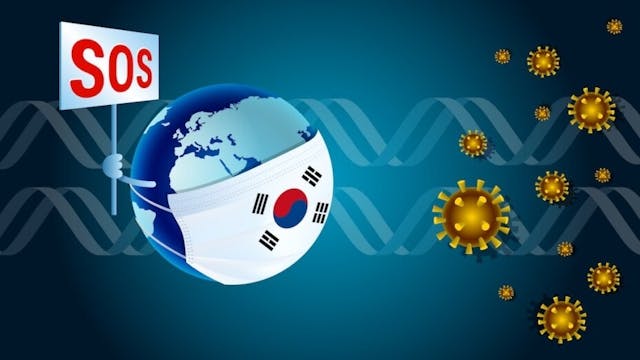
在疫情襲擊的恐懼中,我們更不可以幸災樂禍地嘲笑別人的行為,透過渲染別國的疫情失控來展現自己的英明和偉大,而忘記了自己並沒有走出險境。美國和意大利的報紙上密密麻麻的訃告,看去令人悲傷和沉重,恰恰彰顯了人性的一面。中國不少媒體將意大利和美國醫院中的屍體的照片無限渲染,而失去親人的武漢人前去領取骨灰盒,為了正常的悼念發出的哀思和照片卻消失了。我們當中總有人不願正視自己的創傷,不可忍受將苦難、悲劇和醜惡呈現在他們面前的人,將讀者高達5000萬的「日記」視為惡毒、無恥,卻又如此鍾情地展示「紐約醫院屍滿為患」、「紐約窮人疫情之下被迫乘坐地鐵上班」、「英國政府勒令醫生封口」這樣的文字和照片。廣東一個企業老闆竟然建議廠家做假測溫槍賣給美國,讓感染者愈來愈多,遼寧有餐廳門外貼出橫幅祝賀美日疫情擴散,就不單單是沒有同理心了,而是無知的反人類言論。
如果我們可以同樣毫無顧慮地拷問自己,猶如如此心安理得地對他人提出質疑,我們的心智就一定不會萎縮,我們興許也就有了希望。如今,我們甚至無法正常地伸出舌頭,道出自己的甜酸苦辣,又何必如此居高臨下,帶着幸災樂禍的病態,刻意營造似是而非的場景,來彰顯那虛幻的優越感?!但我總是固執地堅信,一個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只要勇於承擔起苦難中的責任,最終一定是會得到別人的理解和讚許的。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我們缺乏的只是疫苗?三之二
本系列文章:
作者簡介
教育家、營銷傳播專家、與媒體人。他專注戰略發展、品牌管理、和營銷傳播。他現擔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 常務副院長(商學及中國發展)暨金融商業學院總監。他推動創立了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ICB)並出任執行院長,以及香港大學SPACE企業研究院並擔任執行院長。
他曾是美國亞洲基金會、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以及德國柏林國際新聞研究院的訪問學人。他曾於1996年在美國被評選為五百位最有影響力的亞裔美國人。他是中國南開大學學士,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碩士,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