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劉寧榮教授現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常務副院長(商學及中國發展)暨金融商業學院總監。他於港大ICB微信平台發布文章,探討如何走出掀起全球大規模示威的「恐懼」與就中美衝突的成因與走向發表意見。本刊分三篇轉載其文章,下文是第二篇。
30年過去 東歐國家民主轉型慘淡收場
左右冷戰40年的東西兩大陣營已經不復存在。
2019年5月,我再次來到闊別幾乎30年的布達佩斯。上一次是在大雪紛飛的冬日來到匈牙利,那是柏林牆倒塌後的冬天,一個極為寒冷的冬天,濕漉漉的街道反襯着行人臉上憂鬱的表情。那也是對不可知的未來,充滿恐懼和期待相互交錯的冬日。
30年過去了,多瑙河畔那座奧匈帝國時期建造的輝煌的議會大廈依舊,而雙城之一的佩斯,其外表已經多了不少現代化的痕跡,市中心的街景與全球所有的大城市一樣,四處遍佈我們再熟悉不過的那些名牌商店了。在這座城市,昔日的恐懼已經不再,但當年的期待或許早已落空,隨之而來的也是幻滅。
與所有東歐國家一樣,民主轉型給大家帶來了程式上的民主,但匈牙利和波蘭早已背離了民主變革的初衷。一方面,當權者不斷地挑戰自由與民主的底線,排斥移民,極權的陰影重新籠罩;另一方面,裙帶資本主義已開始改變國家的政治,左右華沙政壇的家族勢力和布拉格的政商聯姻,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不幸的是,民眾的幻滅還在於,他們曾經不惜代價地想方設法擠入歐盟這個大家庭,卻在今日成為歐盟的「棄兒」和「壞孩子」,淪落為二等公民。

當我踏上至今依舊是歐洲最為貧窮的阿爾巴尼亞,在首都地拉那迎接我們的是廣場上的抗議者和員警的催淚彈,執政黨與在野黨總是走馬燈似地不停換位,並在此過程中持續地爭鬥。而沿路走過的無數巴爾幹國家,從塞爾維亞,到黑山,到波黑,依然充滿怨氣地等待進入歐盟的入場券。這些在北約主導下解體的南斯拉夫前加盟共和國,更是在掙扎中前行。
30年前,東歐社會主義的實驗場暗淡地關上了大門。30年後自由資本主義的實驗場在這裏也是傷痕累累,踽踽前行。30年前福山或許過於簡單地蓋棺論定「歷史的終結」,但他預見性地看到了歷史終結之處的西方社會,其前景同樣並不光明。他曾經警告自由資本主義的最大威脅是民主國家的極右法西斯,而右派民粹主義已經大搖大擺地走進歐美政壇。過去20年裏,極富煽動性的右派獨裁者的出現,以及極端伊斯蘭的興起和蔓延,這兩者可以說是自由資本主義失靈的內在和外在表現。自由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開始自生自滅並破壞自己的合法性,而吞沒西方民主的政治混亂還有比特朗普入主白宮、英國脫歐、和意大利修憲公投更令人扼腕和捶胸頓足的事嗎?
兩種資本主義各遇難關 不需隔絕和對立
如今自由資本主義忽然間碰到了一個巨大的對手,即主導中國過去40年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今天,這兩個陣營在爭奪全球的領導地位。但無論是歐美民主國家領導的自由資本主義還是中國領導的威權政府積極介入的國家資本主義,都有各自迫在眉睫的問題需要找到解決的答案。
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可以高效率地整合資源,統一協調經濟的發展,但更容易受到腐敗的衝擊;而確保經濟的長期增長已成為政權受到認可的唯一指標。一旦經濟增長緩慢,社會就可能更容易出現失調;長期被壓制的對自由、人權、和民主的渴望一旦爆發,就更容易引發社會的動盪和分裂。而政府的決策又缺少制衡,就會出現匪夷所思的危機,2019年一場席捲中國南北的非洲豬瘟就是其中一個最新的例證。但自由的資本主義也同樣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我們在美國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甚至2009年的金融危機,都見證了放任自由的惡果。
然而無論是在自由資本主義的美國,還是在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國,兩者又面臨前所未有的、且普遍和相似的挑戰與困境。經濟學家布蘭科·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在其新著“Capitalism, Alone:The Future of the System That Rules the World”中,一針見血地指出,資本主義帶來了繁榮,滿足了人們對自由的渴望,卻以犧牲道德為代價,追求物質的成功成為唯一的目標。
自由和財富的實現,也預示着以往社區賴以持續的穩定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這有如浮士徳與魔鬼的交易。過度的貪婪是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基因,財富分配的不公和貧富懸殊已經成為全球性的罪惡。而腐敗也不斷地蔓延,即便作為自由資本主義領頭人的美國,不同形式的腐敗,或者是合法化的「滯後腐敗」變本加厲。所有的離任官員和議員們都可以進入商界,將他們原有的政治資本兌現成商業資本;而華爾街和白宮所形成的共治,更是讓華爾街在過去40年的全球化浪潮中成為最大的獲益者。即便是舉起民主和人權大旗的美國,對民主和人權的雙重標準,更多的是服膺於國家的利益。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西方發達國家竟然出現了以往只有發展中國家才會出現的政商互動,商人與政治家角色的互換已被欣然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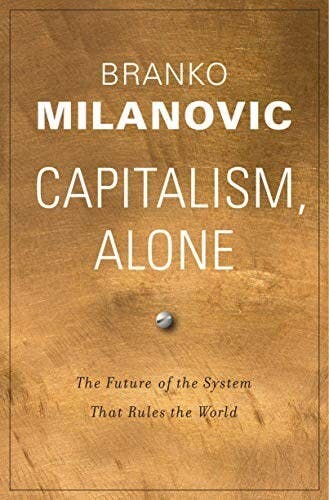
在過去40年,市場經濟在兩種不同的資本主義模式下都獲得了巨大的發展,這當然要歸功於全球化和資料化革命,中國和印度的快速發展就是一個明證。但全球化在今日的歐美已被妖魔化,事實是,全球化本身並無問題;而是當年兜售這些概念的西方政客們普遍失信於眾多中產階級對全球化原有的期望。實際上,從八十年代開始的全球化,為歐美的精英和商業階層提供了歷史上最快速的財富積累機會。但發達國家的普通民眾卻沒有從中受益,他們的收入和生活水準並沒有發生任何變化,這反而令他們更加恐懼暗淡的未來,西方政客又事不宜遲地開始兜售全球化所帶來的恐懼。資本主義的可能失敗,就是因為民粹主義的高漲和對全球化的不滿。所以中產階級的幻滅,不應透過製造新的恐懼而獲得心理上暫時的安撫。
在市場經濟席捲全球之時,我們不應該過多地畏懼自由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彼此間的不同。追求財富、自由、和民主已經成為共同的目標,但由此衍生出的罪惡,以及兩大陣營固有的瑕疵,更需要兩者之間的相互依存和互動,來共同尋找普遍性的答案。即便我們必須選擇競爭,我們也應該努力尋找應對相同挑戰的共同目標。
如今我們卻偏偏要選擇隔絕和對立。曾幾何時,「紐倫港」的價值就在於這三座城市都是向世界開放的大都市。因此把香港視作新冷戰的柏林,不是惡意就是無知,因為這不實際也無益。如果我們只是如此簡單地將一切的不同和衝突都視為民主與極權之戰,不是聳人聽聞,也是自我麻醉和毀滅。如果把香港推向這場戰爭的最前線,我們將成為恐懼和幻滅的最大受害者。在暴力的對抗和衝突中,我們將無法看到一次優質民主的出現。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曾把強有力的政府、法治、以及民主問責視為維繫現代政治秩序的三個最基本要素。如果這樣,或許強有力和廉潔的政府遠比衰敗的民主制度更有價值。
別忘了,歷史是流動的,文明是流動的。2018年的初夏我來到中亞古城布拉哈,這是古絲綢之路上連接東西方的商貿重鎮。在一個古老集市上,在炎熱的夏日裏,我走近一座拱形的房子頓感陰涼舒適。圓形的建築設有朝向四個不同方向的大門,坐在裏面的商販告訴我,這四扇大門連結四條大道,通往羅馬和長安,也通往波斯和印度。
而我正站在當年古絲綢之路的十字路口上。
歷史迴圈前進 中美需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2019年的12月,我在歲末踏上了北非的突尼斯城。我到這裏尋找腓尼基人的足跡。西元前814年由腓尼基人興建的迦太基古城,曾經是地中海經濟強國迦太基的首都。經過三次布匿戰爭,他們在爭奪地中海的霸權中敗北,被羅馬人佔領,在當時成為羅馬以外最大的都市。西元七世紀阿拉伯人佔領這座城市,北非也進入了阿拉伯化的歷史時期。
在突尼斯城東北方向17公里的遺址上,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文明和建築在這座比爾薩山丘上層層疊現。在很長時間裏,迦太基城的故事只是個傳說,古迦太基滅亡之後,羅馬軍隊摧毀了整座迦太基城,勝利者把失敗者從歷史的記憶中完全抹去了。

進入二十一世紀,兩強之爭不應該是這樣的結局。歷史總是在不斷地迴圈前進,不斷地淘汰弱者,和選擇新的霸主。如今這個迴圈又到了一個新的危險轉捩點,持續了45年之久的冷戰最終以和平收場,在度過30年沒有兩強爭霸,只有恐怖主義這一共同敵人的歲月之後,新的霸主之戰再次揭幕登場。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前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早就警告中美需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說,「伯羅奔尼薩斯戰爭的無可避免,皆緣於斯巴達對雅典崛起的恐懼。」雅典的崛起令人歎為觀止,並對其它國家造成巨大的震撼和帶來心理上的恐懼。斯巴達人當時已統治希臘100來年,最終兩國間爆發了戰爭,而這場戰爭摧毀了古希臘的兩個主要城市國家。在修昔底德陷阱中,關鍵的因素就是斯巴達的恐懼。
中國崛起被無限放大 恐懼妄想症無中生有
2019年,類似的恐懼早已被渲染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曾在美國國防部等政府機構任職,且被視為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中國問題顧問之一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幾年前曾出版過一本頗有爭議的書,書名是《百年馬拉松:中國取代美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2019年7月,他在華盛頓大西洋理事會上提及經濟學家預測中國在2049年的經濟總量將是美國的三倍,他對此發出了如下警告:「中國會控制我們,我們將成為中國的殖民地。」
這樣的恐懼妄想症甚至上升到美中的對抗,是一場前所未有的不同文明和種族大決戰。2019年4月,時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的斯金納(Kiron Skinner),在美國一家智庫舉辦的「未來安全論壇」上也同樣危言聳聽,她說:「這是與一個很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識形態之間的爭鬥,而且美國以前沒有經歷過這種情況。」她還說:「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這是第一次我們將面臨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不是高加索人種。」這位在哈佛大學獲得政治與國際關係博士學位的美國非洲裔人竟然認為,白種人和黃種人之間的博弈,是美中對峙與美蘇爭霸的另一個不同之處。
而在2019年,香港議題在毫無防範的情形下走向中美對抗的前檯,恰恰說明兩強相爭推波助瀾的歷史事件往往都是那些意想不到的非主流事件。2019年6月我站在塞拉耶佛市中心的拉丁橋上,回想起1914年6月,奧匈帝國的斐迪南大公在這裏被暗殺,這一事件與英國和德國都沒有太大的關係,但六周內整個歐洲卻因此處於戰爭狀態,並在四年內被全面摧毀,世界因此重新洗牌。在中美走向對抗的這個脆弱敏感期,這些意想不到的事件或許有更大的潛在風險。
甘迺迪在古巴導彈危機之後對赫魯曉夫說:「我們必須為多樣性創造一個安全的世界。」

如果臆想的「中美國」已經不復存在,「中美經濟體」已經消亡,但中美獨立的兩個經濟體的良性競爭,互相依託,恰恰可能為中國提供自我創新而非簡單複製的空間,同時也讓美國心牽腸掛難以忘懷的技術被迫轉讓、智慧財產權、市場准入都不再是令人折磨的難題。其實,我們大可不必因我們的恐懼和幻滅,對所有過去的認知做出180度的大轉彎。特朗普一方面逼迫中國購買更多的美國農產品,獲得更多市場准入的機會,另一方面又如何可以關閉曾經對中國企業開放的美國市場呢?這樣的脫鉤將如何實現?
2009年行將結束時,中國幾乎成為全球的救星和自由資本主義的救星;2019年行將結束時,中國則被描繪成自由資本主義的最大威脅。但這兩種認知都與事實相距甚遠。
原刊於港大ICB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裂變:走出恐懼與幻滅三之二
本系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