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於醫學世家,父親及妻子都是醫生,卻讓子女做喜歡的工作,沒有一個行醫;儘管「揸刀搵食」,他拿起支筆同樣頭頭是道,幾萬字的書,四個月完成;先後出任醫院管理局和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回歸前後做過立法機關議員,也曾是行政會議成員,這個行醫大半個世紀的公職王,一言蔽之形容「醫學是科學,行醫是藝術」。行年80,仍然口若懸河、健步如飛,金刀未老,從無想過退休,他是「金刀梁」梁智鴻。
以為醫生睇症「例遲」,這個髮型恆常中間分界、穿筆挺三件頭西裝的中環人,訪問當日早到十分鐘。「以前教授教落,一定要準時。」還是那副招牌朗笑的梁智鴻,安坐「明德椅」拍照(「明德椅」以明代風格設計,是香港大學頒贈予「明德教授席」捐贈者,以表達謝意的紀念椅),說起他與醫學院的淵源,由父親到胞弟,都是港大醫學院畢業生,到後來他重返母校擔任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兩代一門三傑,情深意重。
想做醫生是受父親影響。「爸爸(梁金齡)在香港仔行醫,那時香港仔仍是偏遠的漁村,要坐貨車去,爸爸是那裏唯一的醫生,也是唯一諳英文、可與政府官員溝通的人,所以大家有什麼,都會找他幫忙。」
打仗時梁家一度離開香港,戰後他父親再度於香港仔執業,那些年的人情味,還有行醫可幫人的記憶,深植他的腦海。「那時在香港仔行醫,因為無人會去那裏賣藥,爸爸和媽媽要用大藤籃,每日帶藥物過去;我最記得媽媽大肚時,都要坐那些改裝貨車,挽住幾個籃入去。」
打風接生 過年簽死亡證
在困乏的年代,大部分的父母都得為口奔馳,每周返足七日工是常態。「唯一見到爸媽就是星期日,跟去診所,他們看病,我們就坐在一角,有時幫手執藥,那個時代藥水是溝出來的。」權充小小藥劑師邊學邊做,教他更理解診所的日常運作。「戰後回港,住過幾個地方,最初住在油麻地黑布街,當時香港百業蕭條,一家七口住在板間房,後來搬了去英皇道、皇仁書院附近。」
自小立志做醫生的梁智鴻,考進聖若瑟中學,每天坐電車上學,讀到最後一年才轉到皇仁:「因為我想讀醫,必須要考生物學,當時聖若瑟沒有高級程度的生物學課程,所以要轉校。」
「(當時)父母都很忙碌,沒有在我讀書的時候教我什麼,但好多身教,最記得有次八號風球,有位水上人要生仔,他二話不說就跳上舢板,幫人執仔。」還有那個教他記足大半個世紀的大年初一:「最記得有位蜑家佬過身,那是年初一,好多人覺得是大忌,但爸爸照去簽死紙(死亡證)。那年代求醫很多時不是付錢,而是封利是,10元左右,加一斤魚和蝦乾,最特別的感受是,做醫生真的可以幫到人。」
小時候品嘗海鮮的機會多的是,但梁智鴻偏偏無福消受。「好怕食魚,食親魚都鯁骨,鯁過七次骨!」笑言這或與自己口若懸河,喜歡邊食飯邊說話有關。
他有七兄弟姊妹,只有他和胞弟、醫院管理局主席梁智仁是讀醫。「我和弟弟性格很不同,弟弟比較內向,我就外向,他排第三,大家相差五歲……我是有點大哥格,好多主見。」那些年,父母想要抽空教導孩子不容易,可幸梁家的孩子都很爭氣。「我們比較好彩,爸媽讓我們七個都可以讀到大學,讓我們都有自己的專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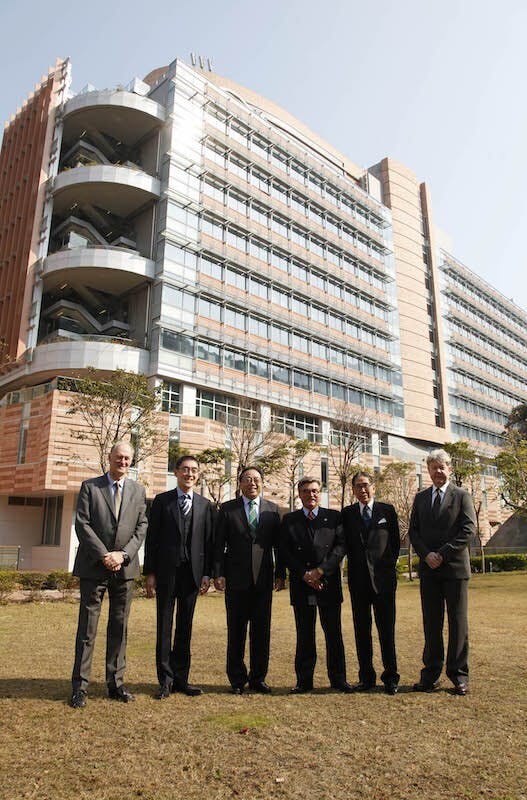
讀醫 一理通百理明
這個擁抱自由主義的父親,也喜歡讓子女自由發揮。「我讀醫、太太讀醫,但女兒在英國攻讀哲學、政治學及經濟學(PPE)畢業,兒子做工程師興建度假酒店。他的公司在曼谷,但他長期穿梭於內地、中東、非洲等地,香港只是過境地,往往在港只會留下一句:爹哋,我今晚回家睡就是了。」教子方程式,無招勝有招。
1962年畢業於港大醫學院的梁智鴻,讀醫一樣舉重若輕。「讀醫是一理通百理明,明白原則,將原則伸展到其他地方就是。」畢業後在港大任教了16年,他直言強記無用:「今時今日跟過我的學生,都說我教書最好,因為不用強記很多東西,我只會教他們幾個重要原則,遇到這個情況,你有三個問題要問自己,記住三個原則,就可以伸展到其他情況。」梁智鴻自言人生之中遇過幾個恩師,終身受用。
醫學是科學 行醫是藝術
選擇外科專科,也反映他的人格特色。「外科醫生通常會說,先打開(開刀)看看情況,內科醫生則喜歡先作思考。我跟過幾個外科的師傅,很欣賞他們的工作,也欣賞他們爽快決斷的性格。」行醫多年,他謙稱是終身學習,「每見一個病人又學到新事物……要知道永遠無完美,只有更好,沒有最好。」他認為,醫學是科學,行醫卻是藝術。「兩個患上同一種疾病的病人,醫生也可用不同的方法診治,所以說這是藝術。」
1970年代初,梁智鴻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進修,之後有幾間,包括在芝加哥及佛羅里達州的大學向他招手,提供教席邀他留下服務,他將因此有機會取得美國公民資格。不過思前想後,這個英語能力勝過中文的「香港仔」最終還是婉拒,原因是心底裏,他服務香港的心仍然熾熱,也不願到彼邦做二等公民。「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決定是對的。」
行醫這些年,梁智鴻這樣表達最苦與最樂:「病人可以再行路、可以康復,做回平常會做的事就是最樂;但當你用盡方法去醫,病人都是好不了,這就是最苦。」他說,「病人康復是頭獎,但你盡全力結果不盡人意,也只能接受……當然會失望,但不應洩氣。」

醫德比醫術重要
謀事在人、成事有時也得看天,只是醫德和醫術之間,輕重就易揀得多。「醫生非單醫病,更是醫人,好多人說醫生是否搵好多錢,我相信好多我們私人執業的行家,十個裏有一兩個病人,是不收錢或者減價應診。」
既是醫生也是公職王,由手術枱到社會服務,他謂互相影響,也一脈相通。「每一份工作都是一種學習,醫生識得醫人,但對社會的認識未必很多,做公職,某程度是將我從一個狹窄的醫生環境擴闊開來,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他舉例,當醫學會會長期間,遇到的都是醫生,大家同聲同氣,但擔任醫管局主席,其董事局成員很多不是醫生,而是很有經驗又知名的行政人員,如何駕馭他們的思想?這是學問。因此幾大幾細的公職,也是一種學習。」
他謂「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從未想過退休的他,笑說年齡只是一個數字,慶幸妻子與他有相同愛好,就是工作,所以很合拍。
任馬主 笑言少探愛駒
梁智鴻目前是「金刀之友團體」名下馬匹「良朋共盛」的其中一名馬主。他不時偕妻子去馬場消遣,也曾是退役團體馬「金刀銀鑽」的馬主之一。這裏「金刀」自然是他,「銀鑽」是他一名牙醫好友,他直言朋友在馬場共聚,是開心的事,只是過去養馬,總因工作太忙無暇探望,殊不知「金刀銀鑽」很爭氣,讓他拉了一次頭馬(2015年),十分驚喜。「朋友都說馬是要氹的,再養真的要去探望。」同是團體馬的「良朋共盛」有福了。
那麼,梁智鴻如何評價馬會對社會的貢獻?「好多年前,馬會要求增加賽馬日,那時很多社會人士反對,認為鼓吹賭博,我是第一個去聽證會表示贊成的人,因為在我心目中,香港賽馬會不是一個賭博的地方,而是一個慈善機構,每年撥很多錢給香港做慈善工作,如果沒有馬會,很多工作可能開展不了。」他舉例指,醫學專科大樓、伊利沙伯醫院的癌症中心及防癌會在黃竹坑的康復中心,馬會都有份支持。

籲求大同存小異
他每次外訪或者去機構探訪,說手信大都購自馬會會所的禮品店LEVADE,一來輕便,最重要還是視馬會為香港最大的慈善捐助機構。
馬會一直支持醫療衞生及復康服務等多個範疇的慈善工作,包括2003年沙士爆發,馬會透過其慈善信託基金捐款5億元支持設立「衞生防護中心」,及捐助2.5億元予醫管局推行「賽馬會安寢輕移計劃」,協助公立醫院安裝病人吊運系統及電動病床等。
金刀未老,未言退休的梁智鴻除了在電台開咪,又寫書回顧人生歷程,書名叫《理性的呼喚》(The Triumph of Rationality: From Surgical Practice to Public Service),對應今日社會,作為社會領袖,確有先見之明。「在任何環境,理性都好重要,人與人之間如無互諒互讓,不肯求大同存小異,是行不通的。」
這名「揸手術刀搵食」的仁醫正計劃將電台節目訪問的不同人物,書寫成不同的人生小故事,值得期待呢。
後記:少年智鴻的煩惱
因為訪問,才赫然發現,眼前頭髮烏黑又健步如飛的梁智鴻,原來已經80歲。求問駐顏心得,招牌朗笑後,他向在場工作人員拋下兩句:繼續做、睇開啲。「要接受自己未必好似以前那樣,行不到五層樓梯都得接受……」
除了駐顏有術,三件頭西裝和髮型中間分界,也是他的個人標記。「我不是一個姿整的人,但肯定是一個愛齊整的人……這麼多年,我未嘗擁有過一條牛仔褲。」穿窿牛更是no way。
至於中間分界,他不諱言曾幾何時,這是「少年智鴻的煩惱」。「梳左梳右都彈起,做細路仔十幾歲時好尷尬,用髮蠟或者夜晚用網套住,第二天醒來仍是彈起……」
兄弟姊妹之中,唯獨他有這個煩惱。「細時覺得好陰功,而家完全無嘢啦,最驚是光頭。」駐顏心法,相信包括清心直說。
原刊於香港賽馬會《駿步人生》第27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