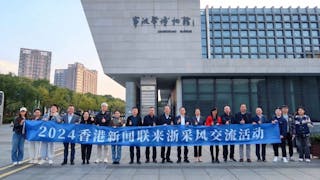近兩個月,筆者先後在湖北恩施、湖南懷化等地走馬觀花式地行走,發現一向被視為落後的中國農村正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對未來中國的發展將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適逢中美貿易戰處於膠着狀態、中國經濟正面對「嚴峻」的「驚濤駭浪」,農村的這種變化無論是從社會還是經濟角度看,似乎正起着「穩定器」、「壓艙石」的作用。
我曾有一個比喻──中國的摩天大樓有多高,城鄉之間、城市人與鄉下人之間的差距就有多大,理論化定義是「二元化」結構。
農民工,社會變革代價最大承受者
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成就,有人認為是產權制度改革的收效,有人認為是打開國門,引進西方資本和技術的結果,官方強調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無論哪種解釋,歸根到底都是農村、農民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當年農民們簽訂「聯產承包責任制」合約,為高層找到可以「借助的話語和邏輯」,撬動前30年陳舊、僵硬體制的經濟改革由此開始。以對外開放方式成為「世界工廠」,如果沒有數億廉價勞動力這個條件,也只是一種奢望。「農民總是社會變革的代價的最大承受者,卻總是社會進步的最小獲益者」(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郭于華語)。這些年,農民工被戶籍制度擋在城市之外、農民工子女在城市讀書、農民工的權利保護都是極富爭議的話題。
國家主義的新鄉村主義
這次湘鄂行,筆者去了湖北恩施、利川、湖南懷化、湘西等市、沅陵等5個縣、若干村鎮。得到的印象是,農村正在施行由政府主導的「國家主義的新鄉村主義」(中國農業大學李小雲教授語)。從社會管理角度看,村級管理和控制在加強,每個村都由村支部主導,很多地方村支部書記兼任村委會主任,政府下撥的各種款項均由村委會發放到農民手中,而村委會又實際為村支部所領導。
掃黑除惡、精準扶貧、鄉村振興,這三項由最高層主導的行動正在衝擊着農村的每一個角落。官方公布的掃黑除惡典型案例中,村委會主任為非作惡、截留、貪污扶貧等款項的佔相當比例。當局在十九大後啟動這個為期三年,使用和反腐、環保相同的最嚴厲手段──派中央督察組到各省實地督戰。
今年10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打好掃黑除惡的『綜合試卷』」的評論員文章,稱「掃黑除惡不單是一道如何懲治犯罪、維護治安的考題,更是一套整肅貪腐、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完善基層治理的綜合性試卷。」如此看來,掃黑一方面表明當局對基層政權失控的憂慮,而精準扶貧、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有賴於這個「神經末梢」去貫徹執行。
雖然村支部、村委會並非正式政權組織,但由於村級集體經濟除了賣地、租地收入,大多為空白,目前這兩個組織運作主要是依靠上級政府撥款,所有它們成為一級事實上的政權組織。在外人看來已經結束的計劃生育,目前仍在農村施行中。湖南永順縣小溪鄉一幹部說,農民仍然重視傳宗接代,如果前兩胎是女孩,一些人就想生第三胎甚至四胎。我們的對策是早發現、早動員,但不會像過去那樣強制打胎,而是用徵收「社會撫養費」方式做處罰。
精準扶貧
此行途中多次遇到農民主動稱讚習近平,緣由都與「精準扶貧」有關。鳳凰縣千工坪鎮黃沙坪村一農民說,他的家庭被列入貧困戶後,政府按照每人25平方米的標準,給了4萬元蓋新房專款,加上自己的錢,用20萬蓋了一個兩層的新房,而且每年政府還有其他補助。

永順縣小溪鎮的幹部認為這種做法欠妥。「如果他有錢蓋那麼大的房子,怎麼會是貧困?」「我們這裏按照貧困戶每人25平方米的標準撥款建房」。
在該鎮遇到一個年近50的婦女,夫婦二人在外面打了十幾年工,沒有來得及在偏遠鄉下蓋新房。就被列入貧困戶,政府不僅為他們在芙蓉鎮附近蓋了新房,而且每年還有各種補助。已經做了奶奶的她感到無比幸福,到姐姐家串門時,不時對着手機低聲吟唱。
相比之下,她姐姐一家就沒有那麼幸運。夫婦二人也是在外面打工多年,用積攢下來的錢在村口蓋了個三層樓房做客棧生意。
問男主人為什麼不是貧困戶?他答:「我是『四類分子』」。四類分子?我很驚訝,難道40年前以階級劃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的「四類分子」死灰復燃?他說不是那四類,而是「有房、有車……」
這個在廣東、浙江、雲南多地有打過工經歷,見過世面的山裏人既坦誠,又狡黠。問他這個房子有多大?他說幾百平方米。我說上下三層,不可能!他不無尷尬地說:「說少點好,說少點好。」
公平向來是一件「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困難事,如今城裏人分割上代人留下的家產,上演了那麼多幕父子成仇、兄弟反目的悲劇,更何況在有2020年完全消除貧困「硬指標」,暗藏着千絲萬縷、錯綜複雜親族關係的農村?
從小溪村去鳳灘碼頭的小巴上,半個小時車程,包括司機在內的車上幾個當地人始終議論一件事──精準扶貧。他們的方言我只能用猜的方式略知一二,但其中一兩句聽的很明白:「3000元就是貧困?現在養頭豬、幾隻雞都超過3000元了。」的確,用一個數字作為全國的統一標準,僅就地域而言就不那麼公平。
這次順江而下的沅江發源於貴州,過去曾是西南連接華中的交通動脈,鐵路和公路的出現令它的功能退化,沿岸城鎮變得冷清,一些地方更加閉塞和貧困。例如曾有「小南京」之稱的湖南瀘溪縣浦市鎮,過去的檣帆雲集盛景已經成為過去,鎮上最熱鬧的日子可能只有陰曆逢二、逢五的集市。
農村「大基建」
這種局面正在改變中。除去已有的重慶到長沙、杭州至瑞麗的高速公路,時下政府正在修建從杭州經常德到貴陽的高鐵,建成後西南與東部沿海的聯繫會更加暢順。
微觀方面,按照振興鄉村戰略的規劃, 每個村落都要修通「硬化度」80%以上公路的指標,所謂「硬化」就是瀝青或水泥路。此外村村通電、通自來水、互聯網覆蓋、電視進村,這些工程雖然以村為單位,但是以全國270萬個自然村計,就是一個非常浩大的工程。
筆者在山區鄉村的「脫貧攻堅」公示欄看到,很多貧困都是由於「交通落後」或「交通不便」造成,脫貧方式是「易地搬遷」。全國貧困地區中,這種「交通不便」或「生態補償」的搬遷也應當是一個天文數字,其中為這些搬遷者蓋建新房數量也將相當可觀。
依此判斷,繼城市大規模基建基本完成後,未來中國下一個「大基建」應當在農村。
農民工返鄉
經濟不景氣不僅表現在股市,農村也感受到經濟下行的陣陣寒意。在位於沅江中下游的五強溪水電站附近一個鄉間餐館,雖然已是午餐時間卻很冷清。夥計說由於經濟不景氣生意差了很多。「原來江邊有很多做沙子生意的,現在都見不到人了。」
官方公布的數字稱,自2015年國務院發布《關於支持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的意見》至去年9月,全國共有480萬農民工返鄉創業,相信一年後的今天又有相當幅度的增加。除了農村發展、就業機會增多,沿海地區一些工廠裁員倒閉都是原因。
令人記憶猶新的是,2008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東部沿海許多生產出口產品的工廠被逼裁員,據稱當時有2000萬農民工被逼返鄉。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嵐清從當時為薄熙來主政的重慶回到北京後,撰寫報告提醒中南海注意這個變化,因為這些農民工當中一些人沒有真正回鄉,而是滯留在重慶的廉價旅館裏消磨時光。中國歷史上「流民」向來是統治者的心頭大患,多次大規模社會動盪都與流民有關。
從目前的情況看,北京高層和社會沒有因此公開表現出太多擔憂。筆者在農村接觸到一些返鄉農民工,他們或幫助家中打理農家樂、客棧,或在本地找些事做。偏僻山區請一個普通勞力,每天人工150元。如果考慮背井離鄉等因素,在當地每個月若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相差不多。

中國農村目前實行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的「三權分置」,農民可以把獲得承包權的土地以流轉的方式委託給其他人耕種。這種制度受到一些學者的批評,認為只要通過土地私有化,允許土地自由買賣,農民通過賣地獲得原始資本後,方可自主創業,進城做生意,最終現代化和城市化。
2000年以來每年有半年時間在農村生活、寫作的內地作家韓少功認為這是書生的想當然,它是「人人都是天然的理財能手、都能『利益最大化』的假設」。幾年前筆者在廣西陽朔與農民交談得知,當地一些農民獲得徵地補償款後,用這筆「意外之財」賭博,很快就被揮霍一空。
韓少功的看法是:「家庭承包責任制儘管不是一個最好的制度,卻是社會巨大的穩定器,是給一大半老百姓社會保障托底。其微觀經濟效益如果不是最優,但至少有宏觀的社會效益最優──至少讓中國不至於成為全球第四個貧民窟大國。」他認為,巴西、印度、墨西哥世界級貧民窟的出現,源於土地被過度兼併。
在家鄉有土地、有住房,農民工面對經濟波動,有了進可攻、退可守的「避風港」,這也是中國的一大特色吧!
新鄉村主義
以農村為研究方向的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小雲認為:「2006年政府取消農業稅,標誌着農民和國家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政治角度來講,隨着農民數量的減少,他們正在成為稀缺的政治社會資源,正在變成各種政治力量競爭的對象,農民正在成為社會政治生活中能動性的政治力量之一。」
他將中共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稱之為的「國家主義的新鄉村主義」。這種政策符合中共的「初心」,因此具有政治基礎。
筆者一位朋友的父親上世紀30年代初參加中共,近年回鄉下江西吉安扶貧。問他鄉親是不是很感謝你們?回答是:「完全沒有。當地人認為早就應當回來報答當年他們對紅軍的支持。」
2010年後,城裏人享受的改革「紅利期」接近尾聲,對於國家未來發展方式的分歧明顯擴大。目前的鄉村振興、精準扶貧,只是農民享受改革「紅利」的開始,支持政府現行政策在他們看來是理所應當的事情。
李小雲教授認為,「國家主義的新鄉村主義」第二個作用是「投資鄉村相當於創造新的需求」,這符合發展理性。深圳某旅遊公司正將湘西鳳凰縣一個完成「生態搬遷」的舊山村進行整體改造,可能就是李教授所說的「投資鄉村創造新的需求」的案例。
此外,「國家主義的新鄉村主義在多個基本面上整合了『左中右』關於鄉村問題的主張,建構了一個超越各種力量的道德框架,這個道德框架是高度去政治化的,不是說我代表左的力量或右的力量,在弱勢主義上大家都會同意。」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力圖構建一個超越改革開放議程的新的政治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