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本港的高等教育,乃至全球大學文化,李歐梵教授最懷念1970年的香港中文大學。那年他剛回港,初到中大任教,馬上就感受到一派濃厚的人文氣氛,大為感動,打從心底裏喜歡這個地方,並認定這就是他心目的理想大學。
可惜事過境遷,李教授數十年後重返舊地,卻驚覺物是人非,不論是中大,還是其他院校的辦學模式,都令他大失所望。他於是屢次提出建議,可惜始終未獲大力支持。
教育就是給予 理應不問收穫
李教授的教育理論,與美國大學的辦學方式十分相似,他以兩地大學作比較,指出兩者單是看待資源的觀點便已是南轅北轍。「我在美國教書的時候,當地院校給了我充足的自由。舉個例子,他們發研究費時,從來不過問我怎麼花,也沒有要求我寫報告。校方偶爾會問我捐不捐款,可是我從來不捐,哈哈,這也沒問題。」
他解釋,教育的意義就是給予,理應不問收穫。「我在哈佛讀研究生的第一年,拿了筆奬學金,可是錢有點不夠,後來該校主動問我暑假要不要錢。他們給我錢的條件只有一項,就是要我學點東西,我說我要學俄文,他們也非常歡迎。你想想,我當時的專長是中國現代史,和俄文是絲毫沾不上邊兒的,為何他們願意給我錢,讓我學和工作完全無關的學科呢?原因就是,大學應該提供廣義的教育傳統,這也是教育的意義,不能要求一年生樹,二年結果。」
可惜的是,李教授熱心教學多年,觀乎本港大學辦學方式,與他心目中的理念始終背道而馳。「所以我放棄了,只批評。因為就算我提出了意見,他們聽了,也沒有辦法做到。比如說,我建議學校直接給教授發研究費,發了就不要管,就當是風險資本,投資一筆錢,賭一個將來。就算投資了三位教授,最後只有一位得了諾貝爾奬,這也就值了嘛。美國有個 Bell Telephone Laboratories,他們開始的時候就是這樣的模式,結果一大堆諾貝爾奬從那裏冒出來。後來他們分專業了:這位教授專門研究電子、那位教授研究甚麼甚麼的⋯⋯搞着搞着,一個諾貝爾奬也得不到。」
「專業化」扼殺創意
Bell Telephone Laboratories 的例子帶出了李教授的另一個辦學理論:「大學教育的最大悖論——愈專業化,創意愈少。追求專業化的後果,就是令大學環境出現變化,使學者愈來愈難寫出一本大書。我常常問人文學者,包括我自己,近10年、20年有哪一本書是全世界的學者都在讀?」
他又以自己從前唸書經驗作例子。「我在美國主修中國近代史,另外也修中國古代史,還有俄國思想史。我非常用心地唸俄國思想史,一整天在唸,結果卻考得很差,但始終受用最多的還是俄國思想史。」

芝加哥大學最特別
李教授年少留學海外,畢業後亦曾在多間世界名校執教,綜觀各地院校,他認為芝加哥大學最特別,讓他深深地感受到,教育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芝加哥大學規模不大,研究生比本科生還要多,但它的本科教育非常特別,當年所謂的 great books,即是『經典閱讀』的教育模式,就是從芝加哥大學開始的。該校的教育方式,可以說是反制度化的,教授怎樣教都可以,我在那裏教書也是完全自由發揮的。研究院也是絕對自由的,所以諾貝爾經濟奬一個接一個從那裏出來。」
「他們聘請了很多大師,給予充分自由,很高的薪水。有一位社會學的教授,某天他跟學生說:『明天教 Max Weber,他是德國人,所以我用德文教,你們聽得懂就來,聽不懂不要來了。』我後來想想,也對啊,德國哲學就應用德文教。同樣,中國文學就是要用中文教,為甚麼要用英文?本港大學錯的是,他們以為『國際化』就是用英文教中國文學。真正的國際化應是多元的,教德國史就用德文,法國史就用法文,俄國史就用俄文。」
每所大學都有怪人
剛才提到的社會學教授其實是美國人,那天他始終堅持用德文教。對於香港學生來說,那位教授可能是個怪人,但李教授指出,其實每所大學都有怪人。「愈是有名的院校,便愈多怪人。芝加哥大學有另一位教授,不懂中文,可是非常喜歡儒家,專門講孔子,講得非常好,該校破例讓他教,給他特別的位置,他後來一輩子獻身芝加哥大學。」
「不止是教授,聽課的人也怪,有個人旁聽上課十幾年,根本不是學生。他把講課的內容錄音,在外公開販賣,這事其他教授都知道,但他們也不管。各種怪人都有,哈佛、耶魯更不用說,更多不合乎主流的教授也有。」
雖然李教授十分嚮往美國教授的自由,然而當地部分民眾卻表示抗議。「『自由』理應包括日常生活行為,但美國大眾都不太接受教授的行為,覺得他們放縱了。這種想法和香港高官一樣,當年一位特首就說,你們教授太奢侈了,也不上班。他又說,要是資助全港學生出國留學,花的錢比現在花在本港大學的還少。這是一種反智的傳統。」
給予教授充分的自由
有人指出,本港大學走向專業化和制度化,為的是在世界大學排行榜上爭一席位,向世界展示本港高等教育的素質。為此,李教授不以為然,認為排名高低並無太大意義。「這些排名都是企業式的,考慮的是畢業生數量、論文數量,若然論文能刊登於國際刊物則更高分。但最荒謬的是,依這個指標,最『優秀』的一本書就是最糟的那一本——The World Is Flat。這本書不見得是第一流的著作。我其實很想找人合作,編一本書講大學教育的反思,衝擊一下本港教育。」
「盲目相信排名即是迷信數字。如要提升教育素質,我的建議依然是給教授充分的自由,但可惜的是本港大學不會這樣做,因為排不了名。以前當教授就像當神父一樣,獻身教育,不計結果、回報。我的理想就是這樣。但有人說我這種想法過時了,我的回答是,你看看哈佛和史丹福,同樣有官僚主義,同樣有排名,但他們通通不管。有一年,普林斯頓大學贏了第一,有人問校長怎樣看,他說:『這有甚麼好說?Of course!』這是開玩笑的。要知道第一流的大學根本不管這些,批評也好,排名也好。」
「再以哈佛作例子,他們一心一意在教育上創新,不停改革,近年就新增了 freshmen seminar,這項活動非常自由,曾經有位年輕的女教授教六四,最後開個大會,請各路人馬來辯論。」李教授表示他也是最近才發現這事,得知時還大吃一驚。「哈佛無論 Business School 怎麼賺錢,都不會影響它的最大教授團體:Art and Science。這個團體是人文與科學連合在一起的,裏面的教授不得了,五分鐘就能把大道理說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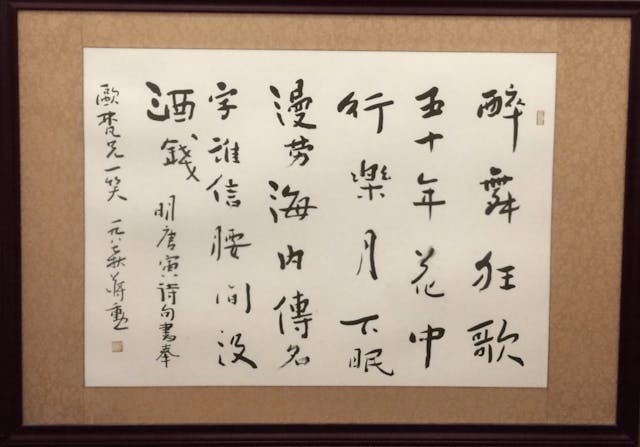
人文學科要特別的教學方法
李教授特別指出,現任哈佛校長是位人文學者,「她是學歷史的,是哈佛史上少數修人文的校長,以往的大多是科學家。另外,芝加哥大學也一度有位校長是個音樂家。說了這麼多,我們要問一問,為甚麼美國大學能夠保持傳統,甚至重新創造傳統,本港大學卻一味認為傳統就是過時,急着要把它破棄掉?不是不讓你破棄傳統,但你也得拿出個新的嘛?可怎麼說也拿不出來!」
事實上,李教授也不是只批評本港大學,他對個別大學也有特別欣賞之處。「說句實話,若只論文化研究、中文系等,嶺南大學最優秀。即使香港中文大學也未必比得上,但我也知學生不是這樣想。而中大呢,它的通識教育很好,我看學生寫的文章後才知道,寫得真的很好,馬克思啊,莊子啊甚麼都有。」
「教人文學科比較難。它不同財經科,只要把最新的資科拿出來就好。教人文不可以用 Powerpoint,就算用也要以特別的方法。我教的時候,也只是把一些文本放在 Powerpoint,總共幾句而己。有次我開玩笑,故意把德文放進去,我說我也不懂,你們學生有沒有人懂?結果有兩位學過德文,懂得唸但不懂解釋。我下次打算把西班牙文也放進去。這是一種挑戰,老師就是應該想盡辦法挑戰學生,讓他們感受自己是在教學裏頭的;而不是被動,我在這兒講,你就只坐在這兒聽。」
香港多幾個李歐梵很危險
「現在有些學生覺得自己是消費者,教師是供應商,我就聽說中大有個內地生對教授說:『我花這麼多錢,你卻教得這麼差。』這也是制度化的問題,大學應該提供一個環境,讓至少有一部分人不守成規。至於如何管理品質,我的建議是請人時要嚴謹,甚至在第一年試用期的時候,全心觀察教授的創意。可是現在聘請教授是有委員會的,教授表現一看學生評分;二看論文。論文只看數量,不理素質。若然一位教授一年能寫十篇論文,他一定高分,也不管論文是不是寫得亂七八糟的。」
簡而言之,李教授建議大學規劃課程時,把人文、科學及財經學術分開,為兩者各自設計合適的結構。「那麼,一些既是人文,又屬科學的學術怎麼辦?應該給它更多的自由。完全不管,鼓勵創意、鼓勵跨學科,如果有位教授願意在商學院裏教老子、物理,給他自由,看看他的成果。」
「但問題是他們不願意冒這個險,怕萬一沒有成果怎麼辦?這種過分 outcome-based 的思維不好,我公開反對。我一直說我教的科沒有 outcome,你們喜歡就上,不喜歡不要來。所以如果香港多幾個李歐梵不得了,很危險。雖然你們看我現在挺好的,可是我非常了解,這不是由於我教得特別好,而是因為我有美國名校做後盾,他們只是借我的文化資本,借我的名氣。」
愈是年輕的教授 愈要讓他們做研究
眾所周知,李教授是世界知名的人文學者,可是倒過來說,年輕教授應怎麼累積自己的文化資本呢?「在美國,我在普林斯頓當助理教授時,他們給我減科,人們教五科,我教四科,給我時間做研究。他們的邏輯是,愈是年輕的教授,愈要讓他們做研究,也要讓他們當資深教授的助理。我現在於中大教書也是這樣,有兩位助理教授幫我教歷史。第一堂,他們很快把東西教好,非常完善。餘下時間我就借題發揮,和學生探討一些問題:例如『司馬遷為何這麼看重項羽?』講着講着,說到劉邦,再談談《三國演義》,一下子把整個文化說出來。如果沒有這兩位助理教授,我可沒有時間教這些了。」
除了這種資深教授與年輕教授的合作教學外,美國大學還是一個特別的現象:最基本的大班課,反而都是經驗老到的教授在教。「普林斯頓有一科『比較革命』,它是本科生的科。教英國革命的是 Lawrence Stone,世界知名的教授;教法國革命的是 Robert Darnton,也是位專家;教中國革命的是我,當然我比不上他們,我在他們身上也學到很多,但重點是,愈是基本的科,愈讓經驗豐富的教授教導,比如『基本物理』也是楊振寧在教。柏克萊加州大學也是這種模式。」
學生選科也要反對專業化
說了這麼多有關院校制度的問題,最後李教授指出,學生自己也應該反對專業化,充分利用時間發展興趣。他認為大學一年級絕對不要分科,更不能一入學就學商科。唯一需要專業訓練很長的專業是醫科。到大學二年級,他建議可以考慮文理分組,但需要鼓勵學生多選科,到三、四年級再分科系,但這個模式香港目前還行不通。「選科的時候,專科不應超過五成,其他時間發展自己的興趣,因為只有自己感興趣的科才會用心學,別人看100頁,你會看300頁。我以前就是這樣,我就是不務正業,不務正業才能做到正業,這就是吊詭的地方。另外,學生自己要互助,組織小團體、讀書會等,一起交流,培養學風。現在也有很多活動,可是大多是社交的,像中大一整天在跳舞拉客的,本末倒置。也有一些憤怒的青年想要改變社會,社會是可以改的,但是要一點一點的改。」
李歐梵教授建議香港開辦私立文理學校,如最近籌辦但政府卻多方阻撓的耶穌會大學,「專業性的大學或專科學校絕對可以開設,但不能和一般大學一樣;換言之,是為專業求職需要——或需要增值——的人設立的,不能和大學同等看待,後者的目的是教育,不是職業訓練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