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年來,任何關注國際關係的人士,不論在哪兒做研究,也不論在為哪一方工作,都不可能不被一個波及面廣泛的勢頭所吸引:全球範圍內,愈來愈多的政府機構和非官方部門,正在採取措施或準備採取措施,以應對中國在海外的「擴張和勢力影響」,或曰中國在外部世界「咄咄逼人的、具有觸犯他方性質的(assertive/aggressive)行為」。
並非早先的「中國威脅論」餘火冒煙
估計有些讀者馬上就會說:這個趨勢乍看起來好像並沒什麼特別新奇之處,大不了就是嚷嚷好多年的「中國威脅論」再來一波嘛!然而,筆者可不是這麼看待的,因為以前是為數不少的外國機構大聲或小聲地談論「來自中國的威脅」,而目前卻是為數日增的外國機構以實際行動或計劃中的行動來對付他們視野裏中國逼近的威脅。
外部世界最近期間對中國的多種反擊,具體實例層出不窮:既有聚焦在中國官方贊助的海外宣傳、教育和文化項目或所謂軟實力投射領域的,也有針對中國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和產權結構不甚清晰的公司從事的高科技(尤其是雙用技術即民用和軍用皆可)轉讓操作的,也有阻止中方資本收購兼併所在國製造業廠家和金融機構的,也有檢討親中的華裔人士金援所在國政界選舉和影響外交政策走向遊說活動的,還有追究中國留學生正規社團在留學地區接受中國駐外使館財源、組織「干涉和操控性」活動的,甚至還有質疑中國新移民社群政治忠誠程度的。至於對來自中國的大宗進口商品有重點地進行反傾銷懲罰、以單一國家軍隊或協調多國武力進行針對中國軍事崛起的抗衡性巡邏和演習,更是被國際媒體高調張揚。
本文標題刻意用「外部世界」,就是因為這些針對中國在海外的項目和活動所發起的反擊雖然還處於實施的起步階段,但發起地點卻不是集中在一兩個國家。美國當然是最引人矚目的發起國之一,但是,就連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這些通常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表現得相當「本分、平和、謙虛」的中小規模國家,也陡然提升了對中國海外勢力和影響的防範及抗衡。這類事例近來發生得過於頻繁,因篇幅所限,此處就不再一一列舉。
理解外部世界反擊的深層思路
對於外部世界以上的反擊勢頭,中國官方發言人及媒體的公開解釋和應對,多半是大家熟悉的那些鏗鏘短語:冷戰思維、反華陰謀、相由心生、草木皆兵、賊喊捉賊、惡人告狀、螳臂擋車、不值一駁,等等。我們必須越過這些套話和成語,冷靜客觀地透視外部世界反擊中國的深層思路,即便我們不同意眾多反擊方的政策取向和具體操作方式,也應該心平氣和地梳理清楚它們背後的脈絡,這對於未來15年的中段時期北京高層如何考量及安排中國和外部世界的相處之道,重要性不言自明。
在國際關係觀察界分析圈裏,對當今中國和外部世界摩擦衝突諸多事態的解讀,最基本的參照框架是三個。第一個在時間上距離今天最近,也最容易吸引工商界人士的關切,那就是1960至1980年代日本和美國之間沒完沒了的貿易糾紛。這個框架在理論上是以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其含義在中文譯名不夠明晰)為分析基準的:對於奉行重商主義的國家來說,國際貿易不像體育比賽而是像戰場。行為國增強本民族國家的實力是其不變的目標;盡可能出口產品以賺取他國的硬通貨是其手段的「陽面」,盡可能設立貿易壁壘以保護本國市場是其手段的「陰面」。陰陽兩面結合在一起,就使得行為國難以和他國合作共贏。日本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後,一直實行的就是這個大戰略。在戰敗之前,日本決策層同時抱有以軍事手段在國際上謀取最大利益的期望;戰敗後再也不願意重操此道,於是以經濟貿易手段來謀取最大利益就成為唯一的富強之道。用當年這個領域最震撼公眾的暢銷書之一的作者的話說,「現在,無論本土廠商多麼有競爭力,在美國沒有一個行業是安全的」,因為日本的做法太厲害(帕特.喬特:《銀彈攻勢》,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1年譯版第1頁)。
第二個框架是蘇聯和西方之間的冷戰。這個框架在理論上是以政治和意識形態為分析基準的:挑戰方對抗西方,是認定西方的價值體系和實踐這套價值觀的政治社會制度既是邪惡的,也是注定要滅亡的。挑戰方不惜以一切手段來促成西方制度的早日滅亡,包括宣傳戰、情報戰、經濟技術競爭戰、代理人戰、直至必要時全面熱戰。滅掉西方制度後,挑戰方將把自己的價值體系和成套制度推廣至全世界,也即是實現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George Kennan, “From Containment to Self-Containment”, pp. 348-423 in G.R. Urban ed., Stalinism: Its Impact on Russia and the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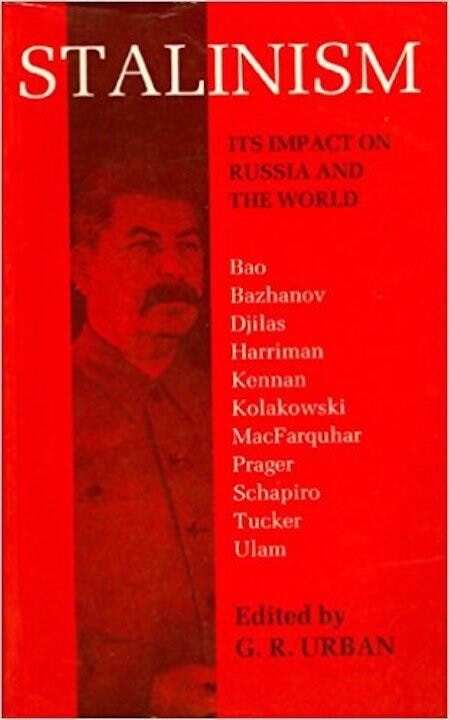
第三個框架在時間上距離今天是最遠的,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世界格局。名著《極端的年代》作者、馬克思主義史學大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對此勾勒得簡明扼要:「對英德兩大競爭國而言,天際才是它們的界限。德國一心想取代英國的國際霸權和海洋王國地位,如果德國意願得逞,國勢已經日衰的英國的地位自然更趨低落。因此,這是一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霸權爭奪戰。法國同樣攸關生死:它的人口、經濟跟德國的差距愈來愈大,而且這種趨勢好像已經無法避免。法國能否繼續躋身諸強之列,資格也受到嚴重挑戰。…… 當時德國的口號是:『以德意志精神更新全世界!』於是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總體戰爆發了。」(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6年譯版,上冊第44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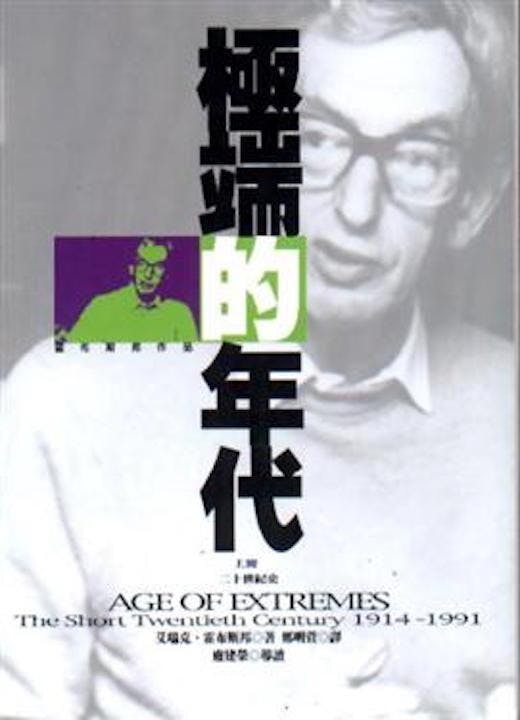
三個參照框架的解釋力和誤差
上述三大參照框架,對解讀當今的中國和外部世界的互動關係都有局部的啟迪意義,也都有重要的誤差。
第一個重商主義的框架,原本是指互動的雙方皆以私營廠商為行為主體,私人企業家被本國政府的宣傳和政策所引導,不按照自由市場的原則做買賣,而是把貿易當作民族國家之間的零和博弈(參閲〈重商主義〉,《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譯版,第3卷第477-481頁)。日本戰後的國際貿易主體也是私營廠商,也是被政府引導,從事違反自由市場原則的操作行為(村上薰:《通產省的挑戰》,台北:創意文化公司1986年譯版)。可是,有些敏鋭的分析家指出,中國經濟的骨幹企業繼續是國有的或政府控股的,拿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貿易摩擦的重商主義框架來解讀中國的對外經貿作為,誤差不可忽視。
第二個冷戰性質的國際關係框架,也面對很多質疑:那個時代的蘇聯及其衛星國,在全球各地不僅和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槍炮對槍炮、核武對核武,不僅對外輸出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而且輸出武裝革命,向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革命組織提供武器裝備和財金援助,必要時甚至派遣大軍開進別國領土扶持紅色政權(比如在阿富汗),力求早日實現世界革命的目標。可是當今的中國,雖然在本國周邊增強軍事實力,對外進行大外宣軟實力投射,但是遠遠沒有在全球範圍內和西方作軍事對抗,更沒有輸出武器金錢支持別國革命組織搞武裝起義和軍事鬥爭。簡言之,當今的中國,並非昔日蘇聯的再版。
有鑒於此,有些分析家就在上述兩大參照框架的關鍵詞之前加上一個首碼「新」(Neo/New)──「新重商主義」、「新冷戰」。奧妙就在這個「新」裏面:新要素是哪些?從何而來?有何特別功能?對互動的對方提出何種新的挑戰?會把當今世界引入何種新的困境?這些要害問題我們將會進一步挖掘。
第三個框架是基於國家或強權之間競爭的歷史經驗歸納,是所謂「價值中立」、接近於「非意識形態化」的分析,被更多的評論家改採納,認為它最適合解讀當今的中國和外部世界的摩擦衝突。即便如此,這個基於第一次大戰前夕國際格局的參照框架的應用,也含有內生的和大環境的困難。我們將在續篇裏再作檢視討論。
原刊於FT中文網,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