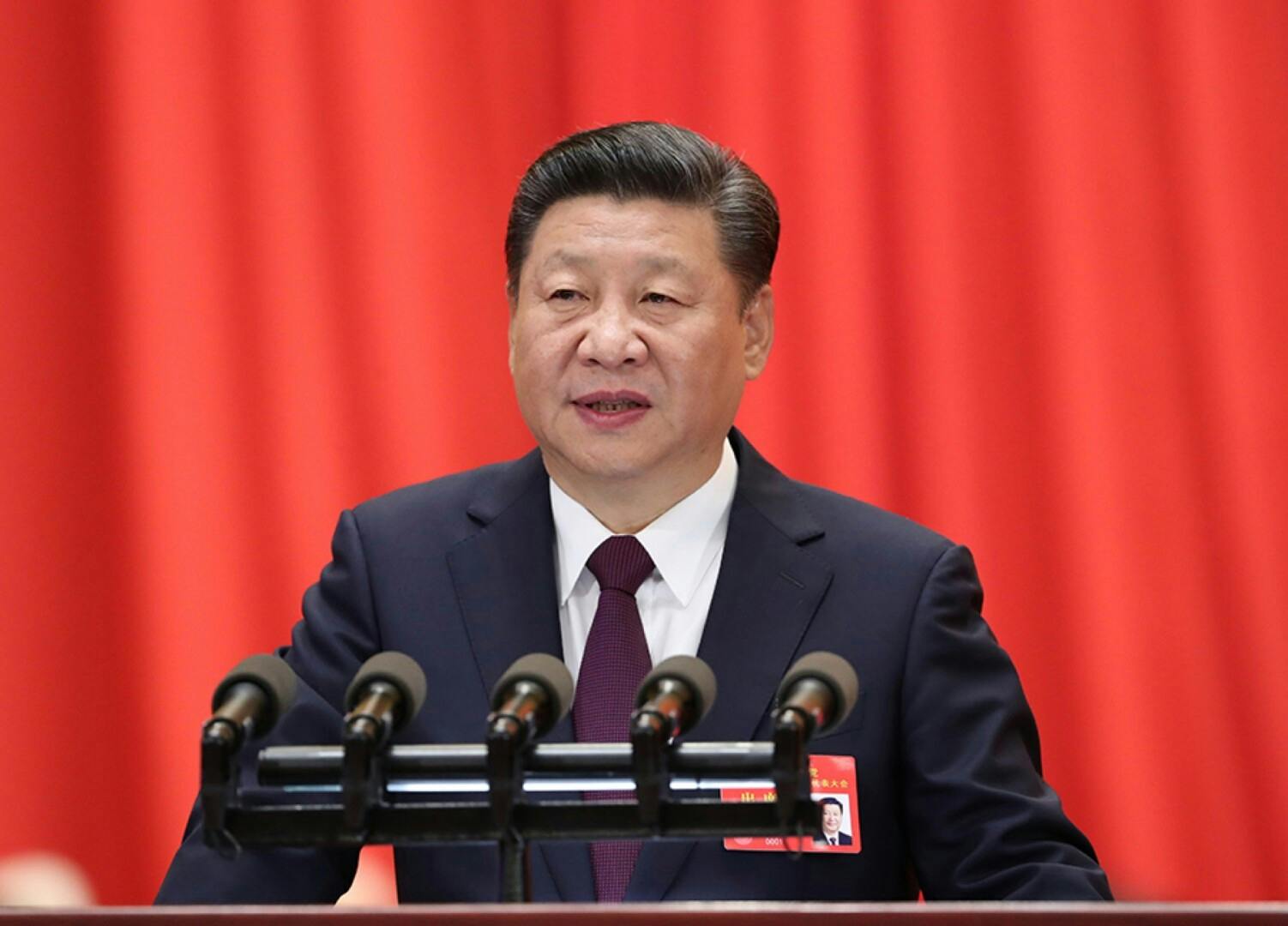就中國可持續經濟發展來說,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需要確立一種有效的政商關係。舊的政商關係出現了重大問題,表現為不可以持續,而新的關係尚待建立。如果不能建立一種有效的新政商關係,下一階段可持續經濟發展就會出現重大問題。中共十八大以來,政商關係改革的目標也非常明確,要從「勾肩搭背」的關係轉型到「親清」關係。
現在的問題在於如何建立這種新型的政商關係。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思考舊的關係是如何產生的。把舊的政商關係所體現的種種現像簡單地統稱為「腐敗」,不足以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更不用說確立新的制度了。只有找到了腐敗的制度根源,才能構建既能預防腐敗,又能促進政商關係的有效制度。
政商關係腐敗源於制度
政商關係的腐敗並非簡單個人層面的原因,而是植根於政府企業之間的制度關係。中國等級性市場體系是由三層市場組成的,並構成各自不同的政商關係。最頂層是在國民經濟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國有企業,海外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
最底層是由中小型民營企業組成的基層市場,海外稱之為「自由資本主義」(或者亞當斯密意義上的「自由市場」)。中間層是政府和民企的關聯企業,或者關聯市場,海外稱之為「戰略性資本主義」,或者「公私夥伴關係企業」,但也有學者常把此關係形容為「裙帶資本主義」,或者「官商勾結」。
這三個層面的政商關係出現了什麼問題呢?先說頂層的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和政府的關係非常特殊,因為國有企業本來就屬於政府。不過,企業屬於政府並非沒有政商關係。實際上,這個層面的政商關係處理不好,其政治社會意義更大,因為國企所承擔的功能不僅僅是經濟上,也是社會政治上的。在這個層面,企業的腐敗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表現在人事關係方面;很多領導幹部甚至是高級領導幹部都來自國有企業。實際上,在改革開放以來,國企一直是一個重要的人才培養基地。很多學者把中國的官僚體系稱為「技術官僚體系」,大多數技術官僚的工作背景就是國有企業。
從國有企業培養的高級幹部包括像周永康那樣的政治局常委。這種提拔方式不僅沒有問題,也是中國制度的強項,但有一個問題沒有處理好,那就是被提拔的幹部和原來工作的國企之間的關係。這些被提拔的幹部往往和原來的企業(系統)有關聯,這有利於他們在成為高級幹部之後培養和提拔自己的支持者,更為重要的是容易形成寡頭政治,干預國家政治。周永康的案例充分說明這一點。
第二:表現在國有資本運用方面;一些高級幹部通過這種政商關係,把國有企業的資本以不同形式投向家族、親族、朋友、支持者的企業,這是明顯的腐敗,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也有國有企業在做企業投資決策時,僅僅是為了政治考量,毫無理性,也造成了國有財產的巨大損失。這方面既表現在國內投資,也表現在海外投資。
底層是自由市場經濟。這個層面的中小企業儘管其經濟總量並不大,但承擔着大量的就業人員,關乎一個地方的社會穩定。再者,中小企業對地方基層政府也有稅收等方面的貢獻。不過,因為這些企業經濟功能強而政治功能弱,政府和官員不會在多大程度上理會他們。
例如,中小企業不能從國有控制的銀行得到有效的金融支持,基本上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在很多地方,如果法制不健全,地方的流氓地痞、豪強甚至個別政府官員會對小企業主有所企圖。除此之外,這個層面的企業基本上處於「自由」的狀態。
不當政商關係演變權錢交易
政商關係最麻煩的是中間層的市場;在這個層面,政商關係不僅不可避免,而且很有必要。一方面,企業做大了,開始需要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企業做大了,政府也開始對企業不放心了,需要「關照企業」。也就是說,這裏的政商關係往往有兩方面因素的結合而促成,即一些企業家的「政治企圖」和一些政府官員的「經濟企圖」。
當「政治企圖」和「經濟企圖」結合在一起時,就演變成為「權力」和「經濟」之間的交易。這種交易既可以由企業家開始,也可以由政府官員開始。企業家的動機是多重的:通過從政府「尋租」把企業做大;在有效法治缺位的情況下,尋求政治保護;通過得到政府的一個位置(例如人大、政協、工商聯組織等)追求社會聲望等等。
政府官員方面也具有很大的動機:直接的經濟利益(向民營企業要錢、入股、甚至是公開地「搶錢」)、安排子女親戚的就業、讓企業家支付子女的就學費用等等。也有一些政府官員用各種方式和民營企業「共同發展」,實現權錢的完全結合。
十八大反腐敗運動以來所發現的各種案例,充分說明了這個領域形形式式的政商腐敗關係,幾乎每一個腐敗官員背後都會牽涉出一大批企業,也幾乎每一個腐敗企業家背後都會牽涉出一大批官員。
正因為出現了如此嚴峻的問題,十八大以來才會發動持久猛烈的反腐敗運動。很顯然,國家可持續經濟發展並不能建立在腐敗基礎之上。不過,「勾肩搭背」的政商關係由來已久,要釐清政商關係並不容易。在反腐敗的強大壓力下,導致了各方的「不作為」。
改革開放以來,就經濟發展來說,中國一直是「四條腿走路」的,即地方政府、國企、民企和外資都各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角。但現在這些主角都不那麼作為了。官僚不作為,他們不知道怎樣和企業家打交道了;國有企業也有同樣的行為。民營企業家或者因為失去了直接的政治支持,或者因為過去的不當行為,而對未來產生深刻的擔憂和不確定性,於是紛紛出走國門。這三者的行為所造成的總體經濟環境,也影響到了外資的行為。
在任何社會,企業無疑是經濟發展的主體。這些年來,人們一直在討論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根據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香港和台灣)的經驗,在逃避中等收入陷阱過程中,處理好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係最為重要。這些亞洲經濟體之所以能夠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在於政府的經濟作用,而政府的經濟作用是通過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係而發揮的。這就是學術界多年來所討論的東亞「發展型政府」的由來。不過,在這些經濟體中,政商關係也產生了重大的腐敗。日本早期的政商關係相當腐敗,即政治人物、官僚和企業之間形成了「鐵三角」關係,後來通過大力改革才改善了關係。韓國也有類似的情形,但缺少有效的改革,直到今天都沒有解決好政商關係,導致歷屆總統都沒有很好的「下場」。香港和新加坡則是兩個相對成功的例子,比較好地解決了腐敗問題。非常有意思的是,新加坡是一個國有企業(政府關聯企業、政府投資企業)佔據主導地位的經濟體,而香港則是一個民營企業佔主導地位的完全自由經濟體。
有效政商關係需要制度配合
新加坡的案例說明了,並不是國有企業都是會腐敗的,問題在於如何設計一套有效的制度。不過,與新加坡不同,對中國來說,國企的最大腐敗莫過於其成為政治寡頭的經濟基礎。這方面,前蘇聯和今天的俄國有很多的經驗教訓。在蘇聯時期,強大的國有企業幾乎壟斷了國家所有的經濟空間,造成了方方面面的壟斷。蘇聯的國民經濟最終在美蘇冷戰期間走向軍事化,和國企壟斷密不可分。
蘇聯之後,直到現在,俄羅斯仍然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葉利欽時期由國企通過私有化轉型成為寡頭,對國家政治構成了威脅。今天的普京也只是通過打壓「異己」的寡頭,而支持「親己」的寡頭以維持局面。中國如果要預防寡頭,可能要對國企「做強做大」做一科學和深入的認識。
「做強做大」並不是說國企要佔領經濟空間的各個方面,而是要在特定的領域,例如自然壟斷、關鍵的產業、關乎社會公共品的產業,國企發揮強大的作用。即使是在這些領域,仍然需要建立反壟斷機制。同時,國企也應當和民營企業確立邊界。
在中間層面,要建立「親清」的政商關係就要處理好幾對重要關係。其一,企業主和企業之間的邊界。現在的情況是,企業家一出事情,整個企業就會受到影響,甚至被停業和關閉。如何使得企業不受重大影響?這方面國外有很多好的經驗可以參照。
其二,企業和政府的邊界;最主要的是要建立政府和企業作為兩個實體之間的關係。現在的政商關係並不是兩個實體之間的關係,而是企業家個人和政府官員個人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表現為不可繼承性,從而也是持續的腐敗,因為每一代企業家都要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培養和政府官員的關係。這客觀上在各個層面造成了人們所說的「一朝天子一朝商」的局面。
其三,產業政策和企業的關係;政府掌握產業政策,企業執行。產業政策影響着國家巨量財力的使用,如果決策和執行不當會產生很大的腐敗。政府官員要尋租,經常把資金投向自己有關聯的企業或者自己的「金主」;企業要尋租,尋找和政府官員的關係來獲取產業政策中的巨大利益。這裏,建立公開、透明的產業制度及其產業實施制度是關鍵。
此外,政府官員的「下海」問題也是必須面對的。對現行官員必須實行嚴厲的管治,確立有效的「利益衝突條例」,防止官員對企業的利益輸送。這方面,各地隨着反腐敗機制的建立,會得到相當的改善。不過,對一些退休官員在企業兼職的問題,可能需要考量。一方面很難禁止,同時也可以利用這些官員的豐富經驗來促進經濟發展。這方面,很多國家也有很好的經驗可供參考。
在底層中小企業領域,政商關係也極其重要。大多創新都發生在這個領域,是培養新企業和企業家的領域。這個領域政府的支持很重要。第一、金融。金融業需要結構性改革,需要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的中小銀行或者金融機構。第二、技術創新的保護,表現在知識產權的保護。
現在中小企業的很多技術要不被抄襲,要不被大企業買斷而「消失」。技術被抄襲就會影響創造者的動力,這點容易理解。大企業收購技術的動力則經常被忽視。這在互聯網領域表現尤其明顯,很多所謂的「風險投資」不是為了培養新企業,而是防止新技術對現存企業的壟斷地位所可能帶來的風險。因此,所謂的「投資」實際上阻礙了經濟和技術的進步。
今天,中國已經進入從中等收入社會邁向高收入社會的過程,也是需要確立有效政商關係的時候了;沒有有效的政商關係,這個過程會很難完成。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