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香港安定繁榮的支柱,近年動亂,掀起對法治危機的關注。不少人對中華律法。存在偏見和誤解。本文從歷史文化與倫理道德,比較中西法理緣由與特色,同時涉及國家與人權、刑法與宗教等範疇,並指出香港法治的危機與解困之道。
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
亂禮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鬥,困乏我多情。(註1)
偏見與誤解
1949年國學大師錢穆先生與唐君毅先生等以「誠明」為校訓,在風雨飄搖中的香港,歷盡艱辛創建新亞書院,致志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莊嚴的校歌,點出人應以尊貴的心靈與廣闊的胸襟,面對一切困厄和挑戰。當年的港人,在戰亂中掙扎求存,相濡以沫,孕育了「獅子山下精神」。艱苦奮鬥,自強不息,造就了「東方之珠」的經濟奇跡。在殖民統治與教育薰陶下,年輕一代的香港人日漸西化,與中華文化疏離,甚至跡近無知。其中也包括了不少深受西方教育的學者專家與各界高層人士。一葉知秋,20世紀60年代,錢穆先生沉痛地指出:「香港缺乏文化教育,只會培養出能講英語、自私自利、不擇手段、只求生存與功利的人才。」並建議:「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並有真實的改進,必先使其對歷史有深切的認識和了解。」(註2)
每一代人對生命,有不同的體悟,好惡與價值觀亦隨之相異。凡事物極必反,盛極而衰。大半個世紀匆匆流逝,「獅子山下精神」早已成為歷史,重英輕中的氣氛亦已成為過去。正藉中國崛起、中港融合之際,面對日趨複雜而微妙的國內外形勢,國學,包括中華文化、歷史和哲學,顯得日益重要,港人必須與時並進,自強不息,才能保住這數十年努力的成果,不被淘汰。因為教養的局限、對國學的疏離與無知,在中西文化衝突與國際形勢急速變動的浪潮中,港人的價值觀與思維出現混淆,因而形成嚴重的偏見和誤解。近年出現歪風和亂象的因由,不少源於中西文化的矛盾和衝突。
法治是香港安定繁榮的支柱,不少人誤以為只有西方的法治,才是至高無上的制度。談到中國的法治,常評為「貪污舞弊、專制霸權」、甚至有認為「東方社會常把法律或法治,掛靠到巫術神權教權皇權上,神聖化、道德化……把法律組織化、群眾化、工具化和機械化……無法無天」,相對地,「資本主義社會(香港百多年)的法治,其精神一般而言在於體制完整,客觀平等標準,公正維持秩序,約束官民嚴格恪守,不徇私枉法,官民互信。」(註3)若真如是,文化如此低劣,中華民族早已滅亡,如何能孕育出漢唐等盛世?對於這些謬論,錢穆先生早已有詳盡的分析。(註4)鑑古而知今,且讓我們跟隨先哲的足跡,以中西文化與歷史的角度,來探索一下中西法律的異同,從而剖析現今香港法治的困局,糾正人們的一些偏見與誤解。

倫理與道德
懷有偏見之士,常批評中華文化的「倫理道德」封建而落後,卻不明其深意。「倫理」是一個社群在日常相處中,為維護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秩序而建立,並逐漸形成的行為規範;「道德」則是指該社群對成員衡量行為正當與否的觀念標準。不論中外,每個社群都有其獨特的發展進程,有它內部公認或約定俗成的規範,是行為的基石。倫理道德及價值觀一旦模糊不清,矛盾叢生,無法協調,就會出現亂象。因此,倫理道德是每一個社群維持安定和諧必需的基礎,它是教化人心、用以衡量是非對錯的「公道」。百年來,香港被殖民統治,中西文化薈萃,短視而功利,因此歷來重西輕中、重術輕道,強調個人主義、自由與人權,忽視倫理道德與文化教育。有媒體報道云:「今日的年青人胡作非為、任性滋事,皆源於『佔中』動亂,釋放了人性的黑暗面,法治未昭彰,法律界歪曲法理,愚昧荼毒年青人的心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經歷半世紀的經濟騰飛,物極而必反,今天的亂象,非一日之寒。
道德觀與法律
法律是文化的現象和產物,同時反映出該民族的心理狀態。中西文化的歷史進程與道德觀皆異,是以對法律的觀念自有不同。西方文化的道德觀始於古希臘哲學,由蘇格拉底、柏拉圖,以至亞里士多德,一脈相承。他們認為人類的道德生於行為,實行而成習慣;並不認為人性會自發向上,認為一切諸善,皆由外間規律影響而成,因此非常重視立法。司法、法律所規定的行為,皆本於道德,因而成為社會的規範,能令人實行一切美德,禁止罪惡。加上基督教教義認為人有原罪,不覺得人性本善,因此捨棄人的感情而就理性,重智而輕情,把公平看成是至德,合法即是公平。守法者為公平,破壞法律是為不公。國家超乎於個人之上,而法律則由國家所立,是公平的化身與保護者,教人克盡公民之責,因此西方社會極為重視守法精神。

相對地,中國儒家主張性善,道德皆由內心而發,本於天賦的內心訴求。認為法律只是用來防止過錯與非為,而人性的美德,是由內心充沛自發,並非由於遵守法律而產生,法律只是用以補道德之不足。儒家認為人「性本善」,因此偏重「真情」,例如「仁孝」。而人類的道德意義,遠在國家之上。相對而言,國家是人為的、短暫的,天道是永恆的、至大的。因此孔子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註5)《易道》更強調天地萬物,皆源於陰陽交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人性兼含善惡,因此教育與管治之道,皆重抑惡揚善。荀子身處戰國亂世,認為人的情欲乃是人的生理素質,人性本無善惡之分,它只是就人的本然情欲,在群體社會中所造成的暴亂而言。韓非子則更進一步,肯定人性本身的「自為心」,整日地為其私利而忙、為其利害而計較,故認為人性本惡。老子更早已強調:「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華文化主張兼容並蓄,審時度勢,因時制宜,以經權管治。經是常道,權即變通。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中華文化做人做事,講求合情合理合法,注重培育倫理道德成為人的內在法則,以修身為本。法律,只是外在的、用以扶正個人行為與社會風氣的輔助工具而已。倫理道德修為,是成敗的關鍵,處上位者尤為重要,因為賢者能教化天下、惠澤萬民,不賢者則反之。今天許多香港人,只顧談法治,而忽視情理與倫理道德教化,本末倒置,禍患自然隨之。這正是一些人迷信法治,認為它是唯一決定是非對錯的準則的最大謬誤。
權利與刑法
西方文化對公平的涵義,歸根結柢,是為個人的權利。而其法律上公平觀念的進展,皆以權利爭衡為重。從古希臘狹義的市邦,到羅馬法的權利進程,皆着重於狹義的「公民觀念」。市民與非市民(外國人)往往享有不同的待遇,不談道德元素。法律成為城邦安定的基石,因為它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能相互依存,一旦出現紛爭,亦無需訴諸武力。因此,新法律的建立,同時意味着社會上某些勢位權力的變動,牽連甚廣,必慎為之。
相對中國人的法律,多指「刑法」,偏重於道德,法用以懲罰罪惡,不在保障權利。老子說:「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古來立法,主治盜賊,偏重禦姦禁暴。單拿公元前400多年的羅馬《十二銅表法》,跟同期的法家李悝《法經》的內容比較一下,就很清楚看到中西律法所側重不同之處。前者關注的是:傳喚、審判、求償、父權、繼承、監護、所有權、房屋土地、私法、公法、宗教法、追補等。主要是跟訴訟、人權及物權有關。而《法經》則是盜法、賊法、捕法、雜法、具法等。單從律名,已能看出端倪。
今天的香港法律,沿用港英時代的英國《普通法》,經多年實踐和積累,對人權及物權尤為清晰。進入廿一世紀,科技與國際形勢促使社會劇變,若社會的運作過分依賴現存法制,必然陷於守舊。任何法典皆奠基於過去的經驗,容易趨於凝固和僵化。當遇到新難題時,因為缺乏條文指引,官員往往束手無策,議而不決,形成紛爭迭起。香港許多過時的法例,早已窒礙了社會的發展,加上紊亂而低效的立法會,使香港的社會問題雪上加霜。這現象亦普遍出現在歷史悠久的公營機構及非牟利團體。商界的情況不同,因為競爭激烈,市場千變萬化,必須不斷創新,方能適者生存。
註1,節錄自《新亞書院校歌》。
註2,《錢賓四全集》,經緯出版社。
註3,洪清田:〈法治内生 「被凌駕、防錯與糾錯」機制的中西之別〉,《明報》, 2017年9月5日。
註4,錢穆:《政學私言》,商務印書館,1945。
註5,《論語・為政》。
中西文化衝突與香港法治困局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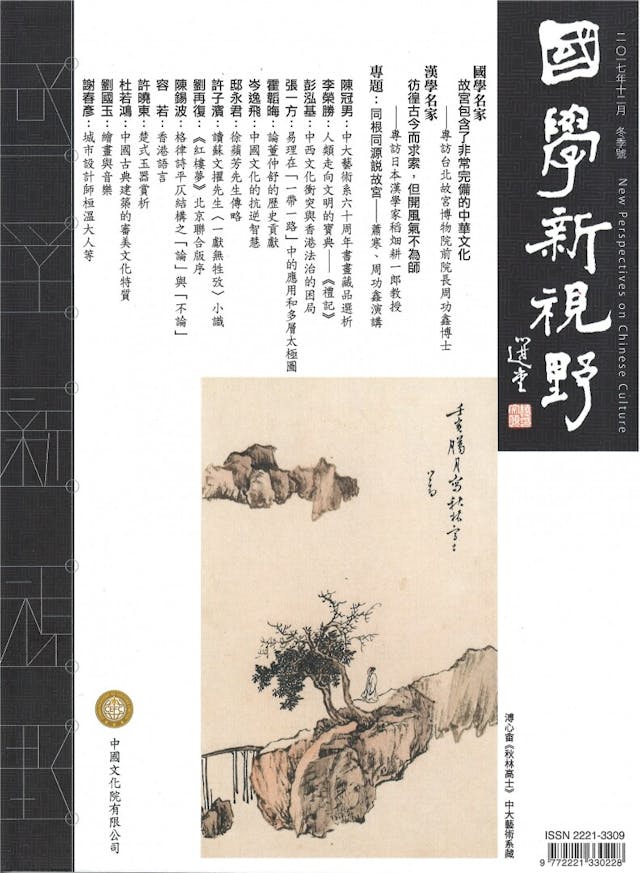
摘錄自《國學新視野》,本社獲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