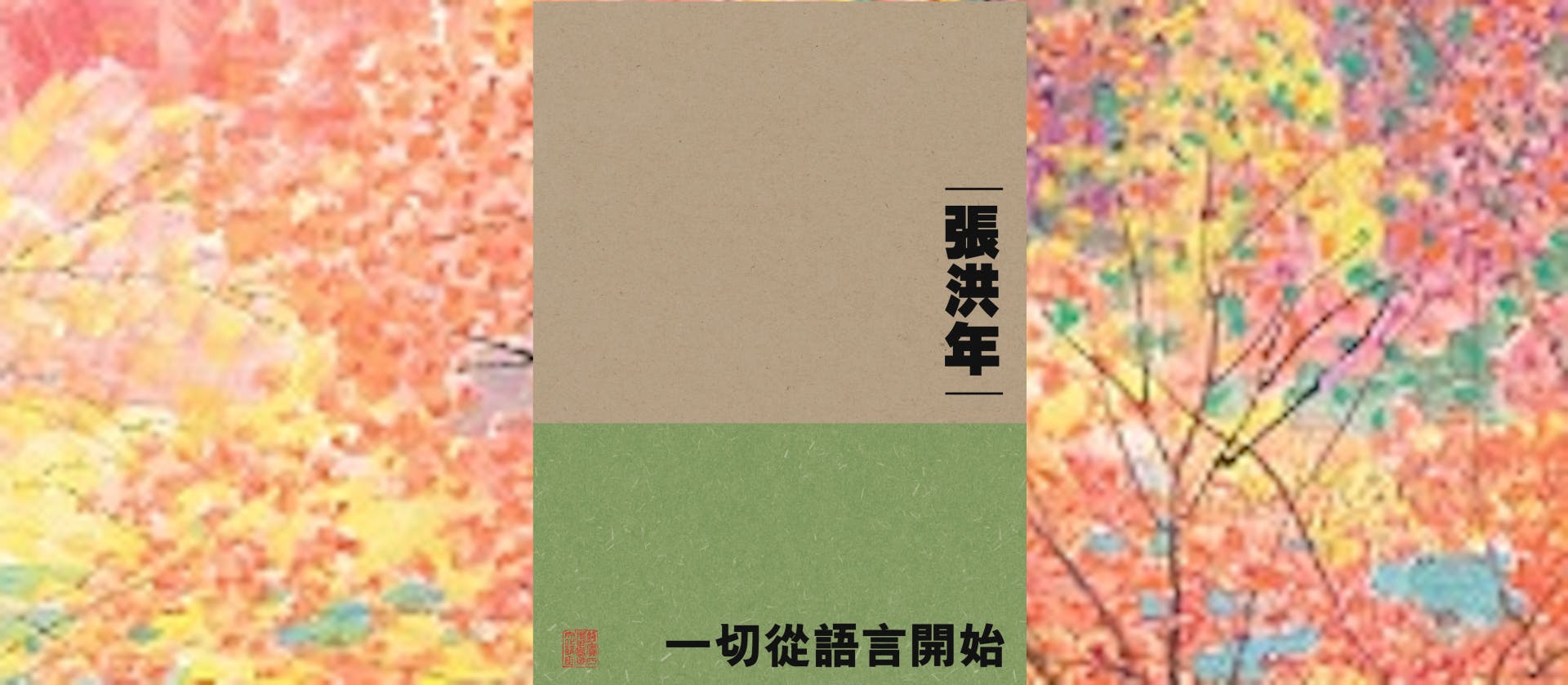我是1963年進入中文大學,在新亞書院上中文系,那年我剛好17歲,新亞還在農圃道。17歲的小伙子好奇心特重,對什麼都感到興趣,所以我什麼樣的課都想去修讀或旁聽。中文、英文、哲學、歷史、藝術系的課都上過一些。那個年頭,新亞是名師如雲,除了校長錢穆先生以外,還有中文系的潘重規先生、哲學系的唐君毅先生、英文系的張葆恆先生、藝術系的王季遷先生、歷史系的牟潤孫先生。我雜七雜八的上課,半懂半不懂,但總算是初入堂廡,眼界漸開。我們中文系那年一年級只有21個同學,大家一起上課、吃飯、參加不同的活動,一邊讀書,一邊玩樂,快活不知時日。
錢先生是1965年離開新亞。那時我已經是大二的學生。在那兩年中,我沒有上過錢先生的課,但是錢先生的講演,我們都盡可能去聽。錢先生口音很重,我雖然會說上海話,但是兩年下來,還只能聽個大概。錢先生很喜歡下午時分,在新亞長廊上來回踱方步。他個子不大,但是在夕陽斜照底下,他背後的身影很長。我們這些17、18歲的小青年,從教室的窗戶,或是在籃球場的欄杆旁邊,望着錢先生的身影,一代宗師的風範,我們都有時候看呆了。也許是太年輕了,心態懵懂,只知道景仰,而不知道景仰背後該做些什麼。我們的系主任潘重規先生,師從黃侃先生,學問淵博。有一天,他在飯後和我們閒聊,說起他自己讀書的艱辛。3000年的經典,他在故紙堆中,埋頭苦讀20年,這才稍稍明白別人提出任何一個小問題,背後其實都牽涉到一些更大的問題,自己這也才敢略略表示自己的看法。學海無涯,他語重心長地說,要是同學還不到20歲的也許可以再玩一些日子,要是已經過了20歲才開始認真唸書,那就為時已晚。當頭棒喝,我們這才漸漸收拾起玩耍的心,打開書本,好好地跟老師學習。
重回新亞中文系
2004年,我回到中文系工作。馬料水的中大跟我從前在農圃道上學的新亞書院不很一樣,原先不很習慣。幾年下來,漸漸熟悉學校的新制度,對新環境也漸漸產生感情,和老師共事,和同學共同學習。是機緣巧合,讓我有這個機會重新投入中大,在中文系任職,參與各種教研和文娛活動,從真實經驗中體會到什麼是我們新亞「結隊向前行」的精神。我們中文系50年前的名師宿儒雖然不再,但是新一輩的老師,人才濟濟,各有自己的研究專長和視野,我從他們身上學到許多。前後6年,同學對我的影響也很大。年輕人的朝氣活力,勇於嘗試、勇於拓新,正是我們做學問最大的原動力。2010年,我退休後重返美國故居。
我這次承新亞書院的邀請,三月間前來參加錢賓四先生學術講座,發表論文,實在感到慚愧和惶恐。錢先生是國學大師,他的學問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他當年南來,艱險奮進之際,創辦新亞書院,繼承我中華人文精神。這種對學問和正義的執着、為繼往開來所作的努力,是錢先生給後學樹立的典範精神。我回首過去,無論在教學或研究方面,自己都是乏善足陳。兩年前,信廣來教授和黃乃正教授兩位前後院長力邀來訪,我的反應是這絕對不可能。我只是一個對語言稍有研究的人,蚍蜉漏見,所知實在有限。怎敢承擔這如此重要的任務?我們談了很久,兩位院長盛意拳拳,我感到卻之不恭。我翻看這許多年來擔任講座的先生都是博學鴻儒,大塊文章,發人深省。我想要是能從語言學的角度討論一些問題,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也許可以提供給各位老師同學參考。考慮再三,我終於不揣其漏,大膽地把擔子接過來。學問之路艱險奮進,原無止境。我的看法就是有粗疏不成熟之處,相信諸位先生一定有以諒我。
我從上研究院開始,研究重點一直是放在語言學上。但是這許多年來,我對文史哲各個領域的興趣從來沒有丟下。這也許是因為文史哲的研究都離不開語言文字。倉頡造字,開啟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文字本諸語言,但口語相傳還往往有賴文字記錄。所謂文以載道,「文」可以理解為表達「道」的形象工具。道可道非常道,道和文之間所表達的雖有偏差,但是道德五千言,還是離不開語言文字。玄奘西域取經,韓愈文起八代之衰,五四倡白話代替文言,哪一種人文工作不是從語言開始?我以前在美國教書的時候,我們的系叫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有人問為什麼不叫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又或者叫EastAsian Civilization?我們都知道Oriental一詞在70-80年代受東方主義研究興起的影響而被淘汰。至於language一詞的概括面是否全面恰當?當時系裏年長的同事說,所有的文化文史研究,都是以語言為根本。所以用language一個字,就可以照顧到整個文化大範疇。我們系本身就兼顧語言、文學兩大範疇,同時也要求外系老師參與教學,從理論討論到材料掌握,進行跨系、跨範疇的研究,拓寬各人自己的視野和識見。
發掘早期粵語趣聞
語言學涉獵面其實很廣,舉凡任何和語言甚至文字有關的現象,都值得深入探討和分析。我的研究重點放在漢語,對歷時和共時變化的觀察、對方言之間的異同、對漢語教學所面對的各種課題,我或多或少都做過一些研究,發表過一些文章。不過這許多年來,我的興趣一直集中在粵語。我在中大上研究院的時候,老師是周法高先生,他讓我寫粵語語法,這就決定我接着幾十年的研究路子。我來美國唸書,老師是張琨先生,他讓我寫敦煌語法,啟發我從歷史角度切入,探討歷時語法變化的軌跡。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我開始搜集有關十九世紀粵語的老材料,研究早期粵語。我在香港工作期間,得到香港政府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資助,讓我能集中精神在這方面做深入的研究,建立資料庫。
我前後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早期粵語的文章,特別是擬構粵語在這快兩百年間的語音和語法遞變規律。這次講座,就把一部分的研究分成兩講,藉以描述早期粵語中一些特殊現象。第一講是有關粵語語法,利用早期傳教士等編寫的粵語口語教材,摘取其中一些特別用例,究其所以,進行一種比較有系統的語法分析。第二講的重點是粵音,所用的材料是一份1866年編製的中英雙語地圖,把其中有關香港、九龍和新界一帶的地名,歸攏在一起,考察當時地名註音所代表的到底是什麼語言?是早期粵語,還是別地方言?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對比十九世紀的讀音和今日21世紀粵語的發音,從同異中找尋這一百多年語音演變的痕跡。兩講所據原有文章都在文中一一列明。
至於第三講,我選了一個文學的題目,討論魯迅的小說。我不是研究文學的人,但對文學、特別是小說別有偏愛。我曾經教過古典和現代小說,也寫過一些有關文章;但因為不是科班出身,沒有接受過正式的訓練,討論未免有嫌是野狐禪。我研究語言,因為我相信任何一個人張口吐舌,發放聲音,每個聲音、每個詞語、每個句子,都是按着一定的規律組合,表達自己心中想表達的意思。要是在聲音高低、用詞造句方面,略有挪動,那麼表達的意思或語氣也就有所不同。要是我能從語言表面呈現的現象而理出語言背後的規律和變化,那麼我想研究文學也應該可以循着同樣路子,解構文本。文學創作,嘔心瀝血。一字一句背後又何嘗不能說明作者寫作時的用心良苦?我就是想從小說的文字中找出文字背後所蘊藏的涵義。我這次討論的是魯迅名作《祝福》。野人獻曝,我講演的時候,在座許多都是研究文學的專家學者,我戰戰兢兢之餘,最後用了「魯班門前說魯迅」一句作為結語,就是為了向聽眾表示我由衷感到的不足。
這次講演的稿子,承中文大學出版社不棄,輯成小書。書名就以《一切從語言開始》為題。文章按講演形式發表,以口語為主,文字略作潤飾。文中不詳列腳註或引用書目,但是在討論中有必須交代的地方,就另作說明。三講部分內容曾在不同學術會議上發表,有關粵語的兩講則根據已發表多篇文章修改成稿,討論部分較簡略,詳細內容請參看原文。書前附有鄧思穎教授為講演撰寫的講着簡介,謬譽有加,實在愧不敢當。
我研究粵語的計劃,前後得到片岡新、郭必之和姚玉敏三位先生多年的鼓勵和協助,在香港講演的那三天,在場聽眾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供我參考,銘感之心,非語言所能形容。新亞講演是陳佩瑩小姐負責一切,籌備工作前後進行幾近一年,會前會後的許多細節和活動,都是她一手包辦。這次講演一切進行順利,陳小姐居功至大。在港期間,得到大學各同仁熱心的招待,實在感激。特別是新亞書院的黃乃正教授、朱嘉濠教授、陳新安教授,中文系的何志華教授、鄧思穎教授,在百忙中抽空主持講演、設宴款待,再三多謝。演講後,得到出版社社長甘琦女士、經理黃麗芬女士、和編輯葉敏磊女士、余敏聰先生全力策劃出版事宜,萬分感激。第一講承黃俊浩先生按當日演講發言謄寫全稿,以便修訂,而三講全文蒙彭佩玲小姐細心校正,費心勞神,在此一併多謝。我特別要借這個機會向陳志新先生表示感謝。這許多年來,陳先生大力支持新亞書院的活動。因為他的慷慨情懷,新亞才能每年如期舉行錢賓四先生學術講座,讓各地學者有機會來到新亞進行學術交流,秉承新亞精神,十萬里、五千載,共同結隊前行,向着不同研究領域共同邁進。
大半輩子與非母語打交道
我研究粵語,但粵語並不是我的母語。我原籍江蘇鎮江,生於上海,在香港長大。我能說粵語,但總有外鄉人的腔調,但是在新亞上學的時候,同班同學常常糾正我的發音。我能說國語,其實也是在新亞接受的訓練。當年我們必得修讀國語,老師是王兆麟先生。他是北京人,教我們說國語,一個字一個字的調教、一個一個聲音的改正。有人說我是雙聲帶,其實都是從新亞開始。
總其言,我的一切從17歲到今年70歲都是新亞給我的機會,讓我成長。17歲的我是充滿好奇的小伙子,70歲的我是個衷心感到滿足的老人。不過,我還是充滿童真的好奇心,對什麼都會感到興趣,只是有時候會感到力不從心。我家住在加州三藩市附近一個小城,叫小山城。後院向東,前門朝西。每天早晚都可以看到雲起雲落的景象。我知道,我在院子裏一坐,坐看雲起時,就會想到遠隔重洋的雲起軒、雲起軒裏的大碗牛肉麵、雲起軒中的諸位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