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資深媒體人李禮撰寫的《求變者:回首與重訪》在第九章敘述了梁啟超於辛亥革命前後的經歷,本社分兩篇轉載撮要,本篇是第一篇。
達爾文主義融合國家主義
1898年歲末,人們在福州印制的《天演論》裏發現,「新會梁任公」已被悄然從書中「例言」刪去。梁啟超是這本著作最早幾個讀者之一。如果說譯者嚴復是個「群主義者」,為此花了很大工夫詮釋「群」與國家強大的關係,梁啟超則很快把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國家主義混為一體,熔為一爐。他所提倡的「新民」,強調的並非個人至上,而是希望「合眾人之識見以為識見」,「合眾人之力量以為力量」。從這一點看,梁啟超是嚴復真正的同路人。
出版之前,嚴復把一份《天演論》手稿抄本寄給梁啟超,當後者向康有為、夏曾佑展示,三人均為之震動。康有為思想雖如海潮音、獅子吼一樣震撼梁啟超,但眼前的達爾文主義卻為康門所無。在此之前康有為已着手撰寫大部分著作,不過仍從這部新著受益匪淺。史華茲弟子浦嘉珉博士認為,康著中的「達爾文式」段落幾乎可以肯定是嚴復之後的裝飾品,「它們全都以嚴復的詞彙講述達爾文、進化與進步」。這位漢學家堅信,「在著名的1898年維新運動失敗之後,康有為在流亡期間才將這些詞彙添加到其著作的修訂本中」。上述說法很難確定,事實卻是梁啟超迅速加入達爾文主義鼓吹者之列,成為嚴復譯作的重要思想提煉人,並在1897年至1903年間發表超過25篇相關文章。那些未來盛傳的口號很多實際出自梁啟超之手。
李伯元記載的一則「趣事」,顯示了梁啟超在達爾文主義傳播中的巨大影響。1903年,趙爾巽從山西調任湖南,面對學堂學生的思想「騷動」,他大談民權自由,寫下幾千字駁斥文章,其中滿是西方名人,從達爾文、斯賓塞到赫胥黎。不過據幕僚披露說,這位新任巡撫只是買了26本《新民叢報》看了半個月,然後便記住了這些時髦人物和觀點。

不遺餘力在報刊論政
近代諸多傑出人物的啟蒙記憶來自《新民叢報》,這種回憶不勝枚舉。一生雖有組黨參政、教書諸多經歷,梁啟超最突出的形象卻無法脫離報刊背景。「西方的新聞記者有沒有通過自己的寫作得到過皇帝的注意和懸賞,遭遇海外流亡,擁有國內政黨的領導權,以及最終獲得內閣職位、半官方的外交任命以及三種教授職位的呢?」(浦嘉珉語)如果將梁視為一名新聞記者,那麼他的成就確實罕有匹敵。從維新、保皇到立憲,立於革命者與政府之間的梁啟超雖隨時可能被體制重納,但言論無疑大異於官方,隨時可能「出軌」。
正如李劍農所言,梁啟超在《清議報》、《新民叢報》所發議論,「大約都是趨重打破現狀的議論」,這恰是其文章魅力所在。自《新民說》開始,梁明顯更多地切斷與儒家經學的聯繫,將思想資源汲取目標轉向日本和西方,他致力塑造的新國民與舊政府之間,衝突難以避免。「在一定程度上,如果說士大夫中的穩健成員變為激進分子是通過接受宣傳而不是他們自己的經驗,那可能就是梁啟超的作品。」(石約翰)清政府很早就明白康、梁手裏武器不多,除了報刊。「至該逆犯等開設報館,發賣報章,必在華界,但使購閱無人,該逆等自無所施其伎倆。」但海外辦報畢竟鞭長莫及,更要命的是包括眾多官員在內,很多人慢慢成了梁任公的忠實讀者。
不過到了1910年、1911年,梁啟超更多轉入幕後,不再像幾年前與《民報》筆戰時那樣親自上陣。1908年,攝政王掌權令立憲派為之振奮,以為歷史轉機已到,然而政聞社被禁、《政論》月刊停刊卻再次清楚地提醒梁啟超,不要忘了自己仍是官方通緝名單上的一名政治犯。
1910—1911年國會請願運動此起彼伏,漸入高潮。與此遙相呼應,這兩年梁啟超共發表80多篇文章,論及憲政者超過30篇,他傳遞政見的主要渠道這時變為《國風報》和《國民公報》。1910年8月出版的《國民公報》可謂國會請願運動副產品,主持者徐佛蘇追隨梁啟超多年。《國風報》與梁關係更加密切,「半數文章」出自其手,包括以「滄江」之名發表的《立憲九年籌備案恭跋》、《憲政淺說》和《中國國會制度私議》。這個報名暗示了一種持續不變的國家主義訴求。然而到了1911年,國內讀者的情緒明顯超出紙上討論,轉向投入實際行動。
康與梁飽受革命者攻擊
這真是悵然若失的一年,君主立憲漸成幻影,革命者們鹹魚翻身,梁啟超則一度成為他們奚落的對象。起初幾個月,年輕的戴季陶在《天鐸報》不斷抨擊政府、議會,康有為和梁啟超是他最熱衷攻擊的對象:「康有為、梁啟超之奸,吾報斥之不下數十百次」(《請看保皇會之逆證》)。甚至直稱梁啟超為「欺民賣國之蟊賊」;與《天鐸報》有競爭關係的《民立報》也毫不手軟,諷刺打算回國的梁啟超,並對《朝日新聞》標榜康、梁為「志士」和「穩和政治家」表示不滿。
這篇《日人將縱秦檜歸矣》(1911年7月23日)作者是宋教仁,時任《民立報》主筆。他參與了黃花崗起義籌備工作,此間起草一批文告和法律文件以備功成所用,這些準備幾個月後不意在武昌派上用場,儘管革命爆發後譚人鳳抱怨他未及時趕到才讓黎元洪當上領袖。那時宋教仁在上海忙著呼籲國際社會承認革命軍為交戰團體、保持中立。他提醒上海市民,武漢在革命黨控制下「安居營業,絕無何等之妨害」,「革命黨非強盜流氓可比」,國人不能拿叛亂來看這場革命(《民立報》10月17日)。
1911年10月28日,宋教仁抵鄂,全力投入到草擬《中華民國鄂州約法》和《官制草案》之中。翻譯過《日本憲法》《英國制度要覽》、《美國制度概要》的宋,憲政理念相當成熟,《中華民國鄂州約法》體現了他的政治理想。這份《約法》最引人矚目之處在於第二章《人民》,18條款目裏除了2條義務(納稅和當兵),其餘均為權利條款,包括平等、言論出版和結社自由、宗教自由、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對當時的國人來說,無疑吸引力十足。
「人群之進化,莫要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梁啟超為此高呼多年,他和嚴復雖熱衷「進化」,承認進化動力其實來自人的自由,不過言論、思想自由和國家富強對他們來說並非總是一回事,有時甚至看上去背道而馳,為此他們內心矛盾,懷揣不安,終於目睹革命降臨。

革命後返國結束流亡生涯
「這是誰的功勞呢?可以說誰也沒有功勞,可以說誰也有功勞。」10年之後,天津學界慶祝10月10日民國國慶,梁啟超發表演說回憶辛亥革命。「當光緒、宣統之間,全國有知識有血性的人,可算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但主義雖然全同,手段卻有小小差異。」表面上梁是這場革命的旁觀者,新生的民國卻尊其為元勳。
1912年11月13日,梁啟超搭乘「大信丸」啟程歸國,15年流亡生涯以一種戲劇化方式終結:海風惡浪令他困於塘沽,3天後才得登岸。岸上原本準備迎接他的隊伍陣容豪華,張謇和黃興苦候三天才無奈離開。各省歡迎電報蜂擁而至,梁任公抵津之後登記拜訪者超過200人,其中包括前直隸總督張錫鑾和民國首任內閣總理唐紹儀。對無緣登門者來說,利順德酒店和李公祠是那幾天圍觀輿論巨子的最佳去處。
這種場面讓回國前不無忐忑的梁啟超感到吃驚,更讓他吃驚的是自28日入京後的12天,他親歷了自己創造的首都社交奇觀:各種歡迎大會多達19場,最多一天需轉場四次。拜會者如此之多,以至於他從每天早上7點忙到深夜2點,並且只能與客人約定會談不超20分鐘。即便如此很多陌生人還是排不上號,比如梁漱溟之父梁濟,二次投書、四次拜謁均未獲回應,悵然若失。京津待遇之隆,大出梁啟超意料,直到此時他才能如此直觀地感受到自己流亡時出版的報刊影響何在。那些散發着啟蒙和抗議色彩的文章經由各種渠道流入國內,廣為擴散。昔日看不見摸不着的讀者現在如此生動地湧現於面前,而他們正是締造民國的中堅力量。
算起來這一過程從《時務報》已經開始,「凡居亞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啟超」。10年之前,孫寶瑄在日記裏不無誇張地說道。新式報刊在中國第一次淋灕盡致地展示力量正是通過梁啟超,這種輿論魔力至《新民說》達到高潮。戊戌政變、自立軍起義的兩次失敗讓他洞察改造中國之難,從而選擇以新聞業入手。如果說魏源那樣的早期人物,影響力乃是通過友人和同僚網絡,梁則明顯借助了現代公共傳播媒介。當然,現實給他的選擇本也不多,正如流亡時期他自況「惟日日為文字之奴隸」,但「捨此更無術可以盡國民責任於萬一」。彼時日本新聞業蓬勃成長,令人印象深刻。梁啟超驚嘆這裏「婦孺可以操筆札,車夫可以讀新聞」。目睹「今世文明國國民,皆嗜讀報紙如食色然」,他不禁樂觀地按美國報紙受眾比例(六人有一人讀報),推算出中國「應有讀報人八千萬有奇」。這個規模顯然絕無可能,但不妨礙描繪一個美好遠景:「安知中國五十年後,其盛大不有更驚人耳目者乎。是在造時勢之英雄焉矣」(《新民說》)。
推崇思想、言論及出版自由
近代民主在世界各地的推進面貌各異,共同點可視為國家權力分散至社會和個人。在此過程中新興媒體系統雖無法變成一種制度權力,卻足可左右社會心理,因此一躍崛起為第四權力。這種西方觀念經過日本人松本君平等人傳遞給了梁啟超,他將言論、出版自由推崇為現代文明之源:「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實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種種現象皆其子孫也」。
然而當啟蒙話語轉化為大眾媒體語言,實際效果卻異常複雜。《清議報》、《新民叢報》持論理性,卻因此失去聳人聽聞的效果。相比之下,革命報刊更擅煽情,況且現實危機正激發年輕一代與「祖國」決裂,他們所求者乃是快速改變國家和自身命運,必然為各種激動人心的新觀念吸引,一場場改良革命之爭令君主制層層去魅,皇權政治權威蕩然無存。梁啟超的言論不夠刺激,客觀上卻做了大規模西方政治思想掃盲的工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說他與革命宣傳同構,大體不差。
保中國而不保大清,官方對「保國會」的這個指責正是康、梁逃離時身負罪名之一,梁啟超的「國家主義」與清政府本不是一回事,他大力鼓吹國家、朝廷分離,筆下的國家與政府注定潛伏著一種緊張,這種張力尋得恰當時機隨時可能導致衝突。何況理論意義上梁並不否定政權更換的正當性,到了「惡政府之生命與國家之生命,實相克而不並立」時,他可以轉而號召推翻「惡政府」,比如國會請願運動連續遭到彈壓之後。
或者正因為如此,民國肇立,持「梁先生實有間接之大力」(徐佛蘇語)論調者比比皆是。典型如柳亞子,稱梁啟超「雖然沒有敢倡言種族革命,不過字裏行間,引起青年們對於滿清的反感,實在十二分激烈」。更有甚者,乾脆把辛亥年的第一功勞歸之於他,理由是革命能一舉而全國響應,關鍵在於思想改變已深入人心,如無梁啟超多年生花妙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胡適語)。當然,推崇權力操控和直接行動功效者一定難以認同此論,但對那些將思想與觀念置於歷史第一推動力的人們來說,上述觀點卻並非妄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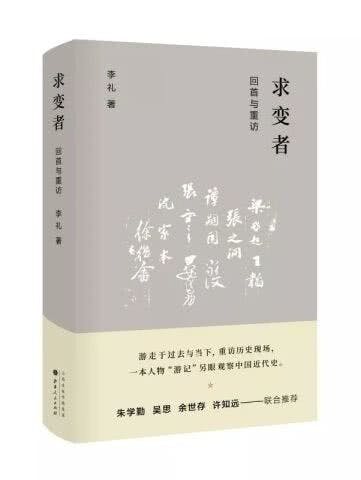
辛亥革命前後的梁啟超之一
原刊於人文經濟學會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