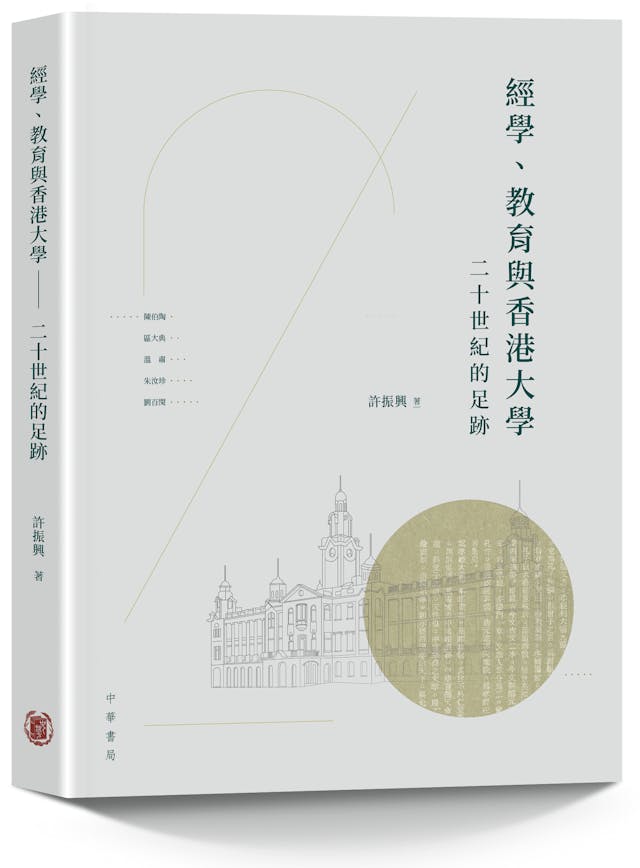「經學」是西漢中期開始確立,以研究、闡釋儒家經籍,建構社會人生準則、成己成人、內聖外王的一門學問。由於它在學術上被西漢以來大多數統治者賦予「法定」的「獨尊」地位,又得到統治者在學校、教育、科舉、任官等方面的大力配合,所以能藉「大一統」、「天命」、「三綱」、「五倫」、「禮治」等思想與觀念的規範,在政治、社會、文化等層面將社會各階層的人民融結成密不可分的合成體。[1]由於它的發展一直跟現實世界息息相關,是以它的實用價值長期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肯定。因此,2000多年來盡心經學者有若恆河沙數,而他們的行事、思想、著述等都一一成為「中國經學」不容忽視的內容。[2]
但隨着科舉制度與君主制度在清末民初相繼被廢除,經學在二十世紀驟然喪失賴以生存的土壤。科舉制度的廢除,令經學無法再成為士子的登龍利器;而民國政府的成立,又令維持經學權威地位的君主集權體制徹底被推翻。[3]西方學校教育既成為國家育人選官的主要途徑,過往以經學為中心的知識體系遂被西方學科分類體系全面取代。「經學」不僅無法成為一門獨立學科(discipline)的名稱,它的內容更先後被劃歸「國學」或「哲學」等學科。這遂使中國的「經學時代」[4]在民國時期因着西方學校教育與學科分類重整的重重衝擊而被逼步上不歸路。[5]
經學在民國時期雖被摒於中、小學課程外,[6]當時不少大學仍藉着開授「國學概論」、「經學歷史」、「經學通論」、「經書選讀」、「專經研究」等科目(course)努力構建無「名」而有「實」的經學教育。[7]「中國經學」的發展遂得以幸運地在「後經學時代」[8]不致驟然橫遭腰斬。二十世紀的中國經歷從「經學時代」走向「後經學時代」的重要轉變,僻處中國南方海隅的香港於這期間能有學者在經學研究與經學教育上貢獻力量,箇中價值與意義自是不容等閒看待。可惜,相關人物的努力一直未獲後世重視。目前已出版的多種中國經學史都未見隻字提及「香港經學」便是明證。[9]
香港大學領導香港的經學研究與經學教育
其實,近數年來香港經學才逐漸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它的定義、對象、內容等無疑都有待學者進一步確定。[10]但二十世紀香港經學的發展跟當時中國的政治、學術、教育、文化聲息相應卻是不爭的事實。日本侵華軍隊在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攻佔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便將二十世紀的香港歷史斷然分割。清廷廢除科舉制度與民國政府廢除君主制度,固然是二十世紀前期中國的要事,而辛亥(1911)革命前後相率移居香港的前清翰林與1912年成立的香港大學,都為此時期香港的經學發展提供了推動者與駐足地。中國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取得最終勝利,與民國政府在內戰中失掉大陸的管治權,都是二十世紀後期中國的要事,而民國政府遷往台灣前後相率南移香港的國內學者,與1946復課的香港大學同樣為此時期香港的經學發展,提供了時、地、人的需要條件。中國政治上的變動意外地為香港的經學發展注入生力軍,而本是大英帝國殖民地大學的香港大學,亦始料不及地一再領導香港的經學研究與經學教育。這箇中的人和事,自然饒具被抽絲剝繭的探究價值。因此,本書雖以《經學、教育與香港大學——二十世紀的足跡》為名,實際仍不可避免地聚焦於跟香港大學息息相關的「二十世紀香港經學」與「二十世紀香港經學教育」。
註解:
[1] 參看周予同(1898-1981)、湯志鈞:〈「經」、「經學」、經學史〉,載朱維錚(1936-2012)主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頁656-657;湯志鈞撰:《近代經學與政治》(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8月),頁1-7;李威熊:〈明代經學發展的主流與旁支〉,載林慶彰、蔣秋華主編:《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年6月),頁77;許道勛(1939-2000)、徐洪興撰:《中華文化通志.學術典.經學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頁1-12、395-400。
[2] 朱維錚的《中國經學史十講》稱:「經學在中國很古老。倘若將西元前一三五年西漢帝國當局宣稱『儒術獨尊』視作起點,倘若將一九一二年民國臨時政府宣佈『廢止讀經』看作終點,那麼以不同形態相繼君臨中世紀列朝統治學說領域的經學,已經走過了兩千來年的漫長旅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小引〉,頁1)
[3] 參看雷海宗(1902-1962)編著、黃振萍整理:《中國通史選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頁702。
[4] 「經學時代」是指儒學成為經學,並主導中國各王朝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發展的時代。馮友蘭(1895-1990)於1931年面世的《中國哲學史》上冊始用此名稱。他認為「自董仲舒(前179-前104)至康有為(1858-1927),大多數著書立說之人,其學說無論如何新奇,皆須於經學中求有根據,方可為一般人所信愛。經學雖常隨時代而變,而各時代精神,大部分必於經學中表現之,自孔子(孔丘,前551-前479)至淮南王(劉安,前179-前122)為子學時代,自董仲舒至康有為則經學時代也。」(馮友蘭撰、塗又光[1927-2012〕纂:《三松堂全集》,第2卷〔《中國哲學史》上冊〕,開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頁370)高瑞泉嘗在他與尹繼佐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哲學卷》指出:「馮友蘭的這個說法有相當的概括力。經學,在今天的學者看來只是傳統學術的一部分,其實在古代中國曾經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因為它提供着整個文化的價值。這至少表現在四個方面:為歷代的政治提供了具體的合法性依據;是科舉取士的正統標準;承擔了文化傳承的任務;注釋經典是哲學家進行哲學創造的主要形式。所以說自董仲舒以後即進入了經學時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頁9)儘管這原是馮友蘭就中國哲學史分期提出的分期說法,現今借用於中國經學史的分期,實亦恰當。趙吉惠(1934-2005)的《中國儒學簡史》便認為後世容或對「經學時代」的具體時限有細微的差異,卻大體一致認同「經學時代」的存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頁337)。本書認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部於1912年廢止師範、中、小學的讀經科正式標誌着「經學時代」的結束。
[5] 主要參看楊天石:〈儒學在近代中國〉,載中國現代文化學會編:《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道路與選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頁311-322;羅志田:〈清末民初經學的邊緣化與史學的走向中心〉,載氏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頁302-341;房德鄰:〈西學東漸與經學的終結〉,載朱誠如等主編:《明清論叢》,第2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4月),頁328-351;左玉河撰:《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10月);張亞群撰:《科舉革廢與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的轉型》(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3月),頁139-151。
[6] 龐樸主編的《20世紀儒學通志.紀事卷》稱:「民國元年(1912)1月19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部頒佈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對舊教育進行改造,其中規定:『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代之以修身、國文和歷史等,而有關儒家經典的內容也只是眾多課程中的一部分。5月,教育部又頒發了第二道法令,『廢止師範、中、小學讀經科』。同時,時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1868-1940)在全國第一屆教育會議上提出了『各級學校不應祭孔』的議案。三個連續動作,標誌着中國長久以來的讀經制度正式廢除。」(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12月,頁18,法帥撰〈廢止讀經〉條)
[7] 參看王應憲:〈民國時期大學經學教育檢視〉,載《中國學術年刊》,第35期(2013年9月),頁110。
[8] 高瑞泉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哲學卷》指出:「後經學時代的最明顯的標誌,是經學從獨尊的、可以提供政治合法性和價值有效性論證的意識形態一變而僅僅為知識的一個特殊門類,而且還是一個日漸冷落的門類。」(頁10)
[9] 朱維錚認為:「經學史在中國卻很年輕。即使從晚清初具近代史學觀念的維新人士的所謂經學論著算起,到上個世紀末,這門學科的歷程,也只有一百多年,況且它的生存還倍歷坎坷。」(《中國經學史十講》,〈小引〉,頁1)因此,目前成書的中國經學史實際只有寥寥數種。皮錫瑞撰(1850-1908)著的《經學歷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馬宗霍(1897-1976)撰著的《中國經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11月)、吳雁南等主編的《中國經學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許道勳與徐洪興合撰的《中國經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都是箇中犖犖大者。
[10] 林慶彰教授在2015年發表的〈香港經學文獻的檢索與利用〉嘗為「香港經學」作定義,稱:「香港經學一詞是最近幾年才流行起來的,它的內涵有待進一步的討論。我粗淺的理解,應符合下列條件學者的研究成果,才能算是香港經學。1.在香港長期任教或作研究的學者,在各地所發表的研究成果。2.某一時段在香港從事教學或研究,此一時段的教學或研究成果。3.香港留學生在世界各地獲得學位之學位論文。符合上述各條件的研究成果,可稱為香港經學。」(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5年第4期〔2015年7月〕,頁1)
新書介紹
書名:《經學、教育與香港大學——二十世紀的足跡》
作者:許振興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20年6月
作者簡介
許振興,香港大學哲學博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先後統籌中文學院「中國歷史與文化」課程與「中國歷史研究(文科碩士)」課程。研究以宋明時期的歷史為主,涵蓋政治、法制、政制、教育、考試與經濟發展等範疇,並旁涉香港的歷史與經學教育。著有《中國經濟史叢論》(合著)、《宋紀受終考研究》,並主編《研宋集》、《研宋二集》、《明清史集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