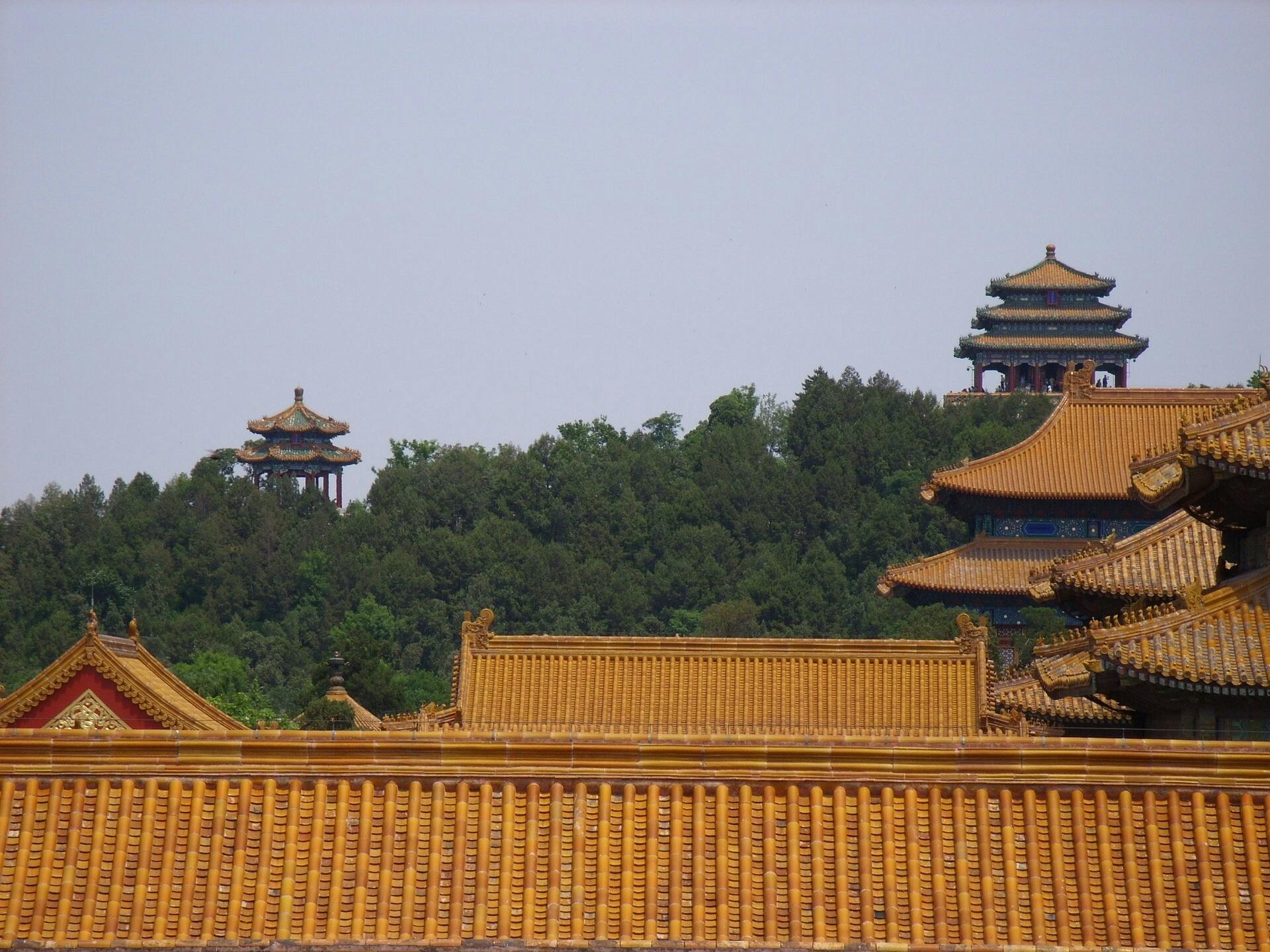在社會層面,今天的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意識形態亂象,各種社會意識形態,無論是進口的還是本土的,紛紛湧現。儘管意識形態的多元是常態,但各種意識形態之間互相爭吵和敵視,並沒有一點點共識。同時,官方本身更缺少能夠讓多數老百姓接受和相信的有效意識形態。官方也有自己的意識形態,但因為這是一種極其精英的意識形態,並不為老百姓所理解。儘管近年來官方也試圖拓展其意識形態的社會性,但並沒有顯著的效果。
這絕非好現象。有效的意識形態為治國理政所需,社會穩定所需,國家發展方向所需。這裏首先要釐清什麼是意識形態。為什麼說中國充滿意識形態,但又缺少有效的意識形態?有人說,就治國理政而言,有效的意識形態就是沒有意識形態。這種說法很有道理。治國理政所需要的是經驗,不是外國的經驗,而是本國的經驗。外國的經驗可以借鑒,因為大家都是人類社會,可以共享經驗,尤其是在近代以來,一波又一波的全球化把世界各國都連接在一起,並且互相影響,治國理政更需要考量到國際因素。但外國的經驗必須融合本國的經驗才會有效;如果不能有機融合或消化不良,將適得其反。治國理政的意識形態和學界所討論的意識形態,並非同一件事情。實際上,學界所說的意識形態只是對一個國家治國理政經驗的總結,即概念化和理論化。
從歷史經驗尋找意識形態的源泉,這是中國的傳統,主要表現在經史的傳承上。在世界各個民族和國家中,很難找到像中國那樣重視歷史經驗在治國理政方面的作用的。所以古人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這句話也不斷被當代人所重複強調。歷史更是最重要的政權合法性來源,這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變化。
「經」是寫「史」的理論
中國有《二十四史》,但這裏的「史」並非今天一般人所理解的歷史。在中國政治傳統上,如何寫史是最為重要的。寫史必須以「經」為原則和指導思想,所以孔子有「吾道一以貫之」的說法,這不僅僅指孔子思想中有一個內核,而且可以指數千年歷史中的內核。在不同時代,人們對「經」有不同的解讀,所以就有「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二經」「十三經」和「十四經」之說。但不管如何變化,大家是有共識的,所包括的都是經典。放到「經史」的內容中,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說,「經」就是寫「史」的「理論」「原則」和「指導思想」。
不難理解,許氏在《說文解字》中解釋,「『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儘管史官為帝王「掌書」「記事」,但其所記的事情,應當處處以「中正公平」為原則。「史」當然不好寫,尤其是當代歷史,因為皇帝都是有「私心」的,都想把「歷史」拉到自己的一邊。不過,中國人又發明了本朝寫前朝的歷史的方法,從本朝看前朝,既可以比較客觀公正,又可以吸取前朝治國理政的經驗。
只有對歷史「公正」,才能吸取有效的經驗。中國《二十四史》很明顯體現這一點。例如,清朝修的《明史》就有《閹黨傳》,記載宦官作惡之事。儘管漢唐以來都有宦官作惡,但明朝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清朝就很注意宦官問題。《明史》又有《流賊傳》,記載李自成、張獻忠兩位農民起義領袖的事情,他們的起義如何促成明朝的滅亡。這裏除了立場問題,對「史」的論述還是很公正的。
「經」指導寫「史」,但「史」對「經」的貢獻更重要。中國人重實踐經驗,不喜歡談論抽象的哲學與理論,人們所說的理論大都是經驗性理論,就是基於經驗之上的理論。這和今天西方社會科學中的「理論」概念相似,就是實證性的理論。從這個視角看,歷史上,「經史」是分不開的,「經」便是「史」。因此,清代史學家和思想家章學誠說「六經皆史」。中國到先秦時期沒有大家公認的「經」,到漢唐之間,經與史的分類才開始變得比較清楚。到了宋代,儒家哲人儘管非常重視經典,但仍沒有能夠決定到底有多少種「經」。王賡武教授認為,在早期,與「經」相比,「史」的用途比較明確,從華夏各民族有記錄開始,就已經有整理史料的想法和做法。之後每個朝代的法政典章、食貨、國防、地理形勢等主要的條例,都成為治國理政的構架。「六經皆史」的概念就是說明,「經」並非抽象的、玄妙的倫理道德,而是國家從歷史教訓集成的結晶。到了宋朝之後,思想家們堅持用儒家的經書作為主導思想,形成社會各階層的共同價值觀。他們編啟蒙讀物《三字經》,教導兒童,「經子通,讀諸史」,即先掌握「經」和「子」的學問,之後才能領會諸史的深層意義。
回到今天中國的意識形態問題,缺少有效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根源在於「經」「史」斷裂。這裏的「斷裂」有兩層含義,第一是傳統經史和現代經史之間的斷裂,第二是經和史之間的斷裂。
《清史》至今寫不出來
就第一方面來說,《明史》為《二十四史》的最後一部,《明史》之後就無中國歷史,到今天《清史》還都沒有寫出來,更不用說是《民國史》了。當然,這不是說《清史》之後沒有歷史書了。今天有太多學者寫的歷史書,但都是學術論述,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史」。這就造成了傳統歷史和近現代史之間的斷裂。
問題在於,為什麼就寫不出《清史》和《民國史》?這裏可能涉及修史本身所遇到的困難。自晚清以來,中國開始受西方影響,不僅表現在思想上,也表現在實踐上。西方對中國的影響改變了中國歷史數千年來的發展軌跡。此前,從秦始皇到清代早期,儘管期間有很大的變化,但都是同一個政治構架內部的變化,也就是說,都是皇朝政治。隨着西方力量的深入,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方面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形成一種新的歷史發展軌跡。
不過,寫不出來的主要原因還是「經」的問題,就是修史的主導思想和原則問題,大家對之沒有共識。就清史來說,之前出版的《清史稿》為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所設清史館編纂清史未定稿,體例依照之前的正史,分「記、志、表、傳」四個部分。再者,因為時間倉促,《清史稿》事實錯誤很多。不過,事實錯誤容易糾正,屬於技術原因。《清史稿》不能成為《清史》主要是政治原因。由於編纂者多為晚清遺老,對清朝歌功頌德,貶低辛亥革命。
這裏所說的政治問題也就是「經」的問題。這不是簡單的方法論問題,例如史料收集方法,而是分析和評估的問題。分析和評估就必然涉及到「經」的問題。從前的做法不可行了,現代的做法又如何呢?從晚清尤其是「五四運動」開始,中國學者使用不同的從西方進口的政治觀念(也就是「經」)來寫歷史,包括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不過,在這樣做的時候,人們忘記了,世界上並沒有單純的理論,理論就是歷史;沒有歷史就沒有理論。結果,簡單地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論來寫中國歷史,最終都是對中國歷史的曲解。近代以來的很多史學著作已經完全改變了傳統的「史」,而是「以史適經」,就是用中國的歷史去適合西方進口的「經」。這很難說是「史」,而是政治。很多歷史概念和論述,直到今天很難理解。例如,有關中國傳統社會的封建性、有關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有關皇權等。「階級」概念也是如此,人們試圖通過用「農民革命」來論述歷史的發展。儘管農民造反的確扮演了一些的作用,但如何能決定中國歷史呢?因為往往是曲解歷史,人們很難看到真實的歷史。沒有真實的歷史,哪會有有效的意識形態?
這裏必須強調「史」在社會科學方面的作用。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就是建立在西方的歷史經驗上的,而歷史是可驗證的。西方的社會科學之所以是西方的軟力量,就是因為它是基於經驗材料之上的,而不是簡單的道德說教和空泛的意識形態。中國無法建立自己的社會科學,而只能照抄照搬西方社會科學,主要是因為中國經史的斷裂。如果沒有「史」,哪有中國社會科學?沒有社會科學,哪有意識形態?
就寫「史」的方法論而言,中國自己具有很優良的傳統。很多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歷史史料收集和分析方法並沒有什麼矛盾。也就是說,人們有很多方法論可以使用。同時,晚清以來的實踐變化是實實在在的,也不是單純的舊史學觀可以解釋的。但這些都不能是寫不出《清史》和《民國史》的借口。人們必須看看清朝是如何修明朝史的?清朝是「外族」,但也修了高質量的《明史》。當然,清朝也是立國100多年之後才修成《明史》的,但畢竟修成了。今天離清朝滅亡100多年了,但《清史》還沒有修出來。對中國的知識界來說,這應當是個說不過去的事情。
因為自晚清以來,意識形態一直主導着史學甚至整個社會科學,要續「史」或者建設社會科學,首先必須有一個「去意識形態化」的過程。同時,寫「史」的過程也是再次確定有效的國家意識形態的過程。如前面所討論的,在中國傳統中,意識形態並不是抽象的理論和教條,而是隱含於一個國家的歷史論述之中的。沒有歷史,就沒有意識形態。今天各種意識形態,無論是西方進口的還是官方所擁有的,之所以無效,主要是帶有太多的道德說教和價值提倡,空洞無物,既不能在歷史的經驗中找到證據,更不能被現實生活所驗證。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叫老百姓相信?
說到底,有效的意識形態建設取決於「史」的論述。沒有「史」,如何解釋今天從何而來?如何論述今天執政的合法性?又如何通向未來呢?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