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蒲實、陳賽
自由選修制:艾略特的改革
1869年,35歲的化學家查爾斯·艾略特上任為哈佛大學新校長。一個陰天的下午,他在麻省劍橋的教會發表就職演講,信心十足地宣布哈佛的教育內容將覆蓋全人類的知識。
人們在無休止地爭論語言、哲學、數學或自然科學是否能很好地訓練學生的心智,自由教育應該以文學素養還是科學素養為主。如今這樣的爭論對我們已經沒有了現實意義。哈佛認為,文學與自然科學之間並沒有實質性的衝突。哈佛並不認為一定要在數學和古典文學、自然科學或形而上學之間做出取捨。我們將兼收並蓄,各取所長。
在《哈佛世紀:鍛造一所國家大學》中,歷史學者理查德·諾頓·史密斯寫道,「1869年是同樣可以看作現代美國的起點的年份」──南北戰爭剛結束沒多久,橫貫美洲大陸的鐵路於這一年建成,美國工業正以令人炫目的速度發展。這個國家需要各種各樣的專家:需要工程師建設橋樑;需要地質學家從地球的外殼中獲得礦物寶藏;需要社會科學家計量這種使人頭昏眼花的發展給人類造成的花費;需要心理學家探測人類隱藏的各種動機;需要立法者和管理者掌握專門的知識、實行多數人的統治……
在開發新大陸的過程中,崇尚實用主義的美國人對這些「有用的知識」有一種天然的尊重。 1862年,美國聯邦政府正式頒布《莫里爾贈地法案》,鼓勵各州利用贈地的資金建造以農工技術為主的應用型大學。一大批州立大學應運而生,比如威斯康星大學、康奈爾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都是著名的贈地大學,它們在課程上並不排斥古典人文科目,但教學的重心卻放在培養農工實用人才方面,以自然科學的應用為主旨,向社會的工業和生產階級提供最好的設施,以使他們獲得實用知識和精神文化。
與之相對的,新英格蘭的古老學院仍然死氣沉沉,不斷重複陳舊課程的傳統還在延續,背誦仍是最重要的教學方法,強迫式的問答則是師生之間最基本的互動。上大學的人口比例在過去幾十年裡一直呈下降趨勢,人們普遍感到高等教育的價值在下降。 1858年入學的亨利·亞當斯在自傳中回憶自己的哈佛歲月:「哈佛教給學生的東西並不多(當然也沒有教給學生太多壞的東西)四年哈佛學院的學習生涯,到最後你心中會留下一片空白,一個心靈的水印。」
事實上,在最初200多年的歷史中,哈佛學院的課程幾乎沒有改變過:邏輯學、修辭學、希臘語、希伯來語、倫理學、形而上學,再加一點數學和自然科學知識。這些知識各自分工明確──學生的邏輯能力由數學培養,其品位依靠希臘語和希伯來語的經典著作來塑造,演講能力有賴於修辭學,他們的理想則通過基督教倫理養成。最終的目標則是培養基督教公民的心智與品格,使他們信奉上帝,獲得真理與自由。
那是一個簡單、清晰而明確的世界──人類知識的體系是穩定而完整的,真理是絕對的、永恆的,大學的目的就是保存它們,並傳授給下一代。
從18世紀開始,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人類知識開始急劇擴張。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的大學在摒棄神學影響之後逐漸形成了專業的學術分工,數學、物理、生物、化學、天文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眾多自然和社會科學的學科日益形成了一個自我完善、相對封閉的學科體系。比起舊知識的傳承,新知識的創造成了現代大學更重要的任務。

另一方面,對「每個人都是可以受教育的」這一觀念的確信,使得高等教育逐漸從作為社會和知識精英保留的特權變為一種普泛性的人權,尤其在美國這樣一個靠教育立國的國家裡。從一開始,知識就是通往自由與財富必不可少的條件。托馬斯·杰斐遜曾說:「一個國家如果指望自己在文明中既愚蠢無知又能得到自由,那麼它所能指望的,實乃過去從未有過將來也不會有的。」
在哈佛園與麻省大街的交界處,Dexter(戴克斯特)門上仍然鑄刻著艾略特校長100年前的題詞,外側寫著「進入本大學,在智慧中成長」,內側則寫著「離開後服務國家與人類」。正是他第一個打破了哈佛與劇烈變化的外部世界之間的隔絕狀況。他的任命,不僅成了哈佛,也成了當時美國高等教育的一個關鍵轉折點—科學將成為未來大學的基石,古典文科的中心地位將被顛覆,而哈佛將從一個古老的、地方性的宗教學院(學生500名,教師23人),變成一所全國性的現代研究型大學。此後,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也紛紛效仿,完成由早期學院向研究型大學的轉變。
一位叫約翰·里德的哈佛學生這樣回憶艾略特任校長時期的哈佛校園生活:「艾略特校長領導的哈佛獨一無二。個人主義之風盛行:一個人如果只圖玩樂,一無所獲,也可以順利通過考試畢業;但另一方面,任何人都可以從全世界的知識寶庫中汲取他想要的一切營養。本科生幾乎無人管制,他們可以住在任何他們想住的地方,做他們想做的事情—只要上課就行。校方從不打算把學生組織起來或者強調任何形式的統一。有些人來上學,口袋裡裝著一年1.5萬美元的零花錢,開著車帶著僕人,住在高檔公寓的豪華套房,而同班的其他人卻在閣樓裡挨餓。」
在對本科生的教學上,艾略特採取的是最放任自由的一種方式—將所有的課程向所有的學生開放,取消一切必修課程,讓學生完全根據興趣選擇學習內容。因為他相信,19歲或20歲的年輕人應該知道他們最喜歡什麼,最適合學習什麼。即使無所愛,至少也應該有所惡。硬把一個學生推向他沒有能力或者沒有興趣的領域去學習是愚蠢的。
在他上任之前,哈佛學生的學習選擇權微乎其微。科目大部分是必修課,唯一可選的只有自然科學與現代語文。如果你想選修拉丁文,無論上大學時拉丁文有多好,都必須等到三年級—就因為那是為三年級學生準備的課程。 1909年,當他40年的校長生涯走到盡頭時,必修課只剩下了一年級新生的英語寫作課和外語課,二、三、四年級的學生可以完全自由地選擇課程。
艾略特年輕時曾經遊學德國,自由選修制一定程度上顯然受到德國大學「學術自由」思想的影響。他認為大學是世界上最容不得獨裁者的地方。另一方面又是出於非常美國式的實用主義的目的:正是通過自由選修制,他才得以將大量專業、實用的知識納入到哈佛的課程之中。例如,語言學的學習不再局限於希臘語和拉丁語的傳統,而是加入了東方語言、德語、法語、意大利語,以及現代英語。哈佛學院的課程大量擴充,從原來的70多門課程增加到400多門。他還創造性地提出了「科目」的概念──包括科目名稱和編號,供各年級學生選修。學分制也由此而生。蘇格拉底式的教學法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教師不再一個人在講台上滔滔不絕地朗讀或演講,而是通過接連不斷地提問、質疑,啟發學生對某個問題的思考、討論、爭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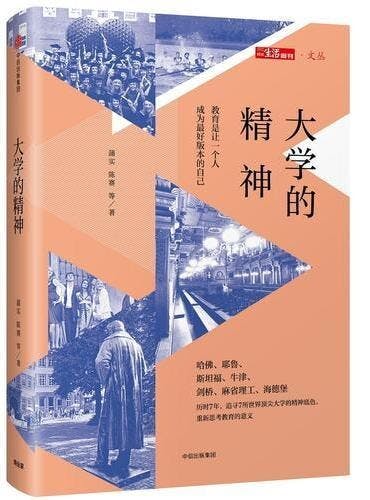
蒲實、陳賽等著
中信出版社2017年1月
上任之前,艾略特曾在《大西洋月刊》上兩度撰文呼籲「新教育」,提出了他的美國大學觀:「美國大學還未從本有的土壤上生長出來,美國大學一旦出現,絕不應該是外國學府的翻版;也不應該如同暖房中的植物,而是從美國社會習俗及政治環境中慢慢自然而形成的產品,提供給一般人實現他的人生目標,也滿足英才的雄心壯志。美國的學院是獨特的,美國的大學也將是原創的,沒有類似或相同的學府可以與之平行比較。」
1894年,上任25年後,艾略特已經創造出一所嶄新的美國大學。它不僅是美國最古老的大學,同時也是最富有的大學。它提供的課程比其他大學都多,任課的是美國最龐大、最受人尊敬的一支教職員隊伍。他著手改造了衰敗的法學院、醫學院,又於1872年建立了文理研究生院,作為師生們進一步探索高深學問的場所,次年頒發了第一個哲學博士學位。在當時美國1000名一流的科學家中,有237人畢業於哈佛,171人畢業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93人畢業於耶魯。
不過,在《知識的自由市場》一書中,路易斯·梅納德教授認為,艾略特對美國大學最具獨創性的一項改造是,在學院(本科)之上交疊添設了職業研究生院,只有經過本科學習,獲得學士學位的學生才有機會進入職業研究生院,比如商學院、法學院、醫學院,完成職業訓練。在此之前,哈佛的職業學院仍然遵循著古老的學徒制,法學院只要住校滿18個月即可獲取學位,醫學院學生只要上過兩個學期的課程,跟隨過一個醫生實習,就可以成為醫學博士。
據說威廉·詹姆斯在哈佛醫學院(1864年入學)讀書時,期末考試只有一道口試題:「如果你能回答這個問題,就能回答任何問題!現在,請告訴我你的家庭以及家裡的情況怎麼樣?」這個看似不起眼的改動,成了美國內戰後高等教育的關鍵變革:一方面在日漸功利化、世俗化的社會裡保留了英式古典自由教育的精髓──本科的學習應該抱著單純的求知之心,為知識而知識;另一方面又迎合了社會的需求,大大抬高了某些職業階層的社會地位—未來的醫生、律師、商人們必須經過四年自由教育的熏陶,才能專心學習謀生所需的知識。
只有這樣,才能如艾略特所願,培養出工業社會的領袖,「實干家、能做出成就的人,他們成功的事業生涯可以大大增進公共福祉」,而不是「這個世界無精打采的觀察家、純粹的生活遊戲的旁觀者,或者那些對別人的勞動過分挑剔的評論家」。他認為,這是一所大學對即將來臨的美國都市社會以及工業社會必須承擔的責任。




































